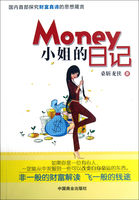医院是最缺笑声的地方,连塑料花都耷拉着脑袋。他这条爱撒野的鱼儿被放到沙漠里,彻底翻腾不起来了。蔫了的他破罐子破摔,彻底沦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鼻哥”:不是挨个病房跟人闲扯偷懒,就是躲在无人的角落睡大觉,瞅准时机,把公家的棉签呀一次性坐垫啥的往怀里揣,偷偷拿出去卖。管后勤的主任一说他,他就嬉皮笑脸地打哈哈:我可是高中毕业的呀,在以前那可就是秀才,秀才你知道不?主任碍于他父母的面子,想想也没多大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样正好,他就可以两眼都不睁,躲进仓库梦周公。不过今天很怪,周公没见着,久违的贾二却一踢腿出场了。只见那贾二一个侧翻来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哈哈大笑,他的鼻子像被针扎一样,一下把他扎醒了。醒来后的他鼻子却真的疼起来了,一阵一阵的,忍过一阵,消停一会又疼得他哇哇叫。借着在医院的优势,他又是拍片又是抽血又是CT,还是检查不出端倪来,再查,被检查室的同事轰出门来,啐道:没事做检查玩,有你这么占公家便宜的么?
渐渐的,鼻子的痛越来越频繁了,几分钟就痛一次。
该不会是什么绝症吧?
这么一想,他吓成了煮烂的面条,软绵绵黏在医院的某个角落,扶也扶不起,叫也叫不动。跟他一起打杂的老杨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还喘着气呢,装什么死?没看这里一堆中药要磨粉呢,想累死老子是不是?
见他没反应,老杨一把捏住他的鼻子,让你睡!让你睡!
他“啪”一声打开老杨的手,翻了个身,继续睡。
就这样,伴着磨药机器的轰轰声,老杨的骂声,他愣是睡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怪了,几个小时过去了,鼻子竟一直没疼?
他疑惑地摸摸鼻子,拿开手一看,手指沾了什么东西,借着玻璃一照,鼻头沾了些白色粉末。对了,一定是刚才老杨捏他鼻子时沾上的。
莫非——这药粉能治鼻子?
他喜得蹦起来,急急追问老杨,你这磨的是什么药?
老杨瞪了他一眼,滑石粉,你没长眼睛呀?
滑石粉有什么用?他问。
清热敛疮啊,你不是秀才吗,不懂?
他顾不上老杨的嘲笑,抓了一把滑石粉就往鼻子上涂,怕粘不住,还拌了点口水。这下可好,活脱脱又成了白鼻哥!
成了白鼻哥的他心情大好,心情一好就想唱曲,唱什么?当然是梦牵魂绕的贾二了。
之乎者也矣焉哉,喜事却从天上来。
在下名姓,贾二秀才!
我饱读诗书十载,
得闲无事书拒常开,问
本追源查三代,
应对如流喔——我可算天才!
于是医院里有了这样一个奇人:好端端推着输液架呢,忽然来个大小跳,挤眉弄眼就开嗓了;或者提着两个热水瓶走路呢,忽然把热水瓶往怀里一搂,咿咿呀呀就唱上了。
医院毕竟不是戏院,没几天,投诉的人就把后勤部办公室的门都敲烂了。主任灵机一动,干脆扔去特殊病房,那里躺着的都是植物人,再怎么吵也不会被投诉。他虽然觉得这些观众不会笑不会鼓掌没什么意思,但既来之则安之,照样唱得卖力。
这天,他正唱得起劲,忽然隐隐约约听到有笑声,他停下来竖起耳朵听又没动静了。他继续唱,笑声又起。他环视着直挺挺躺在床上的“观众”们,顿时有点毛骨惊然。忽然,他发现有台仪器在响,赶紧喊来护士,护士一看,又喊来医生,医生一看,大叫:快!快通知家属,老教授醒了哇!
这捡回一条命的老教授叫苏起,年轻时也是唱丑角的,“文革”时跟戏班子一众人等一起被插旗子批斗,因受不了这侮辱,唱花旦的上吊死了,唱小生的疯了,连唱大花脸的都愁白了头。只有苏起心态最好,嬉皮笑脸没心没肺,活到了平反还活蹦乱跳,还被安排到戏剧学校,一跃成了苏教授。这算苦尽甘来了吧?可惜却没那个命,一场意外成了植物人。
没想他唱的几段戏,竟把苏教授唤醒了。醒来的苏教授揪住医生就问:是谁在唱贾二?
就这样,他认识了苏教授,认识了教授的他更趾高气扬了。今时不同往日呀,医院里终于有了一个认真听他唱的人了,知音,知音懂不?
教授不仅会认真听他唱,听罢还会说,你唱得不错,来跟我学戏吧?
他吃着别人给教授送来的水果,打着哈哈说,你学生那么多,怎么会看上我?
苏教授叹了口气,我那些学生,个个都想唱小生唱花旦,都不肯唱丑角。
也是,在这个“颜值”时代,谁愿意把自己往丑里整呢。
可他不在乎,他本来就是白鼻哥呀。
见他愿意学,苏教授可高兴了,送给他一堆教学的光碟,还掏钱带他去看丑角大佬倌叶兆柏的演出。说起来那场演出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八十岁高龄的叶兆柏表演毫不含糊,一个侧手翻接腾空转身落地亮相,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丑行,不丑哇!威风着咧!
被震撼到的他不再疯疯癫癫乱唱了,开始一板一眼跟着光碟学。这越学就越疑惑,越疑惑就觉自己越无知,一开腔不是调不对,就是不合曲牌,一亮嗓疙疙瘩瘩的,舌头都打结了。
医院可不管那么多,自从上次唤醒植物人的“壮举”之后,医院对他的表演有了新的认识,决定安排给他新的任务:给患孤独症的小孩表演,或者给抑郁症患者表演。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他表演的行头也简单,直接涂上白鼻子就上阵。有时涂的是药粉,有时涂的是食堂的面粉,反正不管涂什么,鼻子再也没疼过。屁绝症,只要有戏唱,不治而愈了!
那天他连唱带翻跟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坐在小凳子上的孤独症小孩全程面无表情,默默蹂躏着手中的橘子。忽然,小孩抠开皱巴巴的橘子皮,跑到他身边,踮起脚往他嘴里喂了一团半肉半皮的东西。他一咬,酸中有苦,苦中有甜,满口白鼻哥的味道哇!他一下就找回了儿时的状态,把小孩抱回椅子后,嘴一歪张口就来:我贾二哇,秀——才!
窗外,嫩绿的小尖芽好奇地从光秃秃的枯树丫上探出头来,互相推搡着,瞧!春天挤眉弄眼地,翻着跟头来了。
(本文发表于《羊城晚报》,获得第五届“珠江情”征文大赛二等奖,后被《岭南文学》转载)
世界末日前夕
风起,风停,叶子来不及起舞,花儿就凋落了。
门开,门关,邻家的喜字还没千透,孩子就呱呱坠地了。
跑得真急呀!她深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继续侍弄院子里的花草。
咔嚓,她剪去桃花歪扭的枝蔓。桃花呀,即便你只灿烂一季,也不能不修边幅不是?
咕噜,她给水仙灌上满满的清水。水仙呀,春天只剩下尾巴,再不开花你就永远装蒜吧。
喵!一只猫从花盆后窜了出来,打翻了一盆正酝酿花蕾的山茶花。她生气地捡起一块小石子扔过去,猫己不见踪影。
算你跑得快,她说。静了一会,她又喃喃道,跑得快又怎样呢,跑得过时间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这么漂亮的院子,这么美好的世界,都要不复存在了。
她早已没了刚知道这个消息时的惊慌与悲伤,安静得跟这个院子一样。独处时,她经常幻想世界末日来临那一天,会是怎样的情形。
或许她正与他坐在摇椅上,看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龇牙咧嘴,气喘吁吁。一圈,两圈,三圈……好像没有尽头,又一下到了尽头。
或许她正与他并排躺在院子中央,被她亲手种的花环绕着,银色的月光披在他们脸上,他久久凝视着她的脸,就像读书时那样。一刹那,那画面就成了永恒。
总之,不管怎么想象,她都离不开他,离不开这个院子。尽管她和他住进这个院子,还不到两个月。
三个月前的某一天,晴,没有风,他进门时脸上却挂着风暴。她一看就明白了,他准是从哪里知道世界末日的事情了。
还有多久?他问。
也就三个月吧。她说。
他不语,任凭脸上的风暴变成雷雨交加。
我想辞了工作。他说。
辞了吧。她温顺地附和。
我们把房子卖了吧。他说。
卖了吧。她温顺地附和。
我们买个院子吧,就是我们一直憧憬那样的。他说。
买吧。她还是温顺地附和。
他们结婚时就约定好了,先努力挣钱,在城市里买房,生孩子,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等将来老了,就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座小房子,在院子里种满各种各样的花,弄一块菜地,再养几条狗,几只鸡,过上世外桃源般的惬意生活。为了这个约定,他们没日没夜地忙,省吃俭用地过。
见他天天要到处去拉业务,她对他说,买辆车吧,挤公交太辛苦了。他摇摇头,养车多费钱呀,还得上保险,还得租车位,还是把钱留着,将来可以买大一点的院子。
见她拖着疲惫的身躯晚归,他对她说,不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她不肯,又不是什么节日,干吗出去吃呀,把钱省下来,给咱将来的院子多添几盆你最爱的茶花。
然而省下的钱,并没有变成院子的面积,也没有变成名贵的花,它们都被送进了银行,变成一纸债单——他们如愿当上房奴了。
这样,他们的第一步目标就算完成了,可是第二步却迟迟完成不了。说不准是谁的原因,也许是他缺乏锻炼造成的,也许是她太过劳累的缘故,总之就是怀不上孩子。
现在看来,这倒是件好事,世界末日到来时也少个牵挂。他们把约定提前了,短短的三个月内,他们把三十年后要做的事,做了个遍,在小院子里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
然而她的世界末日最终却没有来。医生说,她的癌细胞居然没再扩散了,真是奇迹。
他的世界末日也没有来。她没事,他也就用不上偷偷藏着的那瓶安眠药了。
他们开了香槟庆祝,她与他并排躺在院子中央,被她亲手种的花环绕着,银色的月光披在他们脸上,他久久凝视着她的脸,就像读书时那样。
我们又得重新开始奋斗了。他说。
嗯,重新开始吧。她温顺地附和。
桃花正妖娆,水仙花也不装蒜了,没有花盆护着的山茶花顽强地爆了蕾……院子正是最美的时候。可是他们却没看见。从医院检查回来的第二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回城里了,他们唯一带走的是那条小狗,直到现在它还是会傻傻地追着自己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