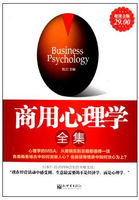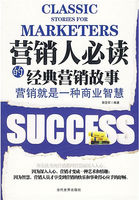天已大亮,太阳由宫中高塔一侧升起,这寒气也被暖阳冲散。
木苍儿听她这句,想她是因没能嫁与太子神伤,劝慰道:“你可懂得,皇家家事与朝政牵连,嫁为君王枕畔也并非完全好事。”
暮西暇从未羡慕一朝入宫为妃,今后扶摇直上,那与她来说并无用处。
于她最为重要的都已失去,所以无论如何过活都是一样。
“我也懂得。”暮西暇浅浅一笑,而周身疲倦,只想回内寝休息,“你我快些回去吧,我很累了。”抬手揉了揉眼睛。
木苍儿见她如此没再多言,挽过她手臂朝尚寝局方向走去。
“只怕今日宫中便会大乱起来。”暮西暇锦鞋踏在这宫廊地砖之上,她步步稳当悠悠一声。
木苍儿与她互相搀扶,行至尚寝局宫门之前,踏过门槛。
当今圣上驾崩,今日宫中必将人心惶惶,暮西暇能够想见,新帝便将即位,如此这大唐王朝易主,将会改变众多人的命运。
暮西暇她仰头看去,这片天空最远处青山一侧,太阳正朝天空正中升去。
能亲眼见证这从前只有在古装剧当中看到的桥段,也算一大收获。
而她更清楚的知道,她此时身处于怎样的角色当中,这一切于一个小小宫婢来说并无用处。
她还如蝼蚁一般要辛苦过活。
所以还是保住这副身子,至少不要让身体的虚弱使这日子更加难捱。
她不过是顺随着暮西暇的人生,替她度过罢了,所以对这一生并无过高追求。
暮西暇与木苍儿才至内寝门前,便听得燥燥一阵人声,她两人驻足看去。
之间崔尚宫疾步朝外而去,与身旁两名随行女官碎碎念道:“昨夜至飞霜殿执勤是何人?为何本宫在此刻才知晓圣上西去?”
“圣上宾天传至掖庭宫中才一刻钟,尚宫何须自责。”
而暮西暇两人看去,只见得尚寝局如此,而其他五局二十四司,乃至宫中各部又是如何乱象。
只怕今日她两人也得不来清闲,暮西暇实在乏了,双腿一软险些栽了下去,幸好木苍儿在身旁搀扶,“你啊,还关心我身体不适,竟不知你自身这般娇弱,快些回去睡下吧。”
木苍儿嗔了句,便与暮西暇一同进入内寝去了。
今日大早,由飞霜殿外礼监传报,那一声声接连传报之声,扩散至唐宫各处,此后人人皆是朝飞霜殿而去。
天渐渐清明起来,那早起阴霾此时已被日光驱散。
金光高檐,层层岩石堆砌而成石阶,飞霜殿内。
殿内静若死水,正黄纹龙幔帐,铜铸香炉,那袅袅檀香飘飞至寝殿高柱。
苍寞寒他与一众人等跪于床榻一旁,他此时仍是一身红服,昨夜大婚身上喜服还未换下,宿醉才醒,便得知他父皇驾崩。
如此这事一件接连一件而来,他还未回神,便已奔至飞霜殿守孝了。
他身后是服侍先帝日常起居的宫人奴仆,这飞霜殿内尽是啼哭之声。
而于苍寞寒,于这殿中的众人在本心看来,先帝逝世,对何人都无真正悲伤。
而唯一为那已断了气息,身子瘫软正平躺于锦绣纹龙图样床褥之上的垂暮老者忠心者,也只有昔日为他身旁躬身照料,卑贱不堪那内监几人而已。
床榻一旁,一正黄华服,头冠之上尽为华丽珠饰那妇人伏于那尸身之上大哭不已,她正是先帝正宫皇后,未央主位之人。
“皇后娘娘莫太伤怀,保重凤体啊。”一旁内监劝阻道。
苍寞寒已见惯这些场面,他此时正在未能与心爱之人成婚当中伤怀,至于他生身之父,当今圣上死活却还顾不得。
他的神经早已麻木,死去那人不过是位铁血帝王,苍寞寒极少能够在脑海当中回忆起有关与他的温情片段,在他印象当中,这位父亲他冷血无情。
而多年来,苍寞寒仰起头来,眼神空洞看向床榻那处,正哀哀垂泪他的母后,多年来,他的父亲独宠惠贵妃,将他母后冷落。
也幸好他早已身在太子之位,不然只怕连承继大统的资格也被惠贵妃母子夺去。
“母后,保重身体。”苍寞寒轻轻开启嘴唇安抚道。
此时跪于这处,不过只为尽孝道,他心中感伤众多,而最沉重之伤,便是他那天作姻缘作废。
只有他自身才知,他是多么痴恋暮西暇那女子,无论她有何种缺陷都可接受。
偏偏,那冷血父亲亲手将他姻缘斩断,他心中愤慨却又无能为力。
在安抚一句过后,他只觉身体疲惫无力,慢慢瘫坐下来,单手撑在地面。
身后婢女见他似是不妥,忙挪过膝盖上前拥住他的身子,“太子殿下……”
苍寞寒他昨夜大醉,这一清早便匆匆赶来飞霜殿,虽身体不适却仍在强撑。
摆手沉声道:“无碍。”
而皇后见他似露出体虚之兆,只稍稍瞧了他一眼,便将眼神转过,哀声道:“圣上仙逝,本宫心哀,而宫中常来运转不可断,月前早已为陛下备下寿材用度,如此便尽快发丧吧。”
皇后她眼帘低下盯于地砖一点,她母子已在当下这位子之上,只要那人一去,她二人便可承继大统之位,于她心中,那人死与活之间,仍是更偏向前者。
殿内几人寥寥几语,此时听得殿外礼监报声,“惠贵妃到——”
她怎在此时赶来?皇后听闻报声,即刻于塌上起身,与身旁内监喝道:“本宫有令,不准闲人入陛下寝室,快些将惠贵妃请出。”
皇后她只是怕惠贵妃此时来此,便会威胁她母子二人,近年来,圣上待四皇子不薄,而又偏宠惠贵妃,皇后她心中一向畏惧,而此时却心中安定许多。
好在那人他逝世突然,方才听宫人道,‘发觉圣上归天之时在黎明,而那时圣上龙体已稍稍冷了下去’,上天竟然连他将心中所愿说出的时机都未留下,便急着将他的命勾去,想到此处皇后嘴角稍稍露出笑意,而后长袖抬起拂于面上。
内监听言便躬身朝殿外而去。
皇后将面上泪痕拂去,而后至苍寞寒身旁,扶住他双臂将他拉起,“皇儿是否身子不适?”
苍寞寒他腰间发紧,而眼底因昨夜未能好生休息显出乌青颜色。
他只闭口吐气,慢慢摇头,“母后放心,我无碍。”
久居宫中,他更知此时为重中之重,不可有一丝懈怠,所以即便强撑,也要忍过这一时。
而飞霜殿外。
年馨儿本是随苍寞寒而来,行至此处却不准她一同进入,便只在殿外跪拜。
此时惠贵妃前来,她一身素裹,早起听闻圣上仙逝,便连珠饰也未装扮在身急切赶来。
而她却不可进殿,被殿外侍卫两只长枪交叉挡住,只得止步在此。
内监应皇后之令而来,至惠贵妃身前俯首一拜,“惠贵妃不可入殿,若为圣上尽心便在殿外守礼。”
“本宫只想送圣上最后一程,圣上生前与本宫情谊深厚,只想得见一面,到底何人阻我。”她戚戚哀哀将话说出。
而最后那句“何人阻我”便是对皇后成见颇重,她年老不得圣上荣宠,却独享皇后之位,而惠贵妃她自身因圣上荣宠,将将便可与皇后之位比肩,当下圣上突然病逝,想来该有话留给她母子二人。
惠贵妃只怕在圣上归天之后,要受皇后与太子他二人仇视。
其实若论太子,他有礼谦和,惠贵妃倒是对他无过多忌讳,只是皇后心狠,要她十分心惧。
内监只得躬身应道:“惠贵妃若心中有疑,不妨与奴才问来,奴才日夜伴于陛下身侧,若有关贵妃必定知无不言。”
而这内监更是通达这宫中之道,他亦早早领悟圣上之意,在圣上临终前夕,曾下令将雍亲王等一众臣等扣押刑部,又将太子婚约除去,而反观待四皇子,交付兵权,待他母妃惠贵妃宠爱有加。
这其中之意,此内监心中明白几分。
惠贵妃此时奔来这飞霜殿,正是此意。
她忙将素面之上泪痕抹去,双手交合在身前,与那内监俯首作礼,好声相问,“还请公公告之,陛下是否留有只言片语与我。”
他两人正低声交谈,惠贵妃拂袖擦泪,而殿外旁人皆不知所说何事。
此时皇后带苍绪嵇从内殿走出,苍绪嵇他实在身子不快,皇后不忍他再辛苦,便将他送出。
才至殿门之前,见得那内监与惠贵妃絮语些什么,皇后顿时柳眉倒竖,大声喝道:“无礼,你等后宫妃嫔与内监亲近过分,可有何事?”
听得这一声大喝,两人才发觉皇后到此,内监只管俯首跪地。
而惠贵妃可是等见皇后一面多时,她不准自身得见圣上最后一面,当真在还未稳坐太后之位便以将宫中实权握在手中。
连月来,圣上早已露出改立太子之意,惠贵妃猜想圣上必定留有遗言,她母子屈居人下多年,不该得此为止啊。
“皇后娘娘,嫔妾可否入殿与陛下相见?”惠贵妃身姿直立与皇后问道。
圣上病逝,莫非她心中哀痛竟连平常宫中礼数都忘做了吗。
皇后见此心恼,与她厉声斥责道:“惠贵妃与本宫应话,竟然全然不顾礼道,是将本宫不放在眼里了吗。”
听她此言,惠贵妃才补上一礼,而后立直身子与她问道:“皇后娘娘可否准许嫔妾与圣上一见。”
宫中大丧,皇后为后宫之首,她自有权治理后宫之事,而前臣不论,后妃行事她自然有权管制。
“圣上已去,惠贵妃不便再前往叨扰,你且只管保重身体,送陛下一程便是。”皇后平声应道。
苍寞寒由皇后搀扶,而他心中却冷静清明的很,惠贵妃她与母亲相争,不外乎为着一句‘母凭子贵’罢了,而他此时实在无心相争。
他亦知晓,他那生父近些年来待他并不如四皇子,而同为兄弟,苍寞寒也不愿与苍绪嵇相争。
他兄弟二人心照不宣,只听凭父亲心意,而他们母亲却僵持之中寸步不让。
见惠贵妃脸色铁寒,苍绪嵇只想好声劝慰,开口道:“惠娘娘若是体弱无力守礼,便也不必如一般在殿外苦熬,惠娘娘伴父皇多年,劳苦功高,儿臣亦感念在心。”
他话中句句温良在理,只面对苍寞寒,惠贵妃便无话可说,眼见他仍着一身婚服,想来昨夜春宵未过便遇寒霜,他亦是不好过。
惠贵妃深深呼吸,转眼看向皇后,她话还未与她说个明白,圣上之意,必要弄个明白,以免耽误前程。
“嫔妾可否与皇后娘娘相商一番,圣上在时,嫔妾便小小着手后宫事宜,只愿能助皇后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