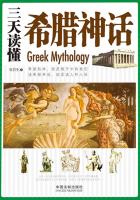孙御医悄悄抹了一把汗,正想着一旦写下凭证,将来被袁霍知晓他有这样一笔财产,势必会彻查到底。还没来得及推诿,宝路已将笔墨送到孙御医面前。他悄悄抬眼,见海弦一脸严肃,只觉得此时已是进退两难。他狠狠咬了咬牙,接过笔写下了一份凭证。
海弦看了看凭证,笑道:“孙御医医术精湛,自是该赏。”
宝路微微一笑,将一包金锞子放到孙御医手中,引着他出了殿门。孙御医走了几步,又忽然定住步子,朝海弦深深一揖。
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褚御医和院判先后来栖凰宫请平安脉。海弦用同样的法子,恩威并施,不仅握住了几人的把柄,也得了一笔不菲的“闲钱”。她点算了一番,统共两千八百两银子,汝明礼倒也算出手阔绰了。她盘算着等请示过袁霍后,就把这笔钱套做现银,悄悄买一批粮草,送去边境。
这一日穆圳川也来走了个过场,海弦将先前从香炉里拨出的香料交给穆圳川,说道:“你回去替我验一验这里头的成份。”
“敢问公主,这些香料是从哪里来的?”他仔细闻了闻,倒也不觉得有何异样。
海弦脸上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只是道:“过些日子,我打算出宫一趟,只是如今汝明礼在宫中当值,倒也不似先前那般容易了。”
穆圳川道:“宫里有一批药材是去年的存货,依照规矩应当送出宫去廉价卖给医馆。明日此事由圳川督办,公主若是不介意药味混杂,倒是不妨一试。”
海弦笑道:“只要能够助我出宫,别的都算不得什么。”
次日天未亮,海弦就穿上“药童”服,牵着板车,车上累满了草药,穆圳川坐在板车一角,看着海弦吃力地拉着车,轻声道:“等到了宫外,圳川便同公主调换位置。”
海弦摇了摇头,向守宫门的侍卫递上了腰牌,神色从容。侍卫们不疑有他,倒也没有严家盘查,便放行了。
到了宫外,穆圳川跳下板车,打算同海弦调换位置。海弦却道:“我坚持得了。”
穆圳川知道,海弦是怕被汝明礼发觉了异样,反倒节外生枝。然而他坐在上头,终究如坐针毡,干脆跳下来走道她面前道:“这般磨磨蹭蹭的,天黑了也回不了宫。”说着便拽过板车的其中一根手柄,同她一道拉着赶路。
穆圳川小声道:“昨天微臣已经验过香料,表面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这里头其中有一味香料同汝明礼调配给陛下的一模一样。”
海弦只是微微颔首,并没有再细问。
穆圳川原打算问一问香料的来历,见她神情失落,倒也不好再问。
两人把草药分批卖往各个医馆后,海弦又跟着穆圳川去了京师第一酒楼。如今梁谷已从跑堂做到了掌柜,梁粟也只需负责贵宾席,如此一来,对海弦倒是十分有利。
穆圳川一进门就要了一间贵宾席,梁粟飞快地迎上来,将两人一路迎进贵宾席。梁粟送上菜牌,穆圳川却把菜牌交给了海弦。梁粟侧头一看,坐在面前的人虽做了药童打扮,但容色清丽脱俗,那眉眼十分熟悉。这人不正是宸永公主吗?他正要跪地请安,海弦先一步将他拦下来,随后指着菜牌上的几个菜道:“咕咾肉、铜锣烧、莼菜羹。”
梁粟道:“这些并非酒楼里的特色菜,公主不妨试一试……”
“你将这些菜拿食盒装了,速速送去点兵库,就说是一名叫阿库的人在酒楼里定的菜。”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一封信,“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将这封信送到他手上。他若问起是谁让你送的信,你只说是酒楼里一位客人托他送的。”
梁粟点了点头,又听海弦随意点了两道菜,便带着信赶忙去了。
穆圳川道:“有句话不知圳川当讲不当讲。”
海弦笑道:“你是想说,阿库如今在为汝明礼办事,我不该冒然接近他。”
穆圳川点了点头。
“这封信是甫翟出征前拖我转交给阿库的,他嘱咐过我不得看信上的内容。我并不知晓甫翟在心中写了什么,但是既然他托我带信给阿库,他势必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或许阿库并没有投靠汝明礼也未可知。”
穆圳川道:“梁粟将食盒送去,怕是他未必肯收。”
海弦笑道:“他若是见过那三道菜,必然会收下的。”
穆圳川回想着那三道菜,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又看了看菜牌,那三道菜打头的三个字合起来读音不正是随了“古桐村”吗?他倒是听宫中人提过一嘴,故皇后本是来自古桐村,倒不知阿库同它有何缘故。
正说着话,有跑堂送上了几道菜,却不是梁粟,看来梁粟已经出发了。
两人吃完饭菜,便坐在包间里焦急地等着梁粟回来。外头跑堂来训问了两三次是否要添茶水,可见是想“赶”他们走了。穆圳川索性点了一壶最贵的茶,跑堂终于没再过来催促。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梁粟才打了帘子进来。海弦忙问道:“他可有说什么?”
梁粟道:“只问了派我送食盒的人是男是女,再没有旁的话了。”
海弦微微有些失落,点点头对穆圳川道:“今日出门忘了带银两,倒是要劳你破费了。”
穆圳川微微一笑:“您只管吃喝尽兴便是了。”
安然回到宫里,海弦终于收到了甫翟寄来的平安信,她欢天喜地的拆了信,虽只寥寥数语,却是字字如千金。海弦把信笺仔细收好,又写了一封回信,也只写了“珍重,勿念”四个字,从烛台上摘下一支蜡烛,沿着封口慢慢滴出一排烛泪,直到烛泪风干,才唤来崔屏,说道:“一会儿把这封信交给采买太监,命他们明日一早寄出。”
崔屏正要去办,海弦却道:“晚些时候也无妨,并不是什么急信。”她微微一怔,又听海弦道,“陪我走一走吧。”
两人沿着御花园一路走着,海弦时不时说起一些关于含芷和鹊儿的事,或伤感、或惋惜或不舍。崔屏只是安静听着,一言不发,海弦忽然道:“含芷若是还在这里该多好,你们一静一动,有些地方却又十分相像。”
崔屏咂咂嘴,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却只是不动声色地跟在她身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掌灯太监已经开始一路燃灯,海弦顺着掌灯太监点起的灯笼慢慢走去,见两位公嫔正坐在亭子里剪窗纸。圆桌上点着一只素纱灯,火影幢幢,她恍惚想起了那年同含芷一道剪窗纸,她嫌弃自己笨拙,含芷却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
海弦忽然神色一动,对崔屏道:“你去内务府另一些彩纸来。”说着先行回了栖凰宫。海弦把彩纸堆满圆桌,从自己宫里找了三四名宫女一起围在圆桌边剪纸。
毕竟同座的人是公主,几名宫女遂都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握着剪刀的手也是僵硬无比,落在位置上如坐针毡。海弦原本想把自己箭的窗纸展开给她们看,见她们一直拘束着,于是扫兴地叹了口气,干脆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管自己埋头剪着。
只有崔屏没有半分拘束,在靠近窗子边的位子前坐下来。手外头大雪纷扬,屋里却是温暖和煦,炭炉子里的银炭换了一次又一次,就连堆在案上的彩纸都含着丝丝温度。崔屏见海弦不说话,便也安静地侍弄着手里的彩纸,殿里安静异常,唯有剪子唰唰的声音响在耳边。
崔屏落剪子的动作极其娴熟,未多时,面前那一叠彩纸都已被剪成了各色花样。她选了一些样子最好看的花样子往窗户上贴,窗上融了一层雪珠子,因此彩纸刚覆在纱窗上,便牢牢地粘在上面,浑然天成。
海弦手指一滞,放下剪子看着窗户上的“松竹贺岁”问道:“你学窗纸的功夫是谁教的?”
崔屏微微一笑,说道:“回公主,是奴婢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教的。”
“从前我有一个好姐妹也有如你一般的手艺,我剪纸的功夫就是她教的,可惜我脑子笨,连她的三成也学不到。”海弦悠悠一叹,有些怅然地揭下贴在窗户上的剪纸,说道,“剪个和合二仙吧,你会吗?”
崔屏的笑容忽然僵硬在脸上,似是在等她说下去,不防她忽然沉默下来,遂只得点头说道说道:“奴婢会,只是剪得不好看。”停一停,她又问,“公主说的那个姐妹是从前在栖凰宫的含芷姑娘吗?”
海弦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崔屏抿了抿嘴,迟疑着问道:“不知含芷姑娘因何走得早?”
海弦定定地看着她,她顿时有些守住无措起来,像个做错了事被长辈发现的孩子,脸上一忽儿青一忽儿白,目光躲闪着。海弦突然朝大家摆了摆手道:“你们先退下去,我有些话要同崔屏说。”
崔屏手指一颤,拈在手里的一对和合二仙在剪子下生生碎成了两半。
宝路领着众人退出大殿,海弦微微笑道:“你无须惊惶,坐下来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