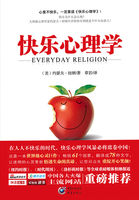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马贵民
两个少先队员接过东西向我敬了个礼,又环顾了围观的10多个小伙伴,含着泪郑重地说:“有他们作证,我们以红领巾向您保证:钱我们交给老师,易拉罐和酒瓶交给小石头!”
列车过了宝鸡,驶入崇山峻岭,开始进出于难以计数的一个又一个山洞。
嗬!如同穿行在明暗交替的阴阳界。
同卧厢里的另外5位旅伴,行业不同,各有特点。对面下铺,是位中途上车的苏北女律师。她身材苗条,柳眉入鬓,凤眼明眸,翘鼻头下却是一张不小的嘴巴。
据她讲,生来原本为樱桃小嘴,5年辩坛的律师生涯,竟将小嘴侃大了。她发乌似漆,面白如玉,再衬上那件薄如蝉翼的连衣裙,真乃飘飘欲仙了。在过路车连座号也没有的情况下,她竟凭借善侃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列车长那里侃来张上铺票。而后又将下铺的那位中年黑胖老板,侃得晕晕乎乎跟她调了铺。
黑胖老板在成都经营烟酒批发,肿眼泡,眯眯眼,大腹便便。胖得流油的老板跟窈窕女律师挨肩坐在下铺窗口,显得极不协调。他的脚下,放着一扎青岛啤酒。
他以酒代茶,时辰不大小桌上就堆了8个空酒瓶。该是碍眼了吧?他双手掬起几个瓶嘴儿,抬臂欲抛向窗外,并说:
“诸位听响了,我要投掷‘集束手榴弹’嘞!”
“别扔。”女律师突然伸出玉手拽住了黑胖老板的粗胳膊,柔声道,“留给我嘛。”
此举,使我愕然了。几个废弃的空酒瓶,对这位潇洒女子有什么用呢?
坐在我身边的中上铺老妇跟她的一对孪生外孙女是西安人。她年过七旬,善眉善眼,满脸尽是笑纹儿,使人联想到庙中的弥勒佛。孪生姊妹同为一张苹果脸,模样儿花朵一般。她俩在姥姥身边长大,已上五年级了。此次远行成都,是姥姥送她们到父母身边去上学。此时,她们仨也向女律师投去了疑惑的目光:她该不是有病吧?
愕然不已的众人里,当属大腹便便的黑胖老板了。他掬瓶嘴的手“定格”悬在半空,眯缝着肿眼泡儿回不过神来。该是猛悟到一个空酒瓶可换回3角钱的价值吧?他弯过胳膊将瓶们重新放回小桌上,皱着眉头说:
“你咋子么?拿瓶子卖啷咯?”
老奶奶似乎也回过了味,她拢了拢白发,以教训的口气对外孙女说:
“学律师阿姨,拾荒哩。”
孪生姊妹亦将她们喝过的饮料罐,整齐地码在铺头上。
黑胖老板斜了眼几上的空瓶,又拍了拍自己吊在腹部的老板兜儿说:
“你长得这么妖冶,短钱吗啷咯?要好多?老子给嘛。”
“不,你猜错了。”女律师拢了拢小桌上的瓶们,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我有用途。”
是何用途?
谜一样的女律师,真令人捉摸不透。
车至秦岭站,如同总统专列光临,我们均置于欢迎的花丛中。身挂补丁的男女山里娃,手擎叫不出名堂的红、黄各色花束,蜂拥至列车窗口,恳求声不绝于耳——“叔叔,花换啤酒瓶!”
“阿姨,花换饮料罐儿!”
“爷爷,帮我找一个空酒瓶吧。”
……此时,我才解开女律师收拢空酒瓶之谜了。只见她通过车窗,将瓶们分递到车下。孩子们又将一枝枝野花,回敬给了女律师。她弯回胳膊,将手里的野花插入茶杯。沐浴了茶汁的野花,顷刻分外艳丽,幽香醉人。
黑胖老板没了空酒瓶,急得拿出两瓶啤酒换回一把野花,咧着嘴也插进了女律师的茶杯里。
我因不喝啤酒和饮料,就满车厢找了两个矿泉水瓶子往下递,却被车下的孩子回绝了:“这个没人收。”自然,我亦未换回野花了。
花朵般的孪生姐妹,竟捧着几个饮料罐跳下车,送给了远离车窗的一个羞涩的小弟弟。当返回车上时,她俩哭了。
因为呵,她俩在车下听人说,秦岭属陕南贫困山区,好多同龄人都失学了。车下山里娃的学杂费,大都是用野花换来的。又听说,远离车窗的小弟弟叫小石头,他和妈妈被在西安打工的爸爸抛弃,妈妈哭瞎眼已卧床不起了。他采野花换瓶子和易拉罐,不仅为支付学费,还要供养卧床的妈妈……小姐妹俩的叙说,使在场的人都沉默了。感情颇丰的女律师,伤心得两眼湿润,她含泪说:
“‘希望工程’就在眼前,我建议:咱们为这个待救的小石头做点实事吧。”
黑胖老板慷慨解囊,率先拿出了100元。而后,你10元、他5元地凑了200多元。
然而,在列车启动的瞬间,当女律师招呼过小石头要给钱时,却被车下的孩子断然回绝了。他说:
“我妈说过,不许平白无故收别人的钱。”
多么倔强的小石头!多么可爱的山里娃!
女律师在分还这笔未赞助出去的款项时,落泪了。
老奶奶接钱时,眼圈儿都哭红了。
我这个泪不轻弹的晋南汉,也掉泪了。
孪生姊妹俩,更抽泣得成了泪人儿。
“后悔死了么,”黑胖老板抬手抹了把泪,追悔莫及地说,“老子打牙祭胡乱花甩的大把子钱,在这儿盖座‘希望小学’都有余嘛。”
我沉默不语,却在心里说:返程再路过秦岭站,我要为小石头捡回一大堆空酒瓶和易拉罐……谁又能想到呀,当我在成都办完事重返秦岭站,且拎着一大塑料袋空酒瓶和易拉罐跳下车,花丛中却找不到那个羞涩的小石头。据车下知情的孩子们讲:小石头的妈妈殁了,他也失学了。
我听罢木然呆愣,心里一片空白。开车在即,我将沉甸甸的塑料袋交给花丛中的两位少先队员,又随手掏出仅剩的80元递过去说:
“袋子里的东西你俩分了。这点钱,代我转交给小石头的老师,拜托他别让孩子失了学。”
两个少先队员接过东西向我敬了个礼,又环顾了围观的10多个小伙伴,含着泪郑重地说:“有他们作证,我们以红领巾向您保证:钱我们交给老师,易拉罐和酒瓶交给小石头!”
在返程列车“咣当”的启动声中,我跟车下的山里娃挥手告别后,心里顿觉空落落。
我能为可怜的小石头再做点什么?
我又能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美文欣赏
一群与贫困搏斗的孩子,几位心地善良的好心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性之歌。在你享受着眼前无忧生活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远方那些在贫穷与困苦中挣扎的孩子们?你是否问过自己: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第六枚戒指
邓康延
他长久地审视着我,渐渐,一丝十分柔和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但我能肯定,你在这里会干得不错。我可以为你祝福吗?”
我17岁那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母亲喜忧参半:家有了指望,但又为我的毛手毛脚操心。
工作对我们孤女寡母太重要了。我中学毕业后,正赶上大萧条,一个差事会有几十、上百的失业者争夺。多亏母亲为我的面试赶做了一身整洁的海军蓝,才得以被一家珠宝行录用。
在商店的一楼,我干得挺欢。第一周,受到领班的称赞。第二周,我被破例调往楼上。
楼上珠宝部是商场的心脏,专营珍宝和高级饰物。整层楼排列着气派很大的展品橱窗,还有两个专供客人看购珠宝的小屋。
我的职责是管理商品,在经理室外帮忙和传接电话。要干得热情、敏捷,还要防盗。
圣诞节临近,工作日趋紧张、兴奋,我也忧虑起来。忙季过后我就得走,回复往昔可怕的奔波日子。然而幸运之神却来临了。一天下午,我听到经理对总管说:
“艾艾那个小管理员很不赖,我挺喜欢她那个快活劲。”
我竖起耳朵听到总管回答:“是,这姑娘挺不错,我正有留下她的意思。”
这让我回家时蹦跳了一路。
翌日,我冒雨赶到店里。距圣诞节只剩下一周时间,全店人员都绷紧了神经。
我整理戒指时,瞥见那边柜台前站着一个男人,高个头,白皮肤,约莫30岁。但他脸上的表情吓我一跳,他几乎就是这不幸年代的贫民缩影。一脸的悲伤、愤怒、惶惑,有如陷入了他人置下的陷阱。剪裁得体的法兰绒服装已是褴褛不堪,诉说着主人的遭遇。他用一种永不可企的绝望眼神,盯着那些宝石。
我感到因为同情而涌起的悲伤。但我还牵挂着其他事,很快就把他忘了。
小屋打来要货电话,我进橱窗最里边取珠宝。当我急急地挪出来时,衣袖碰落了一个碟子,6枚精美绝伦的钻石戒指滚落到地上。
总管先生激动不安地匆匆赶来,但没有发火。他知道我这一天是在怎样干的,只是说:“快捡起来,放回碟子。”
我弯着腰,几欲泪下地说:“先生,小屋还有顾客等着呢。”
“去那边,孩子。你快捡起这些戒指!”
我用近乎狂乱的速度捡回5枚戒指,但怎么也找不到第6枚。我寻思它是滚落到橱窗的夹缝里,就跑过去细细搜寻。没有!我突然瞥见那个高个男子正向出口走去。顿时,我领悟到戒指在哪儿了。碟子打翻的一瞬,他正在场!
当他的手就要触及门柄时,我叫道:
“对不起,先生。”
他转过身来。漫长的一分钟里,我们无言对视。我祈祷着,不管怎样,让我挽回我在商店里的未来吧。跌落戒指是很糟,但终会被忘却;要是丢掉一枚,那简直不敢想象!而此刻,我若表现得急躁——即便我判断正确——也终会使我所有美好的希望化为泡影。
“什么事?”他问。他的脸肌在抽搐。
我确信我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我能感觉得出他进店不是想偷什么。他也许想得到片刻温暖和感受一下美好的时辰。我深知什么是苦寻工作而又一无所获。我还能想象得出这个可怜人是以怎样的心情看这社会:一些人在购买奢侈品,而他一家老小却无以果腹。
“什么事?”他再次问道。猛地,我知道该怎样作答了。母亲说过,大多数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我不认为这个男人会伤害我。我望望窗外,此时大雾弥漫。
“这是我头回工作。现在找个事儿做很难,是不是?”我说。
他长久地审视着我,渐渐,一丝十分柔和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但我能肯定,你在这里会干得不错。我可以为你祝福吗?”
他伸出手与我相握。我低声地说:“也祝您好运。”他推开店门,消失在浓雾里。
我慢慢转过身,将手中的第6枚戒指放回了原处。
美文欣赏
心灵是个花园,善与恶皆是种子。提供爱的土壤和肥料,善的种子便会发芽、生长,反之,就会滋生恶的杂草。善与恶在第六枚戒指上几经较量走入天堂还是踏入地狱,全在我们一念之间的选择。
火车上的姑娘
[英国]拉斯金邦德
“我记不得了,”他回答道,听起来真使人迷惑。“我注意的是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头发。她有一双十分美丽的眼睛,可非常遗憾,对她来说,这双眼睛没有任何用处——她是一位全瞎的姑娘。难道你没注意到?”
我上了开往拉赫那的直达火车,在车上找到了一个包厢。不一会,车上来了一位姑娘。有一对夫妻前来给姑娘送行,很可能就是这姑娘的父母亲。他们似乎很为姑娘的旅途坎坷而感到担忧,那位妇女仔细地告诉姑娘该把东西放在哪里,什么时候不该把头伸出窗外和怎样避开跟陌生人谈话。
由于我那时已经双目失明,所以我无法告诉你这位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拖鞋底拍击脚后跟的声音使我知道,姑娘穿着一双拖鞋,还有,我很喜欢她的嗓音。
“你是去德赫拉墩吗?”当火车徐徐离站的时候,我问这位姑娘。
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坐在暗处,因为我感到我的声音使姑娘吃了一惊。她惊呼一声,说道:“我不知道这儿还有人。”
是啊,对那些眼睛好的人来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看不到就在眼前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要观察的事物太多的缘故吧。而那些失明者,却常常能以他们其余的感觉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判断出眼前的一切。
“我最初也没看到你,”我说道,“但我听到了你进来的声音。”我不清楚,我怎样才能做到不让她看出我是个瞎子。我认为,只要我坐在位置上不动的话,做到这一点还不是十分困难的。
“我去沙哈伦泊尔,”姑娘回答道。“我姨妈会到车站接我的。你上哪儿?”
“先去德赫拉墩,然后再到莫苏里。”
“啊,你真幸运!但愿我也是去莫苏里。我爱那儿的山。尤其在十月里的时候,山上的景色真美。”
“是啊,十月份的确是那儿最好的时光,”说着,我又回想起当我还没失明的时候所看到的山上的风景。“满山都开遍了野生的大丽花,阳光和煦迷人。夜晚,你可坐在篝火旁,喝上一口白兰地。大多数的游客都已离去,留下的小路是那样地宁静,宁静得都近乎荒凉了。”
她没出一声,我不知道我的话有没有传到她那边,她会不会把我看做是一个浪漫的傻瓜。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窗外是什么样!”我问了一句。
她好像丝毫没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奇怪。她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双眼其实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是,她的回答使我立即消除了内心的不安,“你不能自己看吗!
”她很自然地问道。
我不费劲地顺着座位移到窗前。窗开着,我面朝窗外,装出一副观赏景色的模样。在我心灵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一根根迅速掠过的电线杆。“你是否注意到,”我冒险地问道,“看起来好像是车外的树在移动,而我们则是静坐着!”
“这常常是这样的。”她说。
我把脸由窗口转向姑娘,有一阵子,我们俩谁都没出声。“你的脸长得很有趣,”我评论道。我一下子变得很大胆,不过,这是一种安全的评论:因为很少有姑娘是不喜欢奉承的。
她很愉快地笑了,那是一种清脆而又悦耳的笑声。“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她说道:“我早就厌烦了那些夸我脸蛋长得漂亮的人。”
啊,原来她还真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会儿,我出声地说:“当然,有趣的脸也可以是漂亮的。”
“你很勇敢,”她说,“可你为什么这么拘谨呢?”
“你很快就要下车了!”我很茫然地说出了这句话。
“感谢上帝,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我简直不能忍受这样在火车上旅行两三个小时。”
而我,则宁愿在这里一直坐下去,静静地倾听她的说话。她的嗓音有着山涧流水般的清澈和甜美。她下了火车以后,便会马上忘却我们之间的短暂相遇。可这一切将陪伴着我继续旅行,并在旅行结束后相当的一段时间萦绕在脑海中。
火车的汽笛声响了,车轮改变了原先的声音和节奏。姑娘站了起来,收拾起行李。这时候,我很想知道姑娘的头发是扎成一个发髻,还是松散地披在她的双肩上,或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进站了。车外,到处是搬运工和小贩们的吆喊声。在我们的包厢门口,响起了一个妇女尖细刺耳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姑娘的姨妈吧。
“再见了。”姑娘说道。
她站得离我很近,那样的近,以至我都能闻到从她头发中散发出来的香水味。
我真想抬起手,抚摸一下她的头发,可是,她走了,只有香味还弥漫在车厢里。
车厢门口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混乱。一个男子结巴地嘀咕着抱歉的话,走进我的包厢。然后,门“乓”的一声关上了,整个世界又被隔绝在外面了。我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列车员吹响了哨子,列车又缓缓启动了。
火车在飞驰,车轮在吹唱,车厢在轻微的摇晃中发出吱吱的声响。我找到了窗口,坐在前面,凝视着对我来说是一片黑暗的天空。我又有了一位新的旅伴,又可继续我的游戏了。
“很抱歉,我这个旅伴不如刚才下车的那位姑娘富有吸引力!”这男子说着,设法和我进行对话。
“她是一位挺有意思的姑娘,”我说道,你能否告诉我,那姑娘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