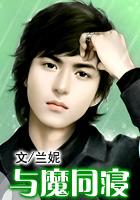是。客人膝盖并得紧紧的,低下脑袋,草帽檐子就要抵到桌面了,是,是自不量力。
承认错误已经晚啰!男主人的瓶口滴下一滴酒,两滴酒,杯口满盈盈的,微微荡漾,像鼓胀的膜。男主人小心地把嘴唇嘬到杯口,吱一声响,接着是一声悠长的惬意的叹。他抹抹嘴巴,看着客人,用中肯的语气说,我看你得病就是因为胡思乱想太多了!你说你们天远地远的,咋会认识呢?
我们是笔友。客人说。
我知道你们是笔友。男主人皱着眉头,端起了那杯酒,悬停在嘴唇边,我的意思是你们左一封信右一封信,有什么意思?
这是个叫客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他还是试图找个理由,嗫嚅着,组织着思绪和言语。
男主人倒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他干掉一杯酒,又倒满一杯,还是满盈盈。看样子他喜欢这样的喝酒方式,一声吱一声叹,两个美好的音节。
我那时候很孤独,一个村子就我一个念书的人。客人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决定用自己的故事来解答男主人的疑惑,因为急于讲述也因为激动,话语就有些乱——
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写信来,只是后来只剩下几个人,他们鼓励我攀登,鼓励我学习,报效祖国……
你就是那么报效的?把自己整进班房里去?男主人嗤了声,露出浅浅的笑,他将一大夹菜塞进嘴里,凶猛地咀嚼,那笑顿时膨胀开来,由黑亮的额头开始灿烂,飞向炫目的天空。
客人慢慢垂下脑袋,目光落在男主人脸上,他没有放弃解释。他说,我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我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我进去是因为……
男主人突然一伸手,亮出巨大的巴掌,那样子像电影里侦察队长突然发现敌情。在发出一声响亮的吞咽声后,男主人慢慢站起来,但是那只巴掌始终耸立,像堵不容逾越的墙,这叫客人很紧张。男主人离开桌子,往前走了几步,巴掌盖在眉头,搭起了凉棚。在男主人前头半步,就是断崖。不过丝毫不用为他担心,他巍然屹立的样子像一棵松。
跳下去了?客人很紧张,揭了帽子,攥在手里。
没有。女主人只打望了一眼就回到了座位上。她搁下拐棍,撑起了伞,一手举伞,一手拿筷子,招呼客人,吃,吃吧。
客人没有心思吃,他坐立不安。
男主人归座,一眼就看见了客人面前的白开水。吃药,你先吃药。
客人摸出药瓶。
男主人对客人的顺从表示满意,他斟满一杯酒,等着要与客人共饮似的。客人的小药片滚到了桌子上。客人去拍,拍住了,却将那杯满盈盈的酒震溢了,一线光亮,沿着桌子蜿蜒。男主人用宽大的手掌截住,慢慢收归,然后用几个指头蘸起来,捋起裤腿,往膝盖上擦抹。等会儿要下水的。他说,接着将杯子里的酒倒了些在手心里,继续擦抹两个膝盖,往小腿肚子上拍。得喂饱它们,要不下水抽筋咋办。
啪啪声停止了。剩余的半杯酒,男主人依然发出了一声清亮透彻的吱和一声豪迈的叹。
客人还在吃药。小白片、小黄片、小灰片……每服下一片,客人都会呆一会儿,接着再捏起一片,仰起脑袋,张大嘴巴,药片悬停一下,准确地掉进喉咙眼儿,啜一口水,脖子一抻。
你吃药的样子倒是优雅呢。男主人意味深长地看了女主人一眼。
最后一片药,客人被呛住了,不厉害,只咳嗽了几声,但是淌出了眼泪。这逗得男主人哈哈大笑。
这笑声叫客人很不高兴,他的眉头都皱到一块儿了。女主人及时地夹过去一筷子菜,要他尝尝,说才吃了药,解解嘴。客人的不悦被这一点客气轻松就化解了,他把那顶草帽戴回到头上,夹起碗中的菜,慢慢嚼着,眼睛从碗里,一点一点移到男主人的脸上,最后落在眼睛里。
你怎么知道她要跳呢?
我就是知道。男主人很得意,看了女主人一眼,我瞄一眼就知道。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住呢?
这里头学问大得很。男主人开始吃菜,大口大口地吃,腮帮子连同颧骨都在动。动得最凶猛的是他的喉结,那一上一下地蹿,像奔跑着一群老鼠。
客人的眼睛始终没离开男主人的脸,目光温和而又固执,这让男主人感到不安。好吧,我告诉你吧。男主人妥协了。他说,要让一个人摆脱自杀的念头,就得让他自杀一次,尝尝死究竟是种什么滋味。根据我的了解,很多投河自杀者,自从被救起来后,从此就怕水了。为此男主人还举了个例子,说有个小伙子,我去救的时候,在水里还精神着呢。于是,我就在一旁闲游,等。等小伙子一口水一口水地喝啊,终于人事不省了,这才上前。小伙子灌得就像只蛤蟆,碰哪里都出水。听说从这以后啊,小伙子连水龙头都不敢动啰!男主人哈哈大笑起来。
女主人探长身子,给男主人倒了杯酒。她没那本事倒得满盈盈的,不过男主人对这样的温情脉脉还是很满意的。他止住笑,将这杯酒倒进嘴里,发出一声叹。然后说,去,你去把那个东西给我拿来。
命令是不容置疑的。
女主人搁下伞,拿过拐棍,像一棵风中的树,晃晃悠悠地去了。
客人眯缝着双眼,看着那座桥。在他的眼中,那座桥一点都不真切,只是一道轮廓。他看不清楚桥有几道孔,有几个墩。他侧耳听了听。引擎声很弱,喇叭鸣放的声音倒还是有些响。他又在眼前竖起一根指头,由远渐近地移动。
你这是干什么?男主人问。
从这个点,到桥那个点,直线距离怕有一千米吧?客人原来在测距。
你咋测的?啥眼水呀?没有,直线距离只有一里不到!男主人像是已经知道了客人的打算,他慢条斯理地斟酒。
从这里步行到桥,要绕好大几个弯呢。客人说。
是啊,这一绕,就得三里半了。男主人嘬着嘴唇,吱了一口。
三里半,跑得最快也得六分钟。五百米,游得最快也要六分钟。再说你都筋疲力尽了,还能救人?数据之下,客人不能不质疑。
老子就是能救!男主人干笑了两声,喝掉那杯酒,这一回他没有感叹。他扭身看着屋里,大声叫嚷道,还没拿出来吗?
女主人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个红红的什么东西,一瘸一拐地过来。近了,客人才看见那是个大大的红簿子,很厚。男主人一把抓过来,抱在怀里,看着客人,你接下来是不是要问我救了多少人?没等客人表态,他一下把红簿子拍在客人跟前,指头笃笃点着,哼哼地笑几声,你自己看,慢慢看!
红簿子有些沉,这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客人的视力。他的视力可真是糟糕透了,双手捧起来,簿子都快挨着鼻尖子了。
十三个!今天这个是第十四个!男主人斟满一杯酒,老样儿的喝法。喝完,杯子往边上一推,站起来,敞开衣衫,走到断崖边,手搭凉棚张望。
客人看清楚了。时间,姓名,受到的奖励,得到的酬谢。还贴着有关此次救人事件的新闻报道,男主人接受鲜花的笑容,接受奖状的骄傲,接受祝酒的惬意……
客人晃晃脑袋,把有些飘散的目光聚集到了一个名字上。是的,女主人的名字,她的名字。他伸出指头,轻轻碰了碰那个名字,火烫了似的,指尖赶紧移向别处。他翻过那页,以为就掩住那个名字。可是,新的一页却是女主人的脸,那张在记忆里出现过千百遍的脸,年轻的脸,没有表情的脸……客人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女主人。他不堪重负般粗重地喘息。他搁下红簿子,掀开草帽,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大汗淋漓。
女主人给客人盛了碗汤,递给他的时候,并不缩回手,而是摊开半个手掌。客人弄不清楚她是要什么。女主人笑笑,点点头。客人明白了,摸出那些药瓶。女主人看看,指着其中一瓶。女主人拿过那个小药瓶,旋开盖子,倒出三片,想想,又倒了两片。她把药片握在手心里,用两根指头旋上盖子,轻轻一抛,药瓶划出个完美的弧线,掉在客人的手中。对此他们都很高兴,都露出了笑容。
快了,就快了。男主人回过身子,看着桌子上的红簿子,问客人,你都看了?
客人点点头。
做何感想?男主人问。
客人想了想,竖起大拇指。
男主人爽朗地大笑起来。
女主人歪着半个身子,给男主人盛满一碗汤,剩下的一点,她倒给了自己。他们三个人都在喝汤。客人的一双眼睛挂在碗沿上,左右转动,看看女主人,看看男主人。男主人的眼睛直视前方,他喝得三心二意,注意力全在那座桥上,他的半个屁股已经离开了凳子,一条腿前迈,一条腿后蹬,随时准备飞奔出去。只有女主人专心,眼睛在汤碗里,小口小口地呷,仔细品着其中的味,不时偏向一边轻轻啐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姜末或者花椒皮儿。
男主人就像被噎住了似的,整个身体突然僵住了。跳了!只听得他嘟哝一声,撂下汤碗,壮硕的身子就像一只巨大的跳跳蛙,噌噌两下,就蹦到了断崖边,趴下身子,手一扬,人就不见了。
客人看得瞠目结舌,屁股不由自主地离开凳子,两腿颤颤地张望。
他装了根消防滑竿。女主人放下汤碗,啐掉一个什么东西,看着客人,轻声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呢?
一阵马达声。从断崖底下驶出一只快艇,翻卷着浪花,奔向桥。就快要接近桥了,快艇突然慢了下来,歪歪扭扭地原地打圈,一圈,两圈,三圈,忽然加速了,只是没有奔向桥,而是往回驶,速度很快,歪歪扭扭的,像一条曲奔的凶猛的蛇。斜刺里去了,撞向了对面的崖壁,轰一声闷响,腾起一股黑烟,接着亮起了火光。
客人慢慢坐回到凳子上,端起汤碗,埋头喝汤。他喝汤的声音很响,嘶嘶的,像忍不住发出的窃笑声。他的额头和脑门全是汗珠,喝完最后一口,他抬头看着女主人。女主人扭着脖子,目光悠远,看着那座桥,和那座桥背后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