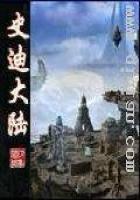王恭见殷确热忱仍同往常,不禁感动地说道:“想我王恭,自打我的祖父王蒙开始,就是晋朝的中流砥柱,他东拼西杀,独当一面,为历代皇帝立下过不朽功勋。由于看不惯朝内许多奸佞大臣的结党营私,公权私用,为自己大捞好处,我这才兴兵讨伐;未承想到了最后,我费力不讨好,未受到朝廷褒扬不说,我自己倒成了大逆不道的人了,我实在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王恭大发牢骚的时候,下人们已将酒菜端到桌子上来。一天多来未吃未喝,滴米未进的王恭,这时实在是被饿极了,他也不再与殷确客套,先端起酒杯,也顾不得饭桌上的礼仪了,一杯接一杯,自顾自的痛饮起来!
在一旁服侍的殷确,看见王恭狼吞虎咽的狼狈相,既感到心痛,又感到好笑!
殷确暗暗想到:“以往,我在你的手下当参军时,你说我工作马虎,做事懈怠,没少往我的头上泼脏水。现在,你自己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肯定是上天为我抱不平,特意安排了这个让我报复你的好机会!”
时间不久,王恭就酒足饭饱,喝了个烂醉如泥!
殷确见时机已到,立即喊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人,吩咐他们说:“王恭是朝廷重犯,现在他自投罗网,正是我等报效朝廷,立大功的机会到了!你们赶紧将他用绳索捆绑,将他送往湖浦尉张大人处,让张大人连夜用小船将王恭送往建康,交到摄政王司马道子爷府上,回来后,我重重有赏!”
听说事后有奖,世上能有几个不见钱眼开的人?下人们为获得奖赏,说干就干,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一切。人们用一块门板,将尚在酒睡中的王恭放在门板上,有四个壮汉抬着,一路朝张湖浦尉处而去。
到了张湖浦尉处,有人向湖浦尉说明事情的原委,又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便离船回府,不提。
张湖浦尉望了一眼仍在熟睡中的王恭,无奈的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说道:“我说王恭啊王恭,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哇!你倚仗自己是皇后妹妹的亲哥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顺眼,还几次起兵妄图推翻朝廷!这回,你不再蹦哒了吧?说实在话,我张某人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无仇,不该干这助纣为虐的事情;可是话又说回来,我端着朝廷的碗,拿着朝廷的俸禄,总不能也像你一样,再来干反对朝廷的事情吧?我把你送往京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一去你是死是活,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简单节说,王恭躺在船舱内,一路忽忽悠悠,就像腾云驾雾一般,在酒力散去之后,小船早已经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建康城了。
第二十九:经过一路晃悠,再经冷风一吹,此时王恭的酒也醒了;他想挣扎着坐起身来,可是手脚都被人用绳索捆绑着,说什么也动弹不了!王恭突然一惊,也终于明白过来:“大事不好!我这是被人给暗算了!”
王恭气愤,王恭懊恼,悔不该去投奔这个白眼狼殷确!可是,无论是气愤与懊恼,现在还有什么用?要知道,世上有包治各种疾病的苦药,就唯独没有这后悔药!事到如今,一切的一切全都晚了!
身居皇宫大院内的司马道子,听说自己所忌恨畏惮的大仇人王恭,已被解压来到建康,喜得他手舞足蹈,对儿子司马元显说道:“王恭这个人,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就骄横得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次好不容易才将他擒获,在他临刑之前,我可要好好的羞辱他一番,以释我的心头之恨!”
司马元显阻止道:“父王,此事万万不可!”
司马道子反问道:“王恭横行多年,我被他羞辱也不只一次两次了,为什么在他临死之前,我去羞辱他一次却不可?”
司马元显解释说:“父亲,你好糊涂!你也不想一想,你是什么身份?你的目的无非是要王恭的性命,岂是羞辱一下就能完事?羞辱,只可满足你面子上的需求,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者,王恭在朝中经营多年,他的亲信爪牙无处不在,你只图一时痛快,如果激怒了这些人,他们群起而攻之,你岂不又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依孩儿之见,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还是不要这样做为好!”
司马道子听完儿子的一番解释后,止不住频频点头,说道:“父亲只求解一时之恨,并未想如此长远,那就依你之见,放弃羞辱王恭的事情。那你再告诉为父,这斩杀王恭的事情,该有谁去执行为好?”
司马元显说道:“现在的朝廷,皇帝低智无能,各路藩王都各显其能,觊觎皇帝宝座的人大有人在,弄得不好,爹的王爷宝座也岌岌可危矣。这杀人的勾当,还是让那些急于想当皇帝的人去做好了!”
司马道子频频颔首,赞同儿子的主张,说道:“你再告诉为父,让谁去完成这个任务为好?”
司马元显将嘴巴附在司马道子的耳朵上,眉飞色舞,连说带比划,把个司马道子说的不住的点头微笑。
最后,司马道子这才说道:“好!好!好!我儿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就按我儿的办法去做好了!”
司马元显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司马师开创晋朝以来,由于家族内部勾心斗角,内斗不已,无论哪个当皇帝,从未出现过杰出皇帝,每位皇帝都是在内斗中无法善终。本家族内本不必说,他们似乎都有资格当皇帝,所以就出现八王之乱之类;在亲戚族内,司马兴男的丈夫桓温也长期觊觎皇帝地位,直到病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叫王法慧,她的哥哥就是王恭,也曾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两次讨伐摄政王司马道子,不但未达到目的,最后还落得身陷囹圄的结果;还有一个人,他袭据继承了父辈爵位称号,更是野心勃勃,梦想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桓温的幼子,现是朝廷权臣的桓玄此人。
桓玄虽然敬佩王恭的为人,也曾公开或暗中支持过王恭发兵攻打建康,认为这在客观上对他有利,但是王恭两次兴兵都未成功,这使桓玄颇感遗憾。尤其这最后一次兴兵,由于刘牢之的半途反戈,使王恭彻底失败,还做了司马道子的阶下囚,看来,王恭的气数是到头了。在接到摄政王司马道子要他监斩王恭的使命时,他还假惺惺的为这位老朋友的惨遭不幸,着实流了数滴眼泪呢。
桓玄前思后想,知道再无办法救王恭了,只好顺水推舟,接下了监斩王恭这道使命。桓玄转念又一想,王恭这个人,向来以刚正出名,自认只有他在朝中一身正气,别人均是奸佞与大逆不道之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司马家族的近亲王爷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他早一日垮台死去,方可解去心头之恨;如果此时桓玄违背了众人意愿,岂不成为王恭的同党?如果我桓玄不将王恭杀掉,我不但从此成为司马家族的仇人,还将遭受司马氏不肖子孙们的嘲讽与围攻。桓玄掂量再三,决定还是接受摄政王司马道子的委派,去做王恭的监斩官。
刑场设在建康城外一个叫做倪塘的地方。刑场四周布满了士兵,也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普通士民。秋风萧瑟,树叶飘零,王恭与他的同党们,都已早早得被绳索捆绑,大多数人面对死亡都被吓得面如土色,不停地抽泣。只有王恭一如往常,他昂首挺胸,谈笑自若,毫无惧色!
王恭问一旁如树干般站立的刽子手:“我王恭是武帝国舅,一生都在为我朝东拼西杀,他司马道子当上了安帝的摄政王,就认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独揽一切了。他今天要是把我给杀了,我敢断定,从此以后,就会朝廷不安,国无宁日!他司马道子是什么东西,难道他真敢杀我?只不过做做样子罢咧!”
刽子手挺身站立,毫无表情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恭又骂道:“今天的监斩官是哪个?为什么快到正午了,他还迟迟不现身?难道他也怕我王恭不成?”
刽子手昂首挺立,面无表情,仍默然无语!
王恭用挑衅的口气,对刽子手说道:“我不但是朝廷命官和重臣,还是当仁不让的国舅爷,难道以愚弄手段取得皇帝信任的人,也敢僭越皇权,动刀杀我不成?你若胆敢举刀杀我,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刽子手昂首挺立,不理不睬,一语不发!
王恭还想再对刽子手说些什么,忽听得人群骚动,人们都不约而同的朝着监斩官坐席方向望去。王恭也抬起头来,远远的朝那个方向看去,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身着朝服的矮个子官员,漫步走到坐席旁,然后稳健的坐了下来。由于距离太远,王恭看不清那位官员的面孔,他心里纳闷,暗想:“他是谁呢?难道他就是来索我性命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