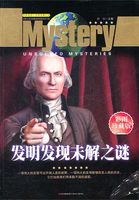像条死狗一般被挂在行刑架上的宋毅风闭口不喝,模样颓废不堪,心气却强硬至极。
柳慢刀将酒壶送回自个嘴边,饮了一口酒后,将那张堆满横肉的脸凑到宋毅风面前阴测测说道,“我的刀法如何?”
宋毅风不答,柳慢刀自顾自说道,“外行人都夸我师兄刀法好,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师兄的刀法实则并不如我。同样是将一个人犯凌迟六千刀,若没有丹药给人犯吊着性命,我师兄行刑的人犯恐怕才割出两千刀就会活活痛死。我就不同,由我来行刑,身体再孱弱的人犯都无须丹药来吊命,说六千刀致才死,我保准能让他六千刀才死。”
喝罢了一壶酒,柳慢刀又开始操刀行刑,因为他的刀法太过诡异,一刀刀刮去宋毅风身上的肉,也没给宋毅风制造出多大痛苦,宋毅风自始至终都没叫唤几声,以致看热闹的人觉得没什么看头,散去不少,有不少不嫌事大的看客好吆喝着要换一个人给宋毅风行刑,不然明日就不来看了。秉公执法的李心安闻言,乱棍将那些好事者全部撵走。
恐惧之中,心力交瘁,又加上柳慢刀割肉的过程实在不痛,宋毅风昏昏欲睡,噩梦连连,也不知睡着了没有,等他醒来时,整条右臂上的血肉已经尽去。
柳慢刀唤上衙差重新提上一壶酒,他含了一口酒在嘴里,喷在宋毅风手臂的白骨上,将白骨上的血水洗净,这才对宋毅风笑道,“你倒是睡得舒坦,可把老子给累死了,每一刀可都是心力活,不容懈怠,不然,你就没这么舒坦。常言道刽子手这个行当不得善终,老子虽然是凌迟人犯的刀手,但与刽子手相差无几,能将你舒舒服服送进阎王殿也算是老子给自己积德,来日能有个善终。”
宋毅风无心听柳慢刀说话,他看了一眼手臂上的森森白骨,随后,目光下移,落在凌迟台上,那些被柳慢刀割下的血肉被胡乱丢在凌迟台上,招来无数蚂蚁,蚂蚁们正争先恐后,将他的血肉一片片抬进蚂蚁窝分食。
如此一幕,让宋毅风悲从中来,以他显赫的身世,完全可以呆在上京逍遥快活,此刻,他无比悔恨当时为何要不听父亲的劝告,一意孤行偏要跟师父来西云地趟这趟浑水,如今倒好,以如此不堪入目的死法命丧洛安城,血肉无存,等洛安城教化司将他仅剩的一具白骨送回上京,交到父亲手里时,也不知父亲该会如何处置。宋毅风不敢细想下去。
柳慢刀扬了扬手,示意今日之刑已经行完,让衙差将宋毅风抬回囚车,送回监牢。
衙差将宋毅风从行刑架上取下,柳慢刀看了他一眼舔着匕首上的血迹说道,“宋公子,明日大爷再来伺候你。”
衙差驾着宋毅风走向囚车,宋毅风一双死羊眼盯着柳慢刀,阴冷说道,“你明知做刽子手不得善终,当初为何还要选择入这一行?”
柳慢刀将匕首上的血迹舔干净后收入腰畔的夹子里,讥笑道,“老子幼时家境平寒,成年后能有个糊口的行当,能养活一家老小就不错了,那还轮得着老子挑三拣四,倒是宋公子你,生而富贵,却不知珍惜,养成一副滥杀如妖的心性,才将自个送上凌迟台。别看老子刮你身上的肉时冷酷残忍,眼睛都不眨一下,实则老子心善得恨,入行的这些年来,除了杀人犯,连鸡都没杀过一只,省吃俭用,还给附近的庙里捐了不少香油钱。”
“不是我要上凌迟台,是你们,是杨铁钢将我送上凌迟台,你们都不得好死。”宋毅风歇斯底里吐着气声吼道。
“自作孽不可活。”柳慢刀冷笑一声,丢下一句话后,走下了凌迟台。
宋毅风半闭着眼睛,眼缝里的光亮如毒蛇,死死盯着柳慢刀的背影,眼角余光却在无意间看到凌迟台下诸多围人中走来了一个人,那人白衣白发白须,甚至连肤色都是诡异的雪白色。
赫然宋毅风将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那个来人身上,眸中光芒大亮,一改方才如死灰般的面色,喜悦着,躁动着,声嘶力竭喊道,“师父,救我啊。”
来人正是宋毅风的师父,春秋四贤之一慕白羊。慕白羊今日早些时候带着泗水刚入洛安城,便听有人在议论什么御史台宋御史之子、天权府教习之徒宋毅风在洛安城犯了命案,教化司总捕头判处宋毅风凌迟六千刀致死,昨日行了一日的刑,今日会继续行刑。
听到这则消息,慕白羊难以置信,以他对宋毅风的了解,宋毅风闹出命案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宋毅风自报家门,洛安城教化司都已经知道宋毅风的身世,竟然还敢判宋毅风凌迟六千刀致死?
小小洛安城教化司已经胆大包天到敢不将春秋朝的御史台放在眼里?敢不将春秋四贤之一放在眼里?
初闻这则消息慕白羊本来并不相信,但入了洛安城一路走来,听到无数人在议论这件事,他深知凡事不可能空穴来风,心下好奇,为了一探究竟,便走到教化司,眼下的结果却令他咋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凌迟台上的人犯双足双手已废,那张被他夸过数次说是生得好看的嘴也已经被刮去,只剩牙槽,听声音舌头都应该被割去了半根。
“这是我的徒儿宋毅风?”望着凌迟台上人不人鬼不鬼的宋毅风,慕白羊就是亲眼见到都不敢相信,直到宋毅风叫他师父,他才确信那就是他的徒儿。
慕白羊一时怒气横生,心中滔天怒火再也无法压制,气得浑身颤抖,白脸上神色霎时凝起一层寒冰,愈加惨白如雪,阴沉的眸子里生起无数风雨,冰冷的气息瞬息之间蔓延周遭,凌迟台下的看客不禁打了个冷颤,随之冻得厉害,哆嗦不断。有些看客随身带着酒壶,见大晴天突然转冷,本想喝口酒暖和身子,扬起酒壶喝酒时却发现,壶中的酒都已凝结成冰。
“是谁敢如此对待我的徒儿。”慕白羊怒吼一声,萧萧声浪席卷八方,周兆的看客被震得人仰马翻。
慕白羊的威声并不针对看客,针对的是凌迟台上台下的十数位衙差,衙差们闻着声浪,抱头捂耳,还没来得及痛呼,便一头栽倒在地,七窍流血,不知生死。
驾着宋毅风的衙差倒下,没有了衙差的支撑,宋毅风也坠向地面,原本相隔十余丈的慕白羊一步而至,将就将栽倒在地的宋毅风稳稳接入怀中。
终于见到了师父,想起这两日经受的折磨,宋毅风鼻涕眼泪横流,情绪激动,又加上只剩半根舌头,他含糊不清说道,“师父,您可算是来救我了,这几日您都去哪了?”
面对这般凄惨模样的徒儿质问,慕白羊不知如何作答。不日之前,他在洛安城与白羊一起看到长岁山有紫霞降世,接人飞升,一人一羊看得惊奇神往。
慕白羊与那头白羊相处多年,白羊能看到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但白羊能通过秘法让他看到白羊看到的东西。
就在有人飞升的那一夜,慕白羊通过白羊的眼睛看到长岁山有人斩出一条长达数千里的剑道直抵西云地。他与白羊心有感应,白羊告诉他,沿着剑道的方向去西云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机缘。
在剑道消失时,慕白羊也没来得及告诉宋毅风他的去向,便立即动身,走向西云地,果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缘,遇到了长生宗尊主九相,得知了西云地将要出世的异物名曰遗世书,并且获悉了遗世书的应召之人是谁,可谓是满载而归。
但归来时,慕白羊却不曾想,他唯一的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