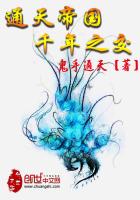锦弦妥协了,为了生活,为了相依为命的哥。
路雪说过:生活就是相互取暖,而爱情,只是青春岁月里的一种病,像高烧一样,始终会退去。
去了郑新的家,他家的房子的确不算小,一百多平,有三个房间,他说买的时候是想接爸妈过来住的,可是房子刚装修好,父亲去世了,母亲就不愿意出门了,说是不习惯南方的生活,可郑新说他知道,母亲之所以不愿意离开老家的那所房子,只是因为那里有她和父亲许多相濡以沫的日子。
她安慰着他,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份不为人知的苦恼,这个高大爽朗的男人也一样,他爱他的父母,想要为家人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然而等他有了这个能力,父亲却不在了。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养而亲不在。
而哥是为了她。他清醒的时候她和他吵架,一而再地离家出走,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和她说话,不能和她交流,她才知道后悔,后悔不该不听哥的话,后悔没有珍惜和哥在一起的涓涓时光。
为了接孟凌东过来,郑新特地把朝阳的那间腾了出来,房间里有明亮的窗,温暖的颜色,和几盆悬挂着绿色植物,比起医院的一片清冷肃然的白,这里要温馨很多,也舒适很多。
她为郑新煮了晚饭,为了表达自己的心中无法表达的感激之情,饭做好之后,两个人在灯下吃饭,郑新吃得很开心,吃完后,心满意足地说:“这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餐饭!”
她心头掠过一丝忧伤,这样的话似曾相识,是哥还是苏楚?穿过往事的影子一点点在心头萦绕,想忘却忘不掉,令人徒增很多的烦恼。
低头收拾碗碟的时候,郑新抢了先,说:“你做了饭,我总该表示一下,要不显得我这个人有多懒似的。”
她帮忙,郑新又怕她不相信似地说:“我刚才说的是真的,出来这些年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的饭,做梦都想吃,有时候到饭店吃饭就点妈妈做过的菜,可不是那种味道,后来就想或许想吃的并不是这道菜,而是这种家常的味道,就像今天一样。”
他的眼睛星星点点地泛着光,有深情的味道,她忙岔开话题,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和你妈一样老?”
郑新局促地解释:“没有哪个意思,你知道的……。”
她其实什么也不知道的,但也没有问,也许并没有答案,并不一定要答案。
又坐了一会,她起身要走,走到门口,郑新突然说:“你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会很累,反正我这儿房间多,等把凌东接过来之后,你也可以考虑搬过来一起住……”
一遇到她瞥过来的目光,郑新慌忙表明立场,呐呐地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让你太辛苦。”
她回绝了,说:“谢谢,我还是住路雪那儿吧。”
他开车送她回,已是冬天,夜凉如水,到路雪家楼下的时候,他把外套给她穿,她想了想,没有拒绝。
郑新的车离开,她转身,隐隐觉得斜刺里有一点猩红的光,空气中弥漫了一种很熟悉的味道,她缓下脚步,思忖着,还是决定不回头看,径直往楼上走。
“就这么不待见我?”苏楚的声音毫无惊喜地响起,听在耳边有些沙哑,像是抽多了烟或是累坏了。
她却没法待见他,如果能够选择,她宁愿从未认识过他,那么她和哥的生活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风波。
她恨自己,更恨他。
她抬步就走,他已一步过来抓住了她的手,他的指尖冰凉,往日光风霁月的面孔和这夜晚的天气一般地清冷肃然,他清瘦了一些,眉头纠结,似是有散不开的抑郁。
她内心脆弱,没有拂开他的勇气,只是虚张声势地说:“放开我!”却也只是像农田里用来驱赶鸟雀的稻草人,做做样子而已,毫无气势可言。
他看着她,无限怜惜,说:“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她看似平静地笑,说:“不需要!”她掰他的手,不想再和他纠缠下去,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哥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根本就不理她,接着说:“医院病房的事你不用担心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钱的事也不用你操心,还有房子也收回来了,你可以搬回去住了……”
他从欧洲飞回来,先去了医院,问明情况后,先安排好了医院的一切,又到了三叔苏清远的家,苏清远看见他有些怵,陪着笑脸问:“不是去了欧洲吗,回来怎么也不告诉三叔一声,三叔也好去接你……”
苏楚叫跟来的人收拾东西,苏清远糊涂了,说:“侄子,你这是干什么?”
他冷然地说:“不干什么,送你回监狱!”
苏清远一边阻止那两个青年男子,一边喊:“苏楚,你不要太过分了……”
他挥手,两个人架住了苏清远,他走过去,咬牙说:“我过分吗?好像过分的是你吧,孟凌东躺在医院里,你都没有一点悔过之心,你停他的医药费,我就让你在监狱中度过后半生……”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痛恨的,他只是去了欧洲一个月,苏清远私下里就做了许多的小动作,就算他不和他计较畅新的事,但是到医院里去停了孟凌东的医药费,要求医院换病房,这样的事一样让他无法忍受。
他的理由是为孟凌东所付的住院费医疗护理方面的费用太高。苏楚却在想,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没有人愿意拿鲜活的生命去换。
苏清远似是明白了,叫喊着:“我要给你老爷子打电话,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只是声音已经越来越远,两个人早把他架了出去。
从苏清远家里出来,他去找锦弦,才知道房子被抵押拍卖的事情,他不敢想象,他走之后,锦弦为他受了多少的苦,难怪林硕在电话里说看到她在酒吧里做买酒女,他辗转难眠,迅速返了回来。
本来早应该来见锦弦的,房子的事占去了他大半天的时间,来了,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上楼,锦弦就回来了,和郑新一起。
她仰起头看着他,嘲弄地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只是个普通人,只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不想和你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等着你玩累了,玩厌了再一口吃掉,就算我求你,放过我,好吗?”她不需要这样的好心。
可对他来说,爱如桎梏,他说不明白,心一丝丝地抽动,为女孩的不能原谅,说:“锦弦,我会补偿你所受的委屈,也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她冷笑,问他:“我要一个健康的哥,你能还给我吗?”
他无言了,慢慢地松开了她。
她往楼上跑,眼泪不停地滚落,心想,做什么都没有了,再多的惩罚也换不回哥的生命。
洗完澡躺下睡觉,路雪跑进来问:“锦弦,我刚才去阳台上晾衣服,看到楼下有个人,好像是苏楚,你去看看……”
她不为所动,拉上被子装睡。
路雪却不停地来向她报告楼下那个人的情况:
“锦弦,我给你打赌,苏楚今天不会走,输了的人明天请吃鸡翅,怎么样?”路雪如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他抽了多少烟了,锦弦,你知道,我最讨厌抽烟的男人了,可是苏楚抽烟的样子看起来很帅……”路雪八卦着,有些花痴般的迷醉。
“他还在……”路雪终于开始打呵欠,倒在床上不一会儿竟睡着了。
风真大,听在耳朵里类似呼啸的声音,她很不安,想狠下心来不去管他,可最终没有做到,蹑手蹑脚地跑到阳台上去看,一开门,一阵冷风吹了进来,她不禁缩紧了身体。
楼下,一点猩红的光,不用说,那个人还在,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给他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叫她的名字:“锦弦……”听起来很高兴。
居然还没有被冻死,她瑟缩着想,嘴上却没好气地问他:“你怎么还不走?”
他抬头,并不知道望向哪个方向,只是漫无目标地找亮着灯的窗户及窗户前的身影。
她说:“别看了,回去吧。”她藏在窗帘后面,他自然是看不到她的,但借着楼下路灯一圈昏黄的光,她却能把他看在眼底。
他回答她:“我还不想走!”只有五个字,并不多说。
她莫名地恼恨,说:“爱走不走,你最好冻死……”
他居然笑,说:“那不正好,可以还你哥的命。”
她“啪”地摁断了电话,因为气愤,和哥相提并论,他还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