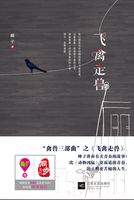罗先梅见到我后,微微有点吃惊,转而笑着埋怨道:“怎么这么半天才来,我们都在等你呢!”
我正纳闷她这话什么意思,进门却闻到一股菜香,客厅里的桌子上摆了好几样家常菜,看样子还没动过筷子,一个中年男人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向他笑了笑,说声打扰了。
男人礼貌性地回了一个笑,继续盯着电视,似乎在看新闻。
罗先梅把我拉到桌边坐下,说:“我就知道你没吃过晚饭,所以正等你呢,和我们一块吃吧!”回头又招呼那个男人,“死老头子,还看什么电视,赶快过来吃饭!”
男人应了声,却没坐过来,罗先梅则去厨房盛饭。
此刻,就我和男人坐在客厅,我心里想着事情,不知道该和这男人说些什么,男人似乎也不觉得尴尬,
只是自顾看着电视,直到罗先梅把饭盛过来了,才终于坐到了桌边。
我随便客套了几句,就准备打听702的事情,没想到罗先梅先开口了。
“小何啊,最近你和你们家小洁是不是闹矛盾啊?都好两天没见她了……”
“哦,她出去旅游了,真不好意思,走之前都没跟您打招呼呢,呵呵……”我再次撒了个谎。
罗先梅笑了笑,然后不经意地问道:“这样啊,她是不是去了你找不到的地方啊?”
我心里一惊,因为她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时间根本无从把握,难道是说她知道了昕洁失踪的事情?或者只是一句很简单的玩笑性的话语?
但不管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还要刻意去隐瞒关于昕洁的事情,倒是没必要了,反而会让罗先梅越来越不信任我。
所以,我放下筷子,恢复了以往的表情,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梅姐,不瞒你说,小洁是失踪了。”
我说完这句话,就去看她的表情,没想到她却显得非常吃惊,张大了嘴巴问道:“什么?你说,小洁失踪了?”
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是这样,看样子,她先前那句就真的只是个玩笑而已,我沉重地点点头,说:“已经半个月了。”
啪!罗先梅把手里的饭碗往桌上一压,然后说了句话,这句话让我又惊又喜。
她说:“你们小两口子倒好,这个说那个疑神疑鬼,那个说这个失踪半个月,弄啥西名堂哟?”
听到这句话,我几乎要跳起来,赶忙追问道:“梅姐,你是说,小洁她……说我疑神疑鬼?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罗先梅皱了皱眉,不耐烦地说:“不就两三天前嘛,跟我说她要离开几天,你自己不做饭,叫我关照下你!你看,我今天不就叫你过来吃饭了嘛!”
“两三天前你见过她?!她还跟你说了什么?”
“对啊,好像是大前天吧,她就跟我说了要关照你,其它倒也没说什么……哎我说,你干吗这么紧张?是不是她跟你闹别扭,离家出走啦?”
“差不多吧,梅姐,小洁她两三天前具体是几点钟和你说的?说完后她去了哪里?”
“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样子,说完后就上楼回去了啊。”
“有没有看到她下来?”
“这我倒没有注意……”
我说我半个月都没见到她了,一直在找,所以麻烦梅姐务必要再好好想想看,最后一次谈话后她去了哪里。
罗先梅低头想了一会还是没想出什么,然后转了个语气说道:“她不会真的离家出走了吧?你们这小两口,好好地咋闹别扭呢?这我就要说说你啦,小何你也真是的,小洁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气走了,你到底做了啥事啊?不会是外面有……有那个了吧?”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是那样的人,不过半个月前她走的时候确实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最近以来也一直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感觉小洁可能是被吓跑的。
“啥奇怪的事情?她怎么被吓跑?”
“不瞒你说,自从上次你不让我去楼上看以后,我觉得这事情还真的和楼上有点关系……”
砰!一声突如其来的拍桌声响起,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瞪了我一眼,脸色阴沉得可怕,转身就朝卧室走去。
我一时间愣住,转头看了看罗先梅,她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似乎我的话触到了他们的忌讳,不过想想也是,自家楼上一家四口全死掉,屋子还闹鬼这种事,若非必要,谁都不愿去提。
但想来,无论如何,像罗先梅丈夫这样的反应,倒显得有点过头了,我赶忙向罗先梅道了歉,然后假装不明就里地问道:“梅姐,你爱人他这是咋了?怎么突然生气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罗先梅的嘴角突然抽了一下,但很快表情又恢复了过来,从桌子那边探过头来,几乎是贴着我的面门,将声音压到极低,说:“关于顶楼的事我不好跟你说太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那是正常的,你就当啥事也没有,别去管也别去想!另外……不是我说风凉话,那个……如果你们经济上有能力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另外找个房子比较好……”
她这话其实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我听出来了,介于顶楼闹鬼的事情,她劝我搬家。
我心说现在不是搬家不搬家的问题,而是找不到昕洁的问题,即使要搬,那也必须等找到昕洁后再说。
至于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鬼,是否就在我家楼上,闹得多么凶,我都不想管,但如果真的是那个鬼造成昕洁的离奇失踪,那就是它惹到我了,我不管想什么法子都会和它斗到底,至死方休!
当然我不可能把我这种想法和一个如此忌讳顶楼的女人去说,而且看现在这种情形,我原先设想让他们两口子陪我上楼的想法也是没必要提了,于是随口应道:“梅姐你说得对,等找到昕洁后我再想办法……”
罗先梅同情似地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叫我多吃点菜。
终于吃完饭,临出门的时候,罗先梅语重心长地说道:“小何啊,听梅姐我的话,千万别去管顶楼的事,找到你家小洁后,就想办法搬家吧!还有,这几天,如果小洁再来找我,我肯定会好好劝劝她的,叫她别再跟你捉迷藏了!”
我附和性地点点头,转身欲走,却又被她一把拉住,凑到我耳边补充了一句:“忘了告诉你,以前住在你们那屋子的也是小两口子,一个疯了,一个失踪了。”
她这补充性质的一句话,立刻让我意识到,我似乎抓到了什么关键性的线索,猛然回头,焦急地问道:“梅姐,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小两口子现在在哪里?”
“不是跟你说了嘛,一个失踪了,一个疯了,都好几年了,我怎么可能知道!”
“那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
罗先梅似乎想了一会,然后拍了拍脑袋,抱歉地说:“哎,你瞧我这脑子,人老了,记性当真是越来越差了,实在想不起来啦……”
我还想再打听点先前这对住户的情况,但想想一下子也没什么好问的,于是跟罗先梅道了谢,上楼回屋里,把刚刚得到的所有线索再重新理一遍。
根据罗先梅的讲述,昕洁至少在三天前还出现过,从这点上来看,如果她的话不假,那么昕洁不是离奇失踪,而是有意要避开我?
但是我实在想不通,在事发当天她是怎么做到以那种极度离奇的手段上演失踪一幕的?而且在这整整半个月里面,一次都没让我见到,甚至连凌志杰以及所有跟她有关系的人也都找不到她,而偏偏只是通过一个住在楼下的邻居大姐来让我知道她没有失踪,她到底怎么做到的?
且先不去管昕洁能否做到,单纯分析她这么做的动机,里面的疑点太多。
以我对她三十几年来的了解,她一个眼神一抬手我就知道在想什么,从穿着开裆裤一起玩泥巴的时代开始,到后来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她对我的信任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她自己,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我,更不会想方设法地躲着我,现在这样的情形,我宁愿相信她是被迫的,是有什么东西逼着她那样做……
我一下子又想起了她消失前最后的那个眼神,充满了不舍与无奈,还有那份心底诉不尽的爱意……
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她没有这么做的动机,也没有这么做的条件。
突然我又回忆起了罗先梅所说的一个细节——她说昕洁跟她抱怨我最近疑神疑鬼。
虽然我无法完全再现当时昕洁找到罗先梅说话的情景,但是从这个细节里我发现两个个非常矛盾的问题,那就是:
一、昕洁是以抱怨的形式来跟罗先梅说话的。而且罗先梅似乎对她当时的神情和语气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就仿佛是很平常的拉家常式的那种抱怨,这跟昕洁消失时的那种神情完全不符合。
二、抱怨的内容就更矛盾了,是“说何宁疑神疑鬼”。这个内容仿佛是在说,她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然后天天看着我在四处找她,才会觉得我“疑神疑鬼”……
想象一下这种状态吧,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就不单单是疑神疑鬼了,简直就可以肯定是完全疯了:分明就能在自己屋子里看到一个人,却还在四处找那个人!
想到这里,我竟然也有点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精神状态来,于是使劲揉了揉眼睛,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看着这个长久没人打理以至于连木餐桌都发霉长毛的屋子,我确定自己没有发疯,也不可能选择性地失明到看不见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人。
我又仔细揣摩了一下这两个矛盾的地方,发觉还是老样子,根本就没办法说得通,但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而且这个不对劲的地方就是产生矛盾的源头,想来想去一时间又想不出来,心下就变得相当急躁。
我使劲捶了捶脑袋,在意识到自己此刻的状态后,决定洗把脸清醒一下。
走进卫生间,却赫然看到那盥洗台上又多了一样东西——一支手表。
我赶忙扯了张纸巾,小心翼翼地将表链一端包住,然后拿起来看。这是一支老式的手表,不大,表盘上有“上海”两个字,翻过背面,是钢印的字体:“上海手表厂 防水 972”。
我又看了看表链,是那种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国产表链,有缩放功能那种,但相对也要窄一点,随即明白了,这是一支女式手表,因为那个年代的手表不和现在一样有非常明显的男女特征,唯一就是大小及适手程度上有些区别。
到现在为止,莫名其妙出现的东西已经有三样了:长头发、口红、七八十年代的女士手表。
一般情况下,这三样东西,再加上屋子里总是看不清晰的鬼影,通常会让人联想到什么?一个女人,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女人,她一直徘徊在这个屋子里,让你感觉到她的存在,却永远找不到她……所以更准确地说,她是个女鬼。
但,对我来说,这三样东西的出现,却让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专业词汇——侵略性心理暗示,也就是俗称的恶意催眠。
当然,我说的恶意催眠不可能像电影《催眠》里所表现得那么夸张,但在实际生活中,催眠倒确实无处不在,它利用的是人类在心理层面上的条件反射。
我们都知道膝跳反应,这是生理层面上的条件反射,而心理层面上的条件反射也是类似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一般都玩过的:我假装打你的眼睛,但实际上不会打到,可你仍然会无法控制地闭上眼睛。
这是人类在自我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而我所说的侵略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利用这种本能的特性,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不断挑拨你的神经,让你的心理防线崩溃,然后跟着侵略者想要引导的方向走。
所以,看到这支老式的女表,我并没有像最初看到口红一样紧张,反而觉得有点庆幸,因为这种东西出现得越多,对我越有利,我可以靠着这些东西得到更多关于整件事的线索。
和先前一样,我找了个保鲜袋,将手表收起来,和口红一起放进冰箱的冷藏柜。
在关上冰箱门转身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罗先梅遇见昕洁的时间。
她说是三天前的下午两三点左右,而那天我正好去自己开的私人诊所里收拾东西,不在家的时间恰好也就是下午一点多到三点多,为什么时间会这么巧,昕洁刚刚凑好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回来?她又怎么会知道我那个时间段不在家?
那么,有谁会知道我那个时间段不在家呢?
罗先梅?对!也只有她会知道,因为她是家庭主妇,一直都在家,也一直都在我们楼下……
而前面我一直想不通的,矛盾的地方,到了这里突然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这根脉络的源头,就是——罗先梅在撒谎。
如果,这些矛盾的事情发生的前提是罗先梅在撒谎,那么就很好解释了,她为了使这个谎看起来更像真的,于是编出一个我不在的时间段出来,好让我无法准确判断。
而她又不能很好地描述在三天前和昕洁见面时的具体情景,则是因为这个谎不够圆满,当然这不能怪她,因为她不知道昕洁失踪时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还有,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的那句“小洁是不是去了你找不到的地方啊?”,看来并非开玩笑,而是她才是知道昕洁去了哪里的人!
那么昕洁最终去了哪里呢?
702!楼上那间一直被罗先梅“忌讳”,并竭力试图阻止我进去的屋子。
昕洁自己做不到,也没有动机,但是有人逼迫她,并“帮助”她做到了——在那天以离奇的方式消失在飘窗上,而“帮助”她的这个人,似乎就是罗先梅他们两口子!
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暂时不得而知,也许在702里藏着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许跟房产有关,在房价不断攀高的时代,为了钱有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思维到了这里,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脑子过热了,竟然变得如此阴谋论起来?
因为静下心来想想,一个住在楼下的,还好心关照你,请你去他们家吃饭的邻居大妈,在我的推测中,竟然会变成这样一个有着巨大阴谋的人物……这种情节实在太戏剧化了。
但不管如何,在我的推测得到现有证据的印证之前,罗先梅两口子的嫌疑暂时不能排除,我会尽快让凌志杰帮忙做那两样东西的指纹鉴定。
至于傍晚时分那个恐怖的黑影,以及702的事情,我也还是需要凌志杰过来帮忙,就我一个人,还不至于傻到像恐怖电影主角一样,哪里恐怖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
看了看挂钟,晚上十点一刻,我再次给凌志杰打去电话,这下很快就被接了起来,那头传来哗啦啦的雨声,还有凌志杰略带焦急而高亢的嗓音。
“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前面说有线索,你找到了什么?”
见他直奔主题,我不绕弯了,道:“最开始不是在我们卫生间里找到一根很长的头发么?今天又出现差不多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
“一支口红,还有一支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牌女式手表。”
凌志杰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问道:“哪里找到的?”
“还是卫生间。”
“你摸过没?”
“口红抓过一下,手表没动。”
“好的,你明天把那两样东西带我办公室来。”
“没问题。对了,你现在还在外面?这几天出的事情很大,我知道你非常忙,但怎么都不跟我说声?”
“有什么好跟你说的?瞧你那失魂落魄的样子,还有空来管我忙不忙?”
我叹了一口气,道:“前段时间确实完全沉沦了,不过你放心,我差不多已经恢复了,接下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忘了告诉你,有人说在三天前见过昕洁。”
“什么?!”凌志杰听到这句话显然比我还要震惊,紧追着问道,“三天前有人见过?谁?你跟谁说了话?”
“楼下502的那位大妈,你应该也照过一次面。”
“她?没什么印象……明天!明天你也不用过来了,我尽量抽时间去你那一趟,今天就这样,我这边还有事情,先挂了!”
我刚说出“别挂,还有件事……”可才说了一半,那边就果断地挂掉了,凌志杰做事向来雷厉风行,连电话也这样,从来不管对方有没有说完,这种脾气是改不了的,谁都拿他没辙。
我赶忙再拨了一次,却没想到那边是彻底不想接听了——关机。
看样子,还是只能把恐怖黑影的事情留到明天他过来时一起说了,今晚上我还有些东西要准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