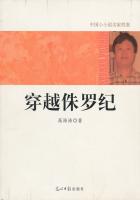三十年的等待
“她”叫红衣,“他”叫蓝衣。简陋的舞台上,“她”身穿大红斗篷,一双小手轻轻弹拨着琴弦。阁楼上锁愁思,千娇百媚的小姐呀,想化作一只鸟飞。“他”一袭蓝衫,手里一把折扇,轻摇慢捻,玉树临风,是进京赶考的书生。湖畔相遇,花园私会,缘定终身。“他”金榜题名,凤冠霞帔回来娶“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那时,“她”与“他”,每天都要演出两三场,在县剧场。木椅子坐上咯咯吱吱,头顶上的灯光昏黄而温暖。绛红的幕布徐徐拉开,戏就要开场了。小小县城,娱乐活动也就这么一点儿,大家都爱看木偶戏。剧场门口卖廉价的橘子水,还有爆米花。有时也有红红绿绿的气球卖。
幕后,是她与他。一个剧团待着,他们配合默契,天衣无缝。她负责红衣,她是“她”的血液。他负责蓝衣,他是“他”的灵魂。全凭着他们一双灵巧的手,牵拉弹转,演绎人间万般****,千转万回。一场演出下来,他们的手酸得麻木,心却欢喜得开着花。
都正年轻着。她人长得靓丽,歌唱得好,在剧团被称作金嗓子。他亦才华不俗,胡琴拉得很出色,木偶戏的背景音乐,都是他创作的。偏偏他生来聋哑,丰富的语言,都给了胡琴,给了他的手。
待一起久了,不知不觉情愫暗生。他每天提前上班,给她泡好菊花茶,等着她。小朵的白菊花,浮在水面上,淡雅柔媚,是她喜欢的。她端起喝,水温刚刚好。她常不吃早饭就来上班,他给她准备好包子,有时会换成烧饼。他早早去排队,买了,里面用一张牛皮纸包了,牛皮纸外面,再包上毛巾。她吃到时,烧饼都是热乎乎的,刚出炉的样子。
她给他做布鞋。从未动过针线的人,硬是在短短的一周内,给他纳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来。布鞋做成了,她的手指,也变得伤痕累累—都是针戳的。
这样的爱,却不被俗世所容,流言蜚语能淹死人。她的家里,反对得尤为激烈。母亲甚至以死来要挟她。最终,她妥协了,被迫匆匆嫁给一个烧锅炉的工人。
日子却不幸福。锅炉工人高马大,脾气暴躁。贪杯,酒一喝多了就打她。她不反抗,默默忍受着。上班前,她对着一面铜镜理一理散了的发,把脸上青肿的地方,拿胶布贴了。出门有人问及,她淡淡一笑,说,不小心磕破皮了。贴的次数多了,大家都隐约知道内情,再看她,眼神里充满同情。她笑笑,装作不知。台上红衣对着蓝衣唱:相公啊,我等你,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她的眼眶里,慢慢溢满泪,牵拉的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心在那一条条细线上,滑翔宕荡,是无数的疼。
他见不得她脸上贴着胶布。每看到,浑身的肌肉会痉挛。他烦躁不安地在后台转啊转,指指自己的脸,再指指她的脸,意思是问,疼吗?她笑着摇摇头。等到舞台布置好了,回头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去寻,却发现他在剧场后的小院子里,正对着院中的一棵树擂拳头,边擂边哭。
白日光照着两个人。风不吹,云不走,天地绵亘。
不是没有女孩喜欢他。那女孩常来看戏,看完不走,跑后台来看他们收拾道具。她很中意那个女孩,认为很配他。有意撮合,女孩早就愿意,他却不愿意。她急,问,这么好的女孩你不要,你要什么样的?他看着她,定定地。她脸红了,低头,佯装不懂,嘴里说,我再不管你的事了。
以为白日光永远照着,只要幕布拉开,红衣与蓝衣,就永远在台上,演绎着他们的爱情。然而慢慢地,剧场却冷清了,无人再来看木偶戏。后来,剧场转承给别人。剧团也维持不下去了,解散了。她和他的泪,终于滚滚而下。此一别,便是天涯。
她回了家。彼时,她的男人也失了业,整日窝在十来平方米的老式平房里,喝酒浇愁。不得已,她走上街头,在街上摆起小摊,做蒸饺卖。曾经的金嗓子,再也不唱歌了,只高声叫卖,蒸饺蒸饺,五毛钱一只!
他背着他的胡琴,带着红衣蓝衣,做了流浪艺人。偶尔回来,在街上遇见,他们怅怅对望,中间隔着一条岁月的河。咫尺天涯。
改天,他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熟人,托他们每天去买她的蒸饺。就有一些日子,她的生意,特别的顺,总能早早收摊回家。
这一年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地下,冷。她抗不住冷,晚上,在室内生了炭炉子取暖。男人照例地喝闷酒,喝完躺倒就睡。她拥在被窝里织毛线,是外贸加工的,不一会,她也昏昏沉沉睡去了。
早起的邻居来敲门,她在床上昏迷已多时,是煤气中毒。送医院,男人没抢救过来,当场死亡。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她活过来了。人却痴呆了,形同植物人。
没有人肯接纳她,都当她是累赘。她只好回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里。老母亲哪里能照顾得了她?整日里,对着她垂泪。
他突然来了,风尘仆仆。五十多岁的人了,脸上身上,早已爬满岁月的沧桑。他对她的老母亲“说”,把她交给我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她的哥哥得知,求之不得,让他快快把她带走。他走上前,帮她梳理好蓬乱的头发,抚平她衣裳上的褶子,温柔地对她“说”,我们回家吧。三十年的等待,他终于可以牵起她的手。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她。他给她拉胡琴,都是她曾经喜欢听的曲子。小木桌上,他给她演木偶戏。他的手,已不复当年灵活,但牵拉弹转中,还是当年好时光:悠扬的胡琴声响起,厚厚的丝绒幕布缓缓掀开,红衣披着大红斗篷,蓝衣一袭蓝衫,湖畔相遇,花园私会,眉眼盈盈。锦瑟年华,一段情缘,唱尽前世今生。
团聚
邓文秀家里很热闹,妻子正和几个姐们打麻将,邓文秀在旁边搞服务,时而为她们倒茶、点烟,时而打点零钱。夜深时,忽然有个姐们说想吃西瓜,可文秀家里没了,妻子叫他去瓜园摘。邓文秀种了三亩地的西瓜,西瓜快成熟的时候,他让六十多岁的老父亲邓伯华,夜里住在瓜棚里看瓜。
邓文秀奉妻子之命来到瓜园,老远就望见瓜棚里有一男一女,男的是父亲,女的背向外,看不见面容,开始他以为是母亲,可她老人家远在十几里外的镇上弟弟家,吃晚饭时也不曾见她回来,这样想着不由心里一惊。如今时兴搞婚外恋,难道老爸什么时候也搞上了?如果真是这样,不说对不起儿女们,怎么对得起老妈啊!借着月色,邓文秀看见老爸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什么。夜这么深了,这女人还送东西来此约会,看来两人感情非同一般。这老相好是谁呢?邓文秀正欲找个最佳位置,把那个女人看个清楚明白时,却见两个老人相拥在一起,说起了悄悄话。
望着天上的月亮说:“你看那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就跟你做姑娘时候的脸一样。”女的有些伤感,叹息道:“唉,如今老啰,比不得当年啦!”老爸接道:“是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都老了,想想还是小时候有意思。小时候我们晚上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拍着手做游戏,还一起唱儿歌:‘大月亮,小月亮……’”说着,两个人不由唱了起来。唱罢,女的说:?摇“那时候真开心。”“可不是,”老爸说,“那时候咱们一起玩呀、唱呀、跳呀,多自在,多快活。”说到这儿话锋一转:“可现在,想在一起也难啊,想亲热会儿,还得偷偷摸摸,跟打游击一样。”停了停,欲搂女的亲吻。女的推开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叫人看见多不好。”“夜深人静,有谁看见?看见了又咋了?”
邓文秀不敢再看下去了,不然自己会很难堪。不行,我得吓吓他们不能任其这样发展下去。于是,邓文秀从旁边地里的一个稻草人头上取来草帽,扣在自己头上,帽沿压得很低,遮去了自己的眉眼。他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捏着嗓音大声道:“你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在瓜棚里干这事儿?!”两个老人吓得一抖,呆在那儿。女人胆小害怕,压低声音问:“怎么办?怎么办?”老爸定定神,大声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邓文秀继续装成捉奸人,口气冷冷地说:“哼,胆儿还不小啊!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老爸听话不对头,忙大声道:“我们是夫妻!”邓文秀心想,以假充真还理直气壮,真不愧是老手!便道:“是夫妻怎么还会说说唱唱,动手动脚,比小青年还猴急呢?”“你……你……”老爸恼怒道,“你管得着吗?!你是谁?有种露出真面目来!想敲诈我吗?做梦去吧!”
女的一直脸朝里,也许是怕把事情闹僵闹大,她转过身子,温和地说:“这位兄弟,你听我说,今天是老头子的生日,我给他炖了一点他爱喝的板栗鸡汤,也想凑一块儿说说话,所以我就来了这瓜棚……”这回,邓文秀听清声音了,他急忙偷眼一瞧,心里暗暗叫道:天哪,她还真是老爸之妻,我的娘啊!今天是老爸的生日,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呢?!此时此刻,邓文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正想着怎么脱身,却听见老妈打开话匣子说起来:“不瞒你说,我们做夫妻都四十多年了,两个儿子也都当爸爸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结婚后,便分了家。老大住这村里,老幺在镇上做生意。为了公平赡养我们老两口,就抓纸团儿,抓到妈得妈,抓到爸得爸,结果我跟了老幺住镇上,老头子跟了老大住村里。想不到我们老夫妻,打从小时候好起,盼结婚,盼生孩子,有了孩子,盼他们长大,盼他们结婚成家,谁知一切盼到了,我们却老了,做不得主了,被儿子媳妇们拆开了。一人养一个,这跟让我们老两口离婚没什么两样,就连有个三病两痛,都见不了面,谁也照顾不了谁,想一起说说话解个闷都没机会。今天是老头子65岁生日,也是我们俩结婚的纪念日,人家搞什么金婚呀,银婚呀,那个热闹,我们不眼红,只想凑一起说说话儿,谁知就让你碰上了……”老妈这一肚子话是哭诉出来的,她老人家泪流满面,老爸在一旁替她边抹泪边安慰:“别哭,别哭……”可自己的泪水也禁不住夺眶而下。
邓文秀羞愧难当,想不到自己为了与弟弟公平养老人,却做了法海,硬是将一对几十年的恩爱夫妻拆散了。难道说人老了,就可以不要夫妻****了吗?!想到这里,邓文秀立即扔掉头上的草帽上前几步,“扑通”一声跪在父母跟前:“爸、妈——”
两位老人惊异万分,喃喃道:“是……是你?”
“是我呀!”邓文秀痛悔道,“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二老双亲啊!”停了停,又说:“请二老放心,今晚我做主了,无论如何也要让二老住在一起,不再分居,让你们老来有个伴,有个照应,有个说话儿的!”
下雨的晚上
他们开始找房子。在网上一条一条地搜集信息,然后打电话过去核实,确定,约下看房的时间。
看了很多房子。有时候要来回兜转好几条路线的车,非常累人。
她的要求高。希望房子很干净。周围有公园和绿化带,并且方便交通和购物。
她说,我和你不一样。你一整天在公司,回家只是睡个觉。而我呢,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要工作,要阅读,要做饭,要散步。如果环境不好会影响我心情。
他自然按照她的意愿,只是这样的房子太难找。要么是家具不全,要么是地段偏僻。
她的情绪化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突然不愿意理他,也不跟他说话。
她从不控制自己的坏脾气。
那天晚上他公司里有应酬,整个部门的人出去吃饭。他不放心,走到门外给她打电话。她在外面。她说,我在买东西,语气很冷淡,不愿意和他多说话,只问他几点能结束。他说,还得等一会儿吧,一时不能完。
那你就吃饭吧。她咯嗒一声干脆地挂了电话。
他在饭桌上心神不定。外面下雨了。他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他突然觉得她会在北京像泡沫一样地消失。两个小时后,手机响起来。有嘈杂的雨声和喧嚣,然后她疲倦的声音传过来,她说,我在王府井,买了很多东西。没钱打车回家了。这里下着好大的雨。
他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她说,我在咖啡店吃东西,我肚子饿。
他说,你等在原地,别走。我过来接你,送你回家。
她说,好。我在天主教堂对面的咖啡店。
他提前告退,打了车往王府井赶。路上塞车。雨点打在车窗上,声音是激烈的。他想她会不会淋湿,又想起来她是在咖啡店里,心落到了实地。
出租车一停下,他就冲进咖啡店里。大雨还是把头发淋得有些湿。小恩就坐在门边的小小桌边,桌子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冰冷的咖啡,巧克力蛋糕已经吃完。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大堆百货公司的纸袋。她手里摊开一本杂志,心不在焉地翻动。看到他进来,她说,我在找你女朋友的名字,叶子。她不是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吗?为什么编辑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
他真是后悔一时失神告诉了她旧日女友的名字,以致让她隔几日就要念叨一番。
他问,买了什么东西?
毛衣、灯芯绒裤子、鞋子,还有晚霜和口红。
都在世都百货买的吗?
是的。
购物狂啊。
她不搭话,脸上闷闷不乐的表情。他脱下外套夹克盖住她的头遮挡雨水,一边拎起她的一大堆购物纸袋子,带着她出去拦车,
出租车里都有人。路上是冰冷的大雨和狼狈的人群。路边的霓虹灯在水汪汪的地面上交织出斑斓的光影。她突然又高兴起来,一边没来由地笑着,一边跟着出租车跑。他说,你疯什么啊,小丫头。她拦住一辆车,抢先挤了上去,把先等在路边的一大家子人挡在了外面。
K,K,她大声叫他,快上车。
他看到窗外那家人措手不及的表情。她用手抱着他盖在她头上的夹克,眼睛亮亮的,得意地看着他。
他说,又神气了,她的脸上还是有潮湿的水汽。他拉住夹克,俯过脸去吻她。先吻她高高的脑门,再吻她神气活现的眼睛,然后堵住她的嘴唇。
她的嘴唇上有雨水清凉的味道。
如果你知道我爱你
你一直不知道我爱你。你不知道明媚的阳光下有我的忧郁;迷醉的酒杯中有我的苦涩;闪烁的霓虹里有我的阴沉;欢乐的人群中有我的叹息;你不知道在你灿烂的笑容后面阴郁的角落里,是我无声的哭泣。你,你这让我神魂颠倒的男人,一直不知道。
我躲在密密的丛林,隐在无人的荒野。我是冰封在湖里的丑小鸭,是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是披着黑纱,穿梭于城市夜空的巫女。我的美丽是不见天日的湖水,我的王子在别人的童话里快乐地生活,我的爱情是工业时代的星星,在灯火通明的都市上空黯淡而孤独。
我以为你爱过我,在你搂着我说我的头发很好闻,在你拉着我的手滑行在人群迷离的溜冰场,在你的声音穿过电话线,对我说你会一辈子这样待我,这样疼我——你说:“你让我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