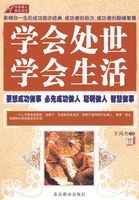庞德受到过日本诗影响,也受到过中国诗影响,他的名言可作代表:“中国是基本的,日本不是,日本是一种独特的兴趣,就像普罗旺斯,或除但丁外的12至13世纪意大利……”中国为何是基本的呢?庞德再三说,中国之于新诗运动,就像希腊之于文艺复兴。
弗莱契在意象派时期就明白“日本诗大抵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高度特殊化的表现形式”。后来他回顾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说:“我们意识到日本文学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学,我们也意识到这些日本形式——它们对于日本诗来说也是个障碍,无法促使其发展——对于意象派了解东方诗来说帮助不大。”
与中日诗都有关系的狄任斯也对中日诗在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不同作用有过分析。她指出,日本俳句过于独特的形式,使人们容易感觉到其影响,“中国诗影响相形之下难于具体看见,但稍迟几年在我们的诗人中就传播开来。”
她甚至还开了一张名单,其中受中国诗影响的包括十个诗人,“以及其他人”;受日本诗影响的有四个诗人,“以及其他人”,这个名单实在不够准确。但这个比例(10∶4)可能是准确的。因为它与J·L·弗伦契所编《莲与菊》一书中所收集的仿中国诗与仿日本诗的比例大致相同。
埃米·罗厄尔把她的仿中国诗与仿日本诗收于同一个诗集,但她自己指出,此集中的仿日本诗“较严格地遵循着俳句形式,而‘汉风集’组诗都没有相应的中国形式”。研究罗厄尔作品的人也很早就指出,她的仿日本诗“依靠集中的瞬间的效果”,而她的仿中国诗在形式上与新诗运动中的自由诗并无不同,“它们是人世的情景,而非瞬时的印象。”
强调中日有别的人,有的人是带着主观感情色彩。例如宾纳就认为美国人与日本人性格不合,弗洛伦斯·艾思柯也强调不能通过日本来了解中国,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不相同。她这么说,是想贬低庞德(通过日本教授笔记翻译的)的《神州集》,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能读中文,与罗厄尔合译《松花笺》算是直接以中文为本。
实际上,新诗运动诗人所知的日本诗,就是俳句。他们对和歌了解极少,而且也不知道这两种形式除了长短还有什么差别。这种情况曾使一个日本评论家竹友太郎(Tarao Taketomo)非常生气,特地写了篇文章来说明这两种诗体的区别。当然这很难起什么作用,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心目中的日本诗,粗略地说,还是俳句。
6.庞德的俳句
庞德也是先接触日本俳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在1913年左右写了一些仿俳句诗,大部分取材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什么他要用中国题材来写英语仿俳句,而不像埃米·罗厄尔那样直接用日本式题材,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也许他感兴趣的始终是中国,而当时只知道写成二行或三行就叫作东方诗。这两首中国内容仿俳是《扇,致陛下》:
哦,白绸的扇,
洁白如草叶上的霜,
你也被搁在一边。
明显来自班婕妤的《怨歌行》一诗最后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另一首诗《蔡植》(Ts"ai Chi"h)成了中西比较文学史上的无头公案,至今不知所本:
花瓣飘落在泉水里,
橘红色的玫瑰瓣,
它们的赭色沾在石头上。
7.庞德的中国式诗
庞德从翟理斯书取材改写的另两首诗,却不再用仿日本形式。其中之一是取材自《九歌》的仿屈原:
我要到森林里去,
那里,众神走着,头戴紫藤花环,
在银青色的潮水边
还有些神驾着象牙的车。
少女们走来
为豹采摘葡萄,我的朋友,
因为豹在拉车。
我将走在林间空地,
我将走出新长的树丛,
加入少女们的行列。
好像是一首希腊诗。实际上来自《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挂旗。……折芳馨兮遗所思……”
而另一首《刘彻》成为美国诗歌史上的名篇:
丝绸的窸窣已不复闻,
尘土在宫院里飘飞,
听不到脚步声,而树叶
卷成堆,静止不动,
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
一张潮湿的叶子粘在门槛上。
这首诗的原文是据称为汉武帝刘彻思怀已故的李夫人所作《落叶哀蝉曲》,诗见于前秦方士王嘉所撰《拾遗记》: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厄尔·迈纳(Earl Miner)认为这首中国诗被庞德“用从日本借来的形式完全改制了”。他所谓“日本形式”,在这里,显然不是指俳句或和歌,而是指庞德在俳句中首先发现的“意象叠加”技巧。关于“意象叠加”,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详细讲:意象叠加在中国和日本的古典诗中都很多,只是由于俳句形式之特殊,意象的叠加关系特别显明,因而庞德首先在俳句中发现它。应当说这首诗被庞德“按意象派韵原则改写过了”。庞德删去了直抒胸臆的最后两行,而去了这两行后“落叶依于重扃”很自然地成为一个诗尾“叠加意象”。
庞德改写这首诗时,并没有想到他是在用中国题材写日本诗,这点我们可以对比他对班婕妤《怨歌行》的改写即可看出。庞德把刘彻看作中国第一流大诗人。这点很奇怪,因为翟理斯的文学史,只用一页篇幅来写刘彻,只引了两首诗(另一首是《秋风辞》)。庞德对刘彻这位“圣君”兼诗人如此尊重,看来与他已经开始萌芽的“儒家式”政治思想有关。
庞德似乎只在1913年写了几首仿俳诗。此后,在1915年,他写过两首开玩笑的俳句,题材还是中国历史人物。从1914年他开始读费诺罗萨的中国诗笔记起,他就离开了俳句。
仿俳句很容易成为庞德所说的“单意象诗”,这样就很难避免单薄。俳句形式极度精简,想对抗维多利亚诗歌之冗长的诗人们立即采用了这种形式,但形式特点之过于明显又往往容易流俗,仿俳句之泛滥也使其很快过时。“写仿俳句风气不久就证明是一条死胡同。”
日本诗的影响使美国诗人觉察到日本背后存在着更巨大的艺术宝库——中国,而且日本诗人和学者的中国文学修养帮助了美国诗人接触中国诗。换句话说,日本成了中国影响进入美国新诗运动的向导和桥梁。这样说,没有贬低日本诗的意思,下文将会指出在许多问题上中国诗和日本诗联合起着作用。
顺带谈一下日本能剧的翻译。能剧是一种短诗剧,很早就有人把能剧译成英文,但没有受人注意。庞德从费诺罗萨笔记中译出一些能剧,集成一书,叶芝很感兴趣。
能剧也影响了沃莱斯·斯蒂文斯的诗剧《三个游者观日出》,但我们下文将指出,该剧结构的能剧化,以及人物的中国化,都只是浅层的,斯蒂文斯的根本思想是西方式的。
庞德在把他译的第一个能剧《卫茅》(Nishikiqi)寄给蒙罗时,希望蒙罗别写他的名字,仅署上费诺罗萨的名字,他说这样“容易被接受”。这份自信心就比译《神州集》时差多了。艾略特在评论庞德这个时期的工作时也指出《神州集》可以作为庞德的创作而立足,而他的能剧翻译只是“《神州集》的餐后点心”。
8.庞德“成形期”的中国影响
把庞德所受的中国影响与日本影响加以区分,还是有必要的。
厄尔·迈纳博学的大作《英美文学中的日本传统》(The Japanese Tradi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1958)在当代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至今尚未有一本关于中国影响的著作能与之媲美。此书材料丰富,分析精辟,而且九章之中,就有整整三章谈的是新诗运动,是研究新诗运动与远东诗歌关系的经典性著作。但是,迈纳没有用中国诗影响作为参照,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观点值得商榷。
迈纳在分析庞德的反象征主义诗学时,引用了庞德1915年的著名论文《旋涡主义》(Vorticism)中的一段文字:
另一种诗,意象诗,与抒情诗一样古老,一样卓有声誉,但直到最近,没有人给它一个名称。伊比库斯(Ibycus,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和刘彻表现了“意象”,但丁也因为这原因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却因为缺乏意象而成为夸夸其谈的诗人,意象主义不是象征主义。
迈纳先生接着从这段文字进行推论:“《鲁斯特拉》(Lustra,1916)是庞德谈论以上诗人和文学作品以后的第一本诗集,但我们从中找不到但丁,找不到伊比库斯,也找不到刘彻——除了一首诗,但是,由于本书前文所引的用来说明意象叠加的大部分诗都收于此诗集,看来我们有正当理由说日本诗是这段时期,即庞德的理论思考和创作的成形期(formative period)的基础。”
迈纳的结论恐怕过于匆忙了。固然把刘彻(汉武帝)作为中国诗的代表人物,这是庞德的无知,但是《鲁斯特拉》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组诗,不是庞德作于1913年左右的那二首用日本俳句形式改写的中国诗,而是庞德写《旋涡主义》一文那段时间改译的《神州集》(Cathay)。
厄尔·迈纳把1916年前称作庞德的成形期,完全正确。但这成形期最大的特点,是庞德从1910年至1912年的普罗旺斯影响,1913年的日本俳句影响,转向1914年至1915年的中国诗影响。庞德的密友梅·辛克莱(May Sinclair)当时就声称在译中国诗时庞德“找到了他最终的自我”。
而且,庞德在1915年前就开始研读被论者认为是庞德诗学基础的费诺罗萨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据弗莱契回忆,1913年7月,埃米·罗厄尔初访伦敦,与庞德和弗莱契晤谈,此时庞德已在谈论中国文字中的奥秘。弗莱契另文又说,庞德在1914年至1915年时常谈到费诺罗萨这篇文章,但秘不示人。
1914年6月1日出版的《自我主义者》上有一段文字,似乎是庞德故弄玄虚的广告:“人们开始私下传说,说费诺罗萨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发动了一场文艺复兴……”
据庞德自己说,他在1915年想在《耶鲁评论》发表“费诺罗萨的东西”(Fenollosa"s stuff),而被拒绝。因此,有人认为庞德只是在发表了《旋涡主义》文章之后几个月才读到费诺罗萨那篇论文,这一说法明显不对。庞德1913年得到的费诺罗萨笔记和手稿中,只有这篇论文有可能被理解为能发动一场“文艺复兴”,因为它提出了一整套美学观点。
如果上面的论述,还不足以使人相信庞德在其“成形期”最大的影响来自中国诗,而不是如迈纳先生所说的日本诗,可以再看庞德传记中的一段记载:“伦敦肯星顿荷兰广场五号,奥尔丁顿夫妇(即理查德·奥尔丁顿与H·D·奥尔丁顿)住在同一层上。”H·D·奥尔丁顿写道:“埃兹拉在译中国诗——其中某些诗美极了!他每天要奔过来四五次,拿出一首新译来读给我们听。”
庞德得到费诺罗萨笔记后如获至宝,立即开始译中国诗,他的激动在其他一些庞德传记中也都提及。因此,让我们看这一段历史:
1913年底:得到费诺罗萨夫人寄来的笔记;
1914年:激动地译中国诗;
1915年:陆续发表译诗,《神州集》出版,在刊物上发表专论中国诗的文章;
1916年:将1913年以来的诗结集《鲁斯特拉》,其中收有全部《神州集》。
而庞德在1913年后就几乎没写过仿俳句。也就是说,最早时,庞德的主要参考书只是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他尚受俳句影响;等到他取到费诺罗萨笔记后,就迅速“中国化”了。因此,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使我们同意迈纳的说法:“日本诗是这段时期,即庞德的理论思考和创作成形期的基础。”相反,我们倒有许多证据说明在1916年庞德这段“成形期”,他所受到的最重要的外国影响来自中国诗。
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小问题,值得提一提:很多人认为庞德在《神州集》中,用日文读音拼中国诗人名字,例如把李白名字拼成Rihaku,是故意的,目的是提醒读者他是通过从日本途径得来的材料在做这些翻译,即强调材料的日本特征。
这种推测没有根据。费诺罗萨笔记中没有写出这些诗人名字的中文发音,《神州集》选择的诗人只有一个人按中文拼音,那是枚乘(古诗十九首之三《青青河畔草》)。这首诗起句叠用形容词,特征太明显,庞德立即回忆起翟理斯《中国文学史》所引的这首诗的英译。的确,翟理斯和费诺罗萨都把《古诗十九首》作为枚乘之作品。
笔者仔细检查一遍,发现《神州集》的诗与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选择的诗,只有这一首重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庞德已经认出Rihaku就是翟理斯书中的Li Po却不愿改过来,而存心在提醒读者他借手日本人译中国诗。至少,庞德没有把握,所以除了一个人名外,其余都沿用了费诺罗萨的日语拼音。
当时在欧美,可咨询的中国文化人竟然一个也找不到,也真叫人感慨。中国诗就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一举成为美国现代诗所受的最主要外国影响,就不可能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