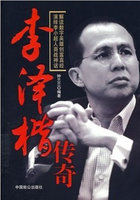三、“琴挑文君”的另类遭遇
古代中国到东汉,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日益成熟,班昭所著的压抑人性、残虐妇女的《女诫》颁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日益完善。
“琴挑文君”的故事所体现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与封建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是不相容的,它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受封建思想文化熏染的文人学士的否定、抵制、批判。这是“琴挑文君”必然会遇到的另类遭遇。
司马迁离世100余年以后,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十七年,宣谕班固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文选》卷四十八《典引序》)他用“污行无节”批相如琴挑文君,为批判司马相如开了个坏头。
魏晋之际,阮籍赋猕猴说:“耽嗜欲而盼视兮,有长卿之妍姿。”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把猕猴比司马相如,转弯抹角骂相如“琴挑文君”是“嗜欲”,不伦不类。阮籍立足玄学,主张还人清静自然,把人的一切正当追求都说成“嗜欲”,明显是错误的。
南北朝时代南朝刘勰说:“相如窃赀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
把相如与扬雄等多位文士放在一起,笼统地贬斥为“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下位也”(《文心雕龙·程器》)。北朝北齐颜之推教训子弟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相如窃赀无操……”把古往今来的文人,连屈原也在内,一锅熬,贬为“轻薄”(《颜氏家训集解》卷四)。
唐代司马贞评司马相如说“相如放诞,窃赀卓氏”(《史记·索隐·司马相如列传·述赞》)。李舟说:“相如薄于贞操,有涤器受金之累。”
(《全唐文·独孤常州集序》卷四百四十三)崔道融在诗中称“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万首唐人绝句·长门怨》)。
宋代以后,儒学发展为压制、禁锢人性自由的理学,对“琴挑文君”的批判,对相如、文君的批判、谩骂,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一些人抛开《史记》所记的史实,对琴挑文君的故事,作了完全歪曲的解读,司马相如就因为“琴挑文君”,他的一切行为,在他们眼中都是罪恶,连为他们说公道话的人,也罪该万死。
苏轼说:“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索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苏轼文集》卷六十五)李樗说:“司马相如为陈皇后尝作《长门赋》……及其惑于嬖妾,而文君又有《白头吟》之叹,躬自蹈之好色之事,其惑于人者如此。”
黄壎说:“及其惑于嬖妾,文君又有《白头翁》之叹。风俗之坏,至此极矣。”(《毛诗李黄集解》卷五)吴子良说:“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
(《荆溪林下偶谈》卷三)乐雷发诗说:“狗监无端荐薄情,鹴裘犊鼻帝乡尘,当时最有文君恨,不识长门买赋人。”(《雪矶丛稿》卷四)魏庆之说:“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诗人玉屑》卷十二《溪》)黄震称:“相如文人无行。”(《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卷四十六)元代淘宗仪称:司马相如为“名教罪人”。(《南村辍耕录》卷九)清代,彭而述称:“文君一事,司马相如得意事也,亦司马子长得意笔也。方其文君新寡,琴心相挑,重赐侍者通殷勤,至于私奔而去,家徒四壁,乃自著犊鼻裈涤器,文君当垆,文人无行至此,可谓寡廉鲜耻矣!而相如为之,此其意在于利文君财耳。及其尽得文君之衣被财物,称为富人。富人矣,而后蜀人杨德意乃得以《子虚》之赋上闻,则此非无故也。安知不以重赐侍者之术再施之于狗监哉?”(《读史亭文集·史评上》卷十六)从东汉到清代,对琴挑文君故事的批判、贬斥、谩骂的言论,大抵如此。这些言论都有所在时代文化思想的烙印以及各人的思想乃至个人的心理特征,言论各不相同,出发点也不尽一致,但思想本质一样,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维护封建礼教,为封建礼教呐喊助威,他们当然看不到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他们骂司马相如是“污行无节”,是“放诞”,是“薄于贞操”,是“文人无行”,是“寡廉鲜耻”,是“名教罪人”,一句话就是没有按封建礼教的规矩办事,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封建礼教的罪人。其具体罪名主要有“窃赀”“窃妻”“好色”“薄情”。“窃赀”一词发明者是扬雄,不过他在《解嘲》中用“窃赀”一词并无贬的意味。他是说:他本人没有蔺相如、商山四皓、公孙弘、霍去病、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的好运气,他们都遇到了明君、遇到了机会,得到了荣耀、地位、好处,他自己运气不好,没有捡到粑货。他用的是一种“不正亦不邪”的语调,完全是自我解嘲,实质是幽默、调侃而已。“窃赀”一词完全作为贬斥,是之后一个又一个借用这个词语的人,一个沿袭一个,最后完全变成一个侮辱性的字眼。什么叫“窃”,古往今来都是清楚的,是指未经他人许可,偷偷地将其财物据为己有。琴挑文君故事,情节清楚,明明是卓王孙在亲属长老的劝说下,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而且也是按汉代法律规定把卓文君应得的财产,分配给卓文君的。再说相如、文君结合之后,宁可清贫自守,也未依法向家庭提出任何财产要求,刺激老父亲。司马相如何曾三更半夜、飞檐走壁偷了卓王孙的钱财呢?按使用这个词的人的逻辑,卓文君必须嫁一个像卓王孙一样富有的人家。找不到这样的人家,卓王孙只有让卓文君老死闺中,寂寞终身!
否则,她嫁的丈夫都是“窃赀”。“窃妻”一词是苏轼首创,他之后,宋代多人沿袭形成了一个批判斥骂司马相如的高峰。“窃妻”就是偷老婆。四川俗话,有说男人“偷老婆”、说女人“偷男人”的话,但都是指已婚男、女“婚外情”的不正当行为。对于处于待婚状态之相如、文君的婚恋行为,与“窃”字有何干系?牛头不对马嘴。按创用者的观点,无非是说卓文君是卓王孙之女,如何处置,是卓王孙的权利。没经卓王孙同意,就是窃。这倒也难怪,在理学思想泛滥的宋代,统治者以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文人,从来没有把女人当人看待,只不过当成一件物品而已。这是他们的固有眼光,毫不奇怪。至于“好色”“薄情”,这个词的制造者,其依据是《西京杂记》所说两条:一是“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二是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于是就给相如造出了“好色”
和“薄情”两顶帽子。青年男女结婚成家,共同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亚圣孟子说:“食色性也。”人生来就有这两种欲望,这是维持现在生命,延续未来生命的必然。相如、文君相爱,把相如说成好色,那天下之人都是好色之徒了。而且《西京杂记》本小说家言,是杜撰编派出来的,《史记》所记,并无此事。纳妾之事,连杜撰者也是“将要”,而不是现实。即便如《西京杂记》所说,相如读了文君的《白头吟》,立即去掉了纳妾想法,这正是他们情深爱重的表现。而且,相如住在茂陵已是人生的最后之年,他重病缠身,就是有这个想法、做法,也不过是给文君找个陪伴而已;何况是杜撰的故事呢!批判者抓着稻草当金条。用他们的话说:真是“大可笑”。至于彭而述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认为杨得意“以《子虚》之赋上闻”,也是相如“再施”“重赐侍者之术”,向杨得意给了小费之故。真是异想天开!
上述种种,毫不奇怪。在封建社会,琴挑文君的故事,长期成为封建的包办婚姻与民主的自主婚姻两种文化碰撞的交接点,越往后它们的碰撞就越激烈。一些人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指责、谩骂,实际上就是对争取民主的自主婚姻的指责和谩骂。不管他们出自何种原因,自觉不自觉,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筑起一道防护民主意识觉醒的防洪堤。但是防是防不了的!随着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被打垮,被摧毁,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正面的解读得到了公认。“五四”运动以后,很多反封建、争民主的勇士,不仅用文章,也用行动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批判。鲁迅、许广平的行为就是实例。郭沫若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指出:“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实是千秋佳话。”泼在相如、文君身上的污泥浊水得到了清除,恢复了相如、文君本来的光彩!
奇怪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竟有声言“研究《史记》四十余年”的专家,突然发现三种“古典文献”:“扬雄的《解嘲》”“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史记》《汉书》中找到三个字(两“缪”一“为”)的新意。什么“新意”?实际上是拾封建卫道士的牙慧。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新,用大量污秽的语言对司马相如、卓文君两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高地位的文化名人进行恶骂(如卓文君“不知廉耻”,司马相如“卑劣、无耻、劫色、劫财,涉嫌包二奶”等),低级庸俗,大演闹剧,把学术讲坛变作了推销自己商品的商场。看似奇怪,并不奇怪,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吸引粉丝们的眼球,为了那50万册“著作”的出卖,为了那白花花的一大堆银子,为了“名利双收”。除此之外,在其眼中、心中还有什么呢?什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什么社会效益,都一钱不值。其行为早已引起了公众及学人的不满。刘南平在《司马相如考释》中指出:“打开电脑,进入当今二十一世纪有关司马相如链接,那些充斥在网页之上,极不健康,充满低级趣味、距离文献、文本真相十万八千里,毫不负责的内容,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化之悲哀。某些当代中国人如此亵渎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耻辱。”
按理说,今天,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诉求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公认,已没有产生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土壤了,突然从一个没有清除的污水坑中冒出的一个,只能是一个另类,无伤大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这朵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中的绝无仅有的艳丽奇葩,具有永恒意义,将永放光辉!司马相如、卓文君,永远是人们心中的情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