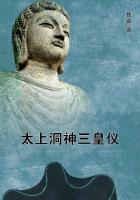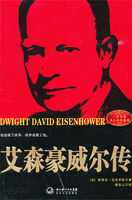——如果被禁锢,被幽闭,她眼中的神采都会统统消失吧。那个自己为之怦然心动的明华容,将会彻底死去吧。徒留一具美丽的躯壳,又有何益。
宣长昊伫立半晌,不由自主往偏殿的方向看去。虽是隔了重重飞檐宫墙,他仍能在心中勾画出那里的每一根廊柱、每一盆花草的模样。那是他心爱之人在宫内待得最久的地方,即便她已香消玉殒,但每当有什么烦忧之事时,他依旧忍不住会到那里寻找些许慰籍,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凡有心事,总要多看一眼那里。
但这一次,他视线甫一看向那边,旋即便像被刺痛一般急急收了回来,心头纷烦更甚,久久理不出头绪。
宣长昊离开之后,先前被他气势震住的小姐们慢慢缓过劲儿来,这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他适才应该是在某处不动声色地审视她们的,不禁纷纷懊恼:刚才全被这场好戏吸引了注意力,以致露出诸多失仪之处,定然是入不了陛下法眼。但转念想到今日既出了这等事,陛下多半是没有心思再挑选贵女,待到改日再行甄选,自己说不定还有机会,这才又稍稍安心。只是,念及种种事情都是项绮罗生出的事端,不禁又向她怒目而视,心内直埋怨她搅乱了这场花朝宴,同时也免不了好奇,她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若在平时,项绮罗定是受不了这种满含恶意的打量,但她此刻已再无暇理会这些人的审视与讥讽。从宣长昊转身的那一刻,她便像被抽走了脊骨一样软倒于地,唯有一双眼睛痴痴看着他的背影。末了像是不甘心一般,伸出手去似乎想要抓住什么,但她一时忘了她的手已被宣长昊用暗蕴内劲的平安扣打成重伤,伸出的手腕除了疼痛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剧烈的疼痛唤回了她的些许神智,将她从一片凄然里拉了出来。恰好这时,长公主身边的宫女走过来对她说道:“项小姐,殿下有命,在事情彻查清楚之前,您先在淑文院待着,不得擅离,也不许家人过来探视。请您这便随奴婢过去吧。”
宫女说得虽然客气,但语气中的强势却是不容置喙。项绮罗本就是娇生惯养,现在又正是满心惶惑,哪里受得了这个,闻言立时尖声说道:“我早说过我没有罪!是那姓陈的污陷我,为什么还要如此待我?!”
听到这话,适才宣长昊在场时一直匍匐于地,生怕惊了圣驾的陈江瀚抬起头来,满面沉痛地说道:“草民与项小姐从未见过面,亦自认从未得罪过大将军府的人,委实不知项小姐为何要百般设计陷害在下,现在却又矢口否认。”
以项绮罗的性子,平时肯定不屑于与陈江瀚这等身份的人说话,但事急从权,当下她也顾不得许多,草草拭了一把额上因疼痛而流下的冷汗,切齿道:“姓陈的,我才想问你:你这般锲而不舍地攀咬我,是受了谁的指使?”
“项小姐既然敢做,为何又要否认?草民早说过并不认识你,而您的身份与草民亦是天差地别。既无新仇,亦无旧怨,何来攀咬之说?况且,以草民的微末之身,若敢做这陷害将军千金的事情,那岂不是以卵击石么?蝼蚁尚且偷生,草民既无死志,又怎会做这自寻死路之事?”
相较被打击过度兼有伤在身,已然不复平日冷静的项绮罗,陈江瀚却是要从容得多,这般有条不紊地将利害关系一一陈明,更能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注意到四周的人都露出赞同神色,项绮罗心中又急又恨,另一只完好的手顿时深深揪紧裙摆,几不曾将厚密的衣料扯坏。
她刚要再度反驳,却听明华容淡声说道:“二位各执一词,在这里便是争到天黑也辩不出个对错来。好在今日之事还另有人证——稍后公主殿下可着人审一审那指证我的宫女,问一问她,那番信誓旦旦说我自称有所倚势而胆大妄为的话,究竟是谁教的。再者,此人能在宫内做出这种种布置,可见身份必定不凡。只要顺着这些线索追查下去,相信定能水落石出。”
她说话时连看也没看项绮罗一眼,但听了她的话,众人的视线却情不自禁再一次向项绮罗转去:相较商贾之身的陈江瀚,项绮罗却是经常出处宫帏,更容易做手脚。再者,就像陈江瀚刚才说的,他又不是得了失心疯,既无利害关系,为什么会想要去攀咬项家的小姐?倒是项绮罗,之前处处针对明华容,虽然不知原由,但她容不得明华容的心思已是昭然若揭。虽然暂时未有实据,但在众人心中,十人已有九人认定,今日这场构陷,乃是项绮罗一手策划的。
但听了明华容的话,项绮罗却是再度气得愤盈胸臆。她虽然大部分时候都能保持冷静自持,进退有据,但在按捺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却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当下她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瞪着明华容,想起刚才宣长昊冰冷的话语和斥责,还有众人轻视嘲讽的表情,心内顿时杀机四起,只觉不杀了这人,实在难泄她心头之恨,亦不足以补偿她今日所受的种种羞辱。她发誓一定会杀了明华容,就像当年杀了……一样!
项绮罗的眼神实在太过可怕,连旁观者看了都忍不住一阵心惊肉跳。长公主见了,立时皱眉将视线移开,命宫人速速将她押去淑文院,又着人将陈江潮、杜唐宝,以及那两名涉事的宫女带下去后,关切地看向明华容:“华容,你没事吧?”
“多谢公主殿下关心,民女无恙。”明华容转向长公主,福了一福,说道:“只是,民女实在惭愧,竟不知是在何时开罪了人,以致闹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败了您今日的雅兴。”
她话说的轻描淡写,但在场之人都是一路看过来的,哪里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见她竟能将被污陷与人有染、放荡不贞的事情如此淡淡带过,心内不禁都对她的大度与镇定生出钦佩来。之前那些对她心生不忿的人亦是有所改观,看向她的眼神皆变成惊叹与敬服。
对于她们态度的转变,明华容倒不是很关心,左右这些人怎么看她,都与她关系不大。现在,她在意的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