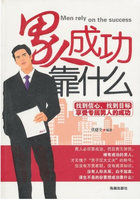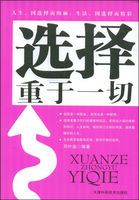雅双
那是12年前的秋天,我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刚经历过情感的挫折,一个人东一头西一趟地在外面跑着,似乎只有这样不停地游荡,才能冲淡那无着落的茫然。那次,我从黑龙江的密山县往回走,中途必须从一个小站坐出租车去另外一个小站赶火车。
哪里有什么出租车,只停着几辆老式的北京吉普。我走过去便有人过来搭话,他们开口就要60元。要知道60块钱当时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见面砍一半儿,我说:“30块。”他们笑起来,我又说打计价器,他们更笑了,事实上这种车根本就没有计价器。几番讨价还价,我仍然坚持,便有人揶揄着城里人,也有人揶揄我是女人,背身走开了。一人说:“你再加点,40。”“35吧。”“走吧。”
司机算不上很健谈,但看上去还随和,开始两人都沉默着,我主动攀谈起来。他说看我是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不容易才拉我的,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40块值不值了。
吉普车在大山的山坳里穿行着,20分钟过去竟不见一辆并行的或有对面的车驶过,面对这空旷的山谷和陌生的司机,我开始有些不安。如果这人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我将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我后悔一上车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此刻,我方意识到刚才的讲价是多么可笑,仿佛我已把生命整个交付出去,自已还不知道,还后悔上车前竟连车牌也没有看一眼。作为补救,我转过头去,借搭话儿的机会,希望更清楚地记住那个人的长相。可在那张东北人特有的骨骼舒展的脸上,我感到的却是北方人的憨厚和直爽。他说,翻过右边的那座山,再过去一座山,就是他的家,也是杨子荣牺牲的地方。他见我表现出兴趣,便说可以带我去,正好还可以去他家住上两天,看着周围的大山。警惕又回来提醒我,我马上婉言拒绝了。
大约一小时,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另一个小站。司机先一跳下车,说“到了!”我长呼了一口气走下车来,掏出准备好的35元,他接过钱去的一刹那,我忽然感到一股歉意涌来,正要再掏钱出来,他说:“时间还早,你等也是等,吃了午饭再上火车正好。”我马上赞同,并说我来买单。他也不拒绝地说道:“谁买还不是一样。”
他带我走进小站附近的一家饭馆,临窗坐下来,他说从这个窗口,扭头就能看到进站的火车。他要了一瓶啤酒,我们边吃边聊。遥望周围环抱的山峦,这大概是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我真的觉得这里很美。
他说:“你别看你到处走,也还是在大城市转,走到咱这旮旯可不容易,你真不该这么急着走,该到家坐坐,哪怕就住一天呢,也是来一趟,带点儿山菜走,现在咱这儿的山菜可受欢迎了。你也认识认识你大嫂,她那人待人更没说的,那年大伙让我从兴安岭抓回来,一个老爷们儿在外头白忙活几年,她连句叹气话都没有。”如果不是急着赶回去,我真的有些动心想认识一下这家人。我让他把他家的地址写下来,说下次再来一定去他家。他惋惜地说:“你们当记者的太忙,哪会有时间给我们这样的人写信呢,再来就更不容易了。”去结账时,他拦住我,说这是到了他家,应该由他来付。服务员也像是和他一伙儿的,隔着我去接了他的钱。忽然,我发现站台上已有一辆火车停在那儿,他说:“就是这趟,才停两分,快跑!”
我跟在他后边,拼命地往站台上跑。他拉着我,眼前的几百米显得无限地长。看着车厢门的脚踏板已经放下了,他说:“你把包给我,自己快上去,开车我也能扔上去。”我迟疑了一下,把包扔下来,一个人跑进站台,车上有两人早已伸手来拉住我,我上了车,车慢慢动起来,我见他紧跑几步,一使劲儿,把包扔过来,我接住了我的包——此行我全部的财物都在这包里。
现在已10年过去了,但我的生活渐入安定,生命走进不惑的时候,许多事情都已忘记了,甚至包括那些曾撞击命运的事件,可那个小站、那位司机的形象,却不时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我甚至已记不起那个司机的名字、那个小站的名字及那件事确切的时间,但这些好像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件事就像熬了又熬的老汤一样,时间越久越浓越醇。
心灵智语
贴心的记忆与美好的过往,总会在人生不如意之时在心头回荡,仿佛是寒冬的火焰,又像是早春的细雨,温暖与滋润着倍感劳累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