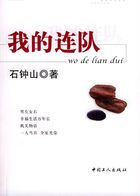在长期的历史流程中,中原子民对西域的想象,仅仅止于楼兰。
对他们来说,楼兰简直就是西域的同义词,是大漠的同义词,是战争的同义词,是死亡的同义词,是建功立业的同义词。楼兰成了一个标志性称谓,一个一段历史记忆的方尖碑,一个中国人对太阳落山的那西地平线的玫瑰色的梦想。
而助长这一代一代人的想象力的,是那些碑载文化,是那史书中的描写和汉唐诗人那天才的吟唱。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中,楼兰话题占了1这么多篇幅的原因。
其实那时候的西域,有许多的国家。楼兰仅仅是其中之一。那么有多少个国家呢?“西域一十六国”这个说法,是冒顿文书中的说法,这说明匈奴那时候还没有涉及到西域纵深。后来大约是张骞回来说,有二十六个,再后来大约是班超回来说,有三十六个。再后来,不断地有人回来,又有发现,于是人们厌倦了确切的数目,而以“西域三十六国”这句话作为虚数使用。
在那个时候的西域,人流的大迁徙像潮水一样的奔涌不定,英雄美人们列队走过御风而行,驼铃丁冬响彻晨昏,那一个一个的小国也许在早上立国、而在黄昏就告终者比比皆是。那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期。那里面该有多少历史细节在的。
史学家把那个时期叫作中亚古族大移位时期。
汤因比曾经无限向往地说,假如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生在屮亚,因为那是一块多么神奇的土地啊!汤因比还称那一块地面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因为世界三大游牧民族欧罗巴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后两者都消失和沉淀在茫茫大漠中了。
这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大部分都迷失在路途上了,将它们的如何发生和如何结束写出来,那会是一本大书的容量。
因此我们还是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楼兰这个话题上。我们毕竟对楼兰知道得稍微要多一点,它毕竟是我们中原子民心目中的一个西域标志物。
在有了本书上面谈到的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之后,这个从遥远的爱琴海迁徙至罗布泊的欧洲种族,后来怎么样厂呢?它是如何灭亡的?那些楼兰遗民最后的去踪又如何?那楼兰城还在吗?那充满神奇的千棺之山,是臆造还是确实存在过?而那罗布泊,它如今的情形又怎么样了呢?
楼兰国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的时候,亡于一个叫“丁零”的中亚古族手里。
“丁零”是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告诉我们,现在的维吾尔族,它在成吉思汗之前,称回鹘、回纥,而在回鹘、回纥之前,称丁零,这样我们知道了,楼兰国是这样灭亡的。
北匈奴是在公元2世纪开始西迁的,大约在匈奴离开这块地域之后,力量对比失衡,中亚古族之间开始进行新的一轮大移位、大兼并,这时候,在某一个早晨或黄昏,楼兰为丁零所灭。
楼兰那时候已经不叫楼兰,而称鄯善,它是在耆公子即位后易名的。
而楼兰国的国都那时候也不在罗布泊岸边的楼兰城了,抑或是由于战争,抑或是由于瘟疫,抑或是由于罗布泊位移而引起的干旱,它们的国都曾数度搬迁。几天前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上面有一条消息说,现代科学家用卫星红外线测试,确定楼兰城的被放弃是由于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的入海口改道,从而导致楼兰城的干旱缺水所致。)而灭亡之前的楼兰城的子民,除了那些遥远的迁徙者之外,它还在公元2世纪时候接纳了从阿富汗高原上过来的贵霜王朝的遗民。
贵霜王朝是当时与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安息王朝并称的世界四大帝国之一,然而它由于至今我们还不知道的某种原因,突然灭亡了。于是,它的遗民们大量涌向中亚地面,而以涌人楼兰国的人数为最多。——为我们提供这一段历史的,是一种叫怯卢文的灭亡了的古文字。
怯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它成为官方文字,而后来又成为贵霜①贵霜王朝在公元3世纪时分裂,在5世纪时灭亡,这是《辞海》中的说法。本书在这里采用的是中国社科院楼兰问题专家杨镰先生的观点,仅为一家之言而已。而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原来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着一些印欧语系的种族,使用怯卢文。后来他们迁徙到阿富汗高原上,建立了贵霜王朝。这一王朝后为迁徙的匈奴人所灭。
王朝的官方文字。奇怪的是,贵霜王朝灭亡之后,怯卢文却又在新疆的于阒、龟兹、楼兰等王国流行起来了。
而在楼兰国,怯卢文甚至成为与汉文并用的官方文书用字。
是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险者和考古工作者们,从和田地面发现的马钱上,从楼兰城遗址找到的木简上,发现这种文字的,然后进一步追根溯源,从而推理出这一段历史人流的走向的。
但是不管是这些先到的人还是后来加人的人,随着楼兰国的灭亡,他们也都像水一样在沙漠中蒸发了。所有的史书都以惆怅的口吻说:人民流亡,茫茫而不知其所终。
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和值得赞叹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史书上大而化之的记载,而硬要刨根问底、寻找这些楼兰人最后的流向,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历史乂将向我们展示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苦难的楼兰人,在楼兰城因为干旱缺水而被放弃之后,他们来到千棺之山,向列宗列祖做最后一次的祭奠,尔后,便拖家带口,向注人罗布泊的―条支流一一米兰河的上游搬迁。也就是说,水流是在那里断流的,他们便搬迁到可以遇见水的地方,然后水流又一次断流,于是他们又一次往上游撵。
他们把自己新建的村子,叫“阿不旦”,意即“有水有草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他们把每一个“阿不旦”,都当作自己永远的“阿不旦”,开始以最大的热情建设它,但是在居住匕十年、百年之后,都发现定居的想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水没有了,他们还得往前撵。
楼兰遗民在长期的演变中,被人们称为罗布泊人。
清朝的一位地理官员在撰写《西域水道记》时,曾经偶然走进过这罗布人最后的阿不旦。在他面前,是一幅凄凉的人类生存图景:他们几乎衣不遮体,他们居住在用芦苇和红柳条搭建的简易房屋中,他们的主要食物是从水中捞出来的大白鱼,他们生活在一群嗡嗡乱飞的苍蝇中间。
这位叫徐松的官员将他的惊人发现报告给了清朝政府。政府于是授予这个村子的族长以“伯克”之职,算是承认这些罗布人是他的子民。
后来,在1900年,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织驼队,寻找罗布泊确切位置,并因此行而意外地发现楼兰古城的时候,曾经从这个村子里,聘请了一位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
罗布人最后的消亡之地,是在我们前面谈到的那傅介子二十壮士囤垦的伊循城。
伊循城是一个着名的所在,高僧法显、高僧玄奘在西域取经归来之后,都曾在那里设坛讲道,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它还是马可,波罗丝绸之路之行路经和歇息的地方。
伊循城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的改名。它现在的名字叫米兰市。这是兵团人为它取的,取的理由是城市的旁边有一条米兰河。它现在属若羌县辖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驻扎在这里。
罗布人是在1921年离开阿不旦村的,罗布泊新湖一喀拉库顺湖的湖水一天天干涸,迫使罗布人只好一步一步地离开那凶险的地方,向后撤退,向塔里木水系尚留有一点水的终结处迁徙,而在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他们被接纳为兵团民族连的农工。
刚来兵团时,他们大约还有几十位吧!1998年秋天,当我随央视《中国大西北》专题片摄制组,来到这里寻找最后的罗布人的踪迹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当时一百零五岁,叫热合曼;一个当时一百零二岁,叫亚生。
在参观了那法显高僧、玄奘高僧曾经在此布坛讲道的着名的米兰佛塔之后,在参观了那有着犍陀罗艺术风格、吐蕃文化痕迹的米兰大寺之后,在那辽阔的郊外旷野上寻找罢那些人头骨、马蹄铁等等历史残片以后,我在最后的两位罗布人热合曼和亚生的向导下,穿过米兰河上的米兰桥,来到一一个叫阿拉干的地方。
阿拉干是一个地名。一百年前,这里是塔里木河咆哮地注入罗布泊的入海口。
塔里木河发源于葱岭。它在塔里木盆地绕了一个新月形的半圆之后,在收容了叶尔羌河、喀什喀尔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河等一系列水流之后,从此处注入罗布泊。
胡杨是中亚细亚的树木。胡杨是苦难的树木,和伴生它的楼兰民族一样苦难。当年,这里曾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林木,如今,它已经全部死亡了。
有些树木倒毙了,横躺在那里,你得迈过去。有些树木虽然死了许多年了,但是还端端地立在那里,在完成着它们早已确定的宿命。这些树木或站或立,模样却十分地庞大、粗糙、丑陋、可怕。那些像狮、像虎、像蟒蛇的丑陋外形,是时间的刀功,是岁月的产物。
出了林子,透一口气,向远处望去。流动的黄沙已经将塔里木河古河道填满,流沙呈现出一层一层的波浪,那是风的形状。远处有些沙包,那沙包也许是当年塔里木河高高的堤岸。沙包子上,偶尔会有一棵高大的胡杨,只剩下斑驳的树身了,像某动物的生殖器一样直翘翘地立在那里,苍凉,悲壮,举目望天。
执着我的手,最后的罗布人、一百零五岁的热合曼眼含热泪地说:“罗布人有许多东西遗忘在路上了,伹是,有一条关于胡杨的俚语,我还记得,这就是:胡杨有三条命一生长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朽一千年!”
我把老人的这段话,用作对“楼兰国的去踪”
这一节的总结,以及对那些所有的消失在路途上的人类子孙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