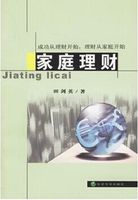按阶级分析的观点,贺盼水是绝对的赤贫,是绝对的依靠对象。在天津卫,像贺盼水这样境况的不少,至少占到四成。还有近四成情况稍好些,但也都是半饥半饱地打发着日子。夏满月、欧阳兰她们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做好贺盼水的工作,启发他的阶级意识,有助于天津卫整个群众工作的开展。
没想到,和贺盼水两口子的对话进行得十分艰难。
“像你们这种情况,家里有人给贺八爷扛活的,在村里还有多少?”夏满月问。
“……让我想想,东成弟兄俩,七爷家的贵才,十五叔,寡妇姨的老三,村西头的榆钱,六指,还有安吉,长吉,歪脖子榆树下的康娃,窑上的骚狸子,坟场的羊娃……还有几户外姓人,哪家都有一两个长工……哎呀,多了去了,一下子算不过来,二十来家三十家总是有的。”贺盼水瞪着眼睛想着,说着,一边看看他的女人。女人点着头,丈夫说一个,她扳着指头记一个,笑着。
“都在贺八爷家扛活?”
“嗯,天津卫就八爷一个大户,人家的势力大着哩,天津卫能浇上水的好地,跑死马,都是八爷的。”贺盼水的女人说,目光中流露出惊羡。
“在村里,你们这些长工是受他剥削最重的。”“啥剥削?”贺盼水问。
“简单点说吧,你们长年给贺八爷当牛做马,却吃不饱穿不暖,连个吃饭的囫囵碗都没有,你们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呢?都变成了贺八爷的高门大院,绫罗绸缎。这就叫剥削,贺八爷剥削你们,你们受他剥削。”夏满月说。
“咦,话不能这么说,人家八爷有地嘛。”贺盼水的女人说,一脸的迷茫。
“地如果没人种,能自己长出粮食吗?”毛丑女说。这个商会会长的使唤丫头,参加红军以后,她对宣传也很有一套了。
“他出地,我出力,两下不都有了?”贺盼水说。
“就是嘛。”她女人在一旁笑着附和说。
“你刚才说都有了--你想想,你有什么了?”夏满月问。
“……要是年景好,一亩地交过租子,起码还有一升半升的。”贺盼水支吾着说。
“大头却流到贺八爷的仓里去了?”又是毛丑女说。
“当然,地是人家的嘛,要是八爷不让你种,连这一升半升也没有,你还不是干瞪眼。”贺盼水说,显得平心静气。
说了一阵话,贺盼水夫妻觉得红军也都和气,一点也不凶,没有了开始时的拘谨,说话放松多了。
对于受剥削,贺盼水夫妻表现出来的平静,让夏满月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她又一次感到这地方太落后,群众觉悟太低。夏满月和毛丑女、陈秋儿对视了一下,她们脸上都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陈秋儿的感情应该更复杂一些,她参加这样的群众工作还不多,在夏满月营长、毛丑女她们和贺盼水夫妻说话的时候,每一句话她都听得很认真,她们的一些话在她听来同样很新奇。她想,那些话自己就说不出来。她觉得她们都很了不起。
夏满月有点悲哀,她觉得在红柳沟劝村民们返村时,讲了许多关于阶级的话,现在联系到他们自己头上时,却都又糊涂了,夏满月觉得自己那番话算是白说了。
“你们天津卫的这六十多户,除了三户外姓,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对吗?”夏满月换了个角度问。
“是的,先祖是抗清的英雄。”贺盼水说,目光明显开朗起来,“只可惜遇上了昏君,朝廷没法呆了,才跑出来,究竟是咋样来到这里的,头头绪绪多了,具体的我也说不上,你们问东头的望乡爷,他肚里装的多呢。我就知道我们的先人是个当官的,老家在天津,天津,那可是个大地方。”贺盼水说,显然,天津卫的人对自己的出身、祖籍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自古忠良多磨难,奸佞之徒乐陶然,《辕门》里杨延景唱的。”他的女人一边说,一边又给两个碗里续上了开水。
“你们想想,一个祖先留下的后代,为啥有的富,有的穷?”夏满月不想把话扯得太长,就这样问。
“命,全是命。戏文上说,各人有各人的造化。这话是守寒窑的王三姐对他那个当宰相的爹说的,造化可不就是命嘛……”贺盼水的女人说,显得很有知识。
贺盼水的女人动不动就搬戏文。
后来夏满月她们才了解到,贺盼水女人的前夫是凉州一个野秦腔班子唱青衣的,在凉州、张掖一带很有名气,后来得痨病死了。青衣死后,这女人又嫁给了一个民勤的骆驼客。只在一起过了三个月,骆驼客在往阿尔泰送茶叶的路上,又被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杀死在酒泉。连着死了两个丈夫,算卦的瞎子给这女人算命,说她命硬克夫,没有人敢再要。后来经人说合,嫁给了天津卫年近三十娶不上媳妇的贺盼水。由于以前跟着唱戏的第一个丈夫经常听戏,戏文便成了指导她处世为人的人生指南。和人说话,排解邻里纠纷,经常拿戏文里的句子引经据典。在村民眼里,她虽然穷,却是相当有见识的。
高台劝化--不只是在黄河北边这个小小的天津卫,在整个大西北的农村,戏文都在他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人生启蒙作用。
“你刚才说的命,其实是地主资本家用来欺骗穷人的把戏,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命,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们完全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夏满月循循善诱说。“改变,咋改变?”贺盼水说。
“受苦人团结起来,成立农会,拧成一个拳头,打倒贺八爷这样的土豪劣绅,自己当家做主人……”毛丑女说。
“就是……”陈秋儿说,她的声音很小。她觉得自己现在也是红军了,也应该说点什么。“哎哟,你凭啥打倒人家?”陈秋儿刚说了两个字,就被贺盼水的女人打断了。
陈秋儿的脸立刻红了。刚才说那句话时,她的心就“咚咚”直跳。被贺盼水的女人顶回来后,她更显得手足无措。“咱种着人家的地,再反过来打倒人家?仁义吗?那还不让村人的唾沫淹死了。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贺字,都是云鹏先祖的后人。”贺盼水接着他女人的话说。
“仁义?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老贺八爷手里有两条人命,现在的这个贺八爷又霸占了别人的五十多亩水浇田,你说,他们仁义吗?他们欺压乡亲们的时候,想过一笔写不出两个贺字吗?”夏满月一脸严肃地说。
贺盼水夫妻同时一怔,互相看了一下,目光露出惊讶,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红军是怎么知道的。
“那些……事情倒有,可是……”贺盼水的女人支吾起来,说话不像刚才那样利索了。“大叔,大婶,这就是恶霸,就是我们红军要打倒的对象。”毛丑女一旁说。
“可是……咱种着人家的地哩。再说,同宗同族,论辈分,我还把现在的八爷喊叔哩,死了的老八爷是爷爷辈。”贺盼水说着,指指媳妇,又说,“我娶她的时候,老八爷还给过三块光洋呢,这事咱一直记着,咱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
“就为了三块光洋,贺八爷家不但压榨了你一辈子,还在压榨你的下一辈。”夏满月说。贺盼水两口子没有马上回话,用狐疑的目光看着夏满月。“你的丫头不是在他家当丫头吗?”夏满月说。
“哦,你是指这个。那是,也是挣饭吃哩,谁白养活你呢?”贺盼水的女人说。
“他们家的八哥死了,说是你丫头喂水多了憋死的,把丫头打了个半死,耳朵都撕裂了。这还不说,贺诚还把那年你们的租子往上加了五成,说是赔八哥的,有这事吗?”夏满月又问。
贺盼水夫妻又对看了一阵,没有说话。
“你们不是同宗同族吗?”毛丑女一旁又说。
贺盼水的女人抬起头,翻了翻眼睛,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
“大叔,大婶,因此,同宗同族也是分为阶级的。在土豪劣绅眼里,咱穷人还顶不上他们养的一只鸟儿,是不是?今天,给穷人当家做主的红军来了,谁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咱们就把谁拉下来,打倒他!”夏满月说。
“那……不就乱了吗?”贺盼水吞吞吐吐说,
“要让天地翻个过儿,还能不乱吗?”夏满月说,她把小屋扫视一遍,最后目光落到贺盼水夫妻身上,说,“你们说,眼前这日子,你们愿意永生永世这样过下去吗?”
贺盼水的目光在夏满月脸上停了一阵,然后叹了一声,低下头去,好久没有说话。他的女人也老半天没有说话,起身往碗里续水的时候,甩下了几滴泪水。
屋里静了一会儿。
陈秋儿望着屋子的什么地方出神。夏营长刚才说那只八哥的事时,她忽然想起了大睁着眼、静静地躺在黄桷树下的哑巴爹,想起了拉着她,一路走一路吹着笛子的爷爷。
直到毛丑女拉她的胳膊时,她才从愣怔中醒来。她看见夏营长和毛丑女已经从坐着的地方站了起来,要走的样子。她也赶忙从炕沿上溜下来。
“想啥子呢,叫你都听不见?”夏满月笑着说。
“没……没想啥子。”陈秋儿红了脸说。
“不舍得走了?”
“不,不是……”
“不想走了就留下,给你煮洋芋吃,我家三亩旱地,种的洋芋个子不大,面得很。”贺盼水的女人说。大家都笑,看着陈秋儿。
“不,不,谢谢……”陈秋儿的脸更红了,那种慌乱的神情又出现在她的眼睛里--她习惯于永远生活在大家的视线之外,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谁都不注意她的时候,是她最轻松的时候。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她这是头一回。
陈秋儿低着头,跟在夏满月身后,像躲避什么似的,赶紧走出了贺盼水的破土屋。
她们已经走出一段路了,贺盼水的女人忽然在她们身后喊了一声:“长官!”
她们回过身来。
夏满月已经多次说过,红军里没有长官,都叫同志,但村民们总也不理会,改不过口,她也只好由着他们叫了。
贺盼水的女人迎着夏满月走了几步,站住,说:“长官,要我的时候,说一声。”
夏满月说:“谢谢,大婶!”
贺盼水的女人站在冷风里,目光定定地放在红军身上,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像骚动的黑烟。
往回走的时候,陈秋儿发现,夏营长的嘴角涌上了一些笑意。
看来,对今天这样的结果,夏满月营长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