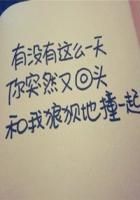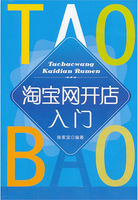雨一样的雾,雾一样的雨。一座丑陋的小茅屋。
男娃儿和女娃儿在低矮的屋檐下坐着,看着迷蒙的山,迷蒙的树,三头水牛在山路上慢慢走着,一群鸭子在竹林下的浅洼里缓缓游着。
男娃儿和女娃儿手撑着下巴,坐了好久。“甜妹儿。”男娃儿小声叫了一声。
“山娃子哥。”女娃儿哀哀地看着哥哥。“冷不冷?”男娃儿问。
“妈才冷呢,妈穿着单衣就埋了。”女娃儿说。“妈不知道冷了。”
“知道。”
“妈死了。”
“死了也知道。”
男娃儿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向女娃儿挪一挪,用胳膊搂住了她。
“山娃子哥。”
“嗯。”
“妈死了,谁管我们呢?”
“有我呢,我是哥哥。”男娃儿挺起了瘦骨棱棱的小胸脯说。
“你也是个娃儿呀?”
“可我是男娃儿,我是哥哥,我会钓虾,会放牛,还会扳鲜笋,会砍柴。”
“我给你洗衣服。”
“我不叫你洗衣服。”
“我能洗干净。”
“我要听你唱歌儿。”
“我天天给你唱。”
“你唱一遍《我看槐花几时开》。”
女娃儿看了看哥哥,嘴唇动了动,没有唱。她觉得自己的小脸蛋热热的。
“你唱一遍。”
“那是大人唱的,等我长大了给你唱。”
山更模糊了,树更模糊了。山路上的三头水牛总也走不到头,一群鸭子走出了浅洼,在岸上扇着翅膀,“呷呷”叫着。“山娃子哥。”
“甜妹儿。”
“妈说我不是你的亲妹妹,你说这是真的吗?”
“妈要我好好照管你。”
“你说那是真的吗?”“……真的。”
“真的?”
“嗯,真的。”
“我不信。”
“我问过舅公,问过水生他爹,还有桃花的瞎奶奶,都说是真的。”
“我朗格一点都不知道?”
“他们说,你亲妈把你丢到我家的时候你才半岁多。”
“不,不,这不是真的,你说的这不是真的……我害怕……”女娃儿惊恐地抓住男娃儿的手,使劲摇着说。
“你姓田,我姓胡。”男娃儿望着浸在似雾似雨中的山水说。
“不,不,你是我的亲哥哥!”
风大起来,雨大起来,山晃动了,树晃动了,三头水牛消失在山路上,那群鸭子不见了。男娃儿和女娃儿偎依着,悄悄地坐着。
“田教员!”那个战士回过头来,用诧异的目光看着田妹,“你喊我吗?”
“没有。”田妹说,雨雾中的竹竿河在她眼前消失了,她又走进了那片陌生的土黄里。那个战士在她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站着。
“你刚才说话呢。”战士说。“哦,是吗?”田妹含混地说。“你哭了?”
“我朗格要哭。”她努力笑一下。“你脸上有眼泪?”
“哦……土眯的。”她用手抹了一下脸。
他们继续向前走。现在,田妹走在了前面,那个战士跟在后面。
田妹觉着那个地方又热了一下,接着,裆又湿了一片。她想收拾一下。但他们正走一个缓坡上,没有可以遮拦的地方,身边又跟着一个男兵。她忍着。翻过缓坡,路的左边出现了一片颓败的矮墙,从土墙隔开的形状看,那里原先是几间房子,顶被扒光了,只剩下几堵墙。走近那些矮墙的时候,她对那个战士说:
“同志哥,你在这里等等我。”战士点点头,背过脸去。
田妹走过去,在土墙间看了看。转到一道土墙的后面,她看到了一片柴草烧过后留下的黑灰。她很高兴,走到那堵墙下,从挎包里抽出一块破布,用那草灰开始收拾自己。
草灰很干燥,也很干净,像是烧过没有多久,她收拾起来感到很舒服。
看到那些红,她的脸也红起来。世上的事有多巧,她想了第一次来红。第一次也是在去教歌儿的路上。
不过那时候走在她身边的是山娃子哥。
那时候她们正走在大雨过后的草地上,头上是明亮的太阳轻柔的白云,脚下是碧绿的水草和五颜六色的野花,以及把美丽的草地隔成碎块的水洼和河沟。那时候田妹脚步蹒跚神情慵倦,她机械地迈动着双腿,她眼前的草地,美丽得虚假而可怕。早晨,它刚刚夺走了疙瘙。疙瘙就死在她的身边,疙瘙死的时候身子使劲扭动着,脸抽得很可怕。她抱着她,哭着喊,怎么了?疙瘙你怎么了?疙瘙在她怀里只是扭动,抽搐,不说话。她央求她,不要走,你千万不要走,我们唱歌班已经走了三个了。疙瘙慢慢地就不扭动了,疙瘙就把脸冲着她,疙瘙就向她挤出了一点笑,然后疙瘙就死了……走在雨后的草地上,疙瘙那张抽得可怕的脸不断在她眼前重复着。
“当心水泡子,掉下去就完了!”她听见有人说话。她觉着自己的胳膊被一只手拉了一下,同时感到一只脚已经踩到了水里。
她从水里抽出了脚。
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了长着络腮胡子的易团长。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困了吗?易团长阴沉着脸问她。她摇一摇头说不困。易团长说困了我背你走一段。她说一点都不困。易团长说你轻飘飘的背你不比背一个手风琴更重--易团长行军时总背着一架到处都漏气的手风琴。她说不困,我真的不困,还甩开胳膊在他面前使劲走了几步,脚故意在地上跺出咚咚的响声。易团长阴沉着的脸舒展了。男兵女兵们都笑了。她也笑了。她问易团长还要走好久。易团长说他也不知道反正越走离革命胜利就越近。她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她问革命胜利了真的天天喝牛奶吃面包吗?易团长说当然。她问牛奶腥不腥。易团长说他也没喝过。她问喝不惯怎么办。易团长笑一笑说那有什么,喝不惯牛奶就喝排骨汤鸡蛋汤呗。她又问排骨汤鸡蛋汤天天都有得吗。易团长又笑一笑说当然,不然我们闹革命干什么闹共产主义干什么?她说共产主义真好,女团员们都拍手说共产主义真好。然后他们就小心翼翼地绕着水坑走路,肚子继续咕咕唧唧地叫着。他们暂时不去想共产主义的牛奶面包,贪婪的目光紧盯着脚下的一花一草,盼望着眼前出现奇迹:一个蘑菇或者一根可食的草茎。雨后的草地被太阳炙烤着,像一个蒸笼,田妹的梦在这燠热潮湿的蒸笼里发着酵。
“……山娃子哥,妈说过等咱们长大了我就给你当媳妇。”
“我不要媳妇。”
“为啥子?”
“我没得钱给你做新袄。”“哪个稀罕新袄。”
“我没得钱雇花轿。”“我不坐花轿。”
“不坐花轿我也不要你当媳妇。”“为啥子嘛山娃子哥?”
“媳妇不好妹子好……”
田妹被谁撞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她稳住神后看见一个背着枪的男兵擦着她的身子走了过去。那个兵走到易团长跟前,朝易团长敬个礼,把一个小字条交给了他,随后易团长就朝她们这边走来。当那个男兵随着易团长转过身来的时候,田妹愣住了。
那是山娃子!
山娃子愣怔一下,也认出了她。他还朝她眨了眨眼睛。人多,他们都没好意思说话。易团长走到她们几个女文工团员跟前停住了。易团长指指背枪的男兵说,三十四团向我们剧团要个教歌儿的女兵。
我去我去我去!女兵们争先恐后地喊着,疲惫怠倦的脸上放出了光彩。她们知道在战斗部队里女兵就是女皇,那些又憨又傻的男兵会争着把他们的最后一把青稞送给她们吃。她们实在太饿了。再说此刻她们真困真乏她们真想坐下来歇一歇。
易团长总是阴沉着的眼睛从她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扫了过去。“只能去一个。”他说。女兵们没有再说话,她们准备服从他的安排。
田妹的心跳得很厉害。刚才女兵们争着要去的时候她一直没有说话。自打认出山娃子的那一刻,她的心跳就加快了。她想自己的脸一定很红,她不敢看易团长,也不敢看那些女兵。她怕他们看出她想去的更多原因跟眼前这个叫山娃子的男兵有关。她把目光送出去很远,那边的水洼里,两只长脖子水鸟正在亲热的交喙。你呢,田妹?她听见易团长问,就把眼睛收回来看着他。易团长说你留下来跟他去三十四团好吗?她尽量抑制住兴奋,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我服从命令。易团长说去了要注意影响。她点一点头说我一定注意影响。这时疲倦和慵懒又爬上那些女兵们的脸。易团长又用阴郁的目光看了一眼山娃子,说你给我把人照看好了瘦了病了丢了我找你们团长算账。山娃子很认真地向易团长敬了个礼。然后易团长挥一下手,向他的部下冷冷地说了声“走吧”。这支被疲乏和饥饿裹挟着的小分队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田妹看着山娃子,眼泪从脸上簌簌地流了下来。面前这个山娃子是个嘴上长着一圈黑茸毛的汉子了。
从川北老家出来后,已经六年多过去了,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他们默默地站着,任泪无声地流,不知说什么好。
风撩动着他们的破军服,让他们感到了从雪山上走来的寒冷。
“山娃子哥!”田妹终于呜咽着叫了一声。
“甜妹,莫哭,你莫哭噢!”山娃子扶着她的肩,慌乱地说。田妹擦了擦眼睛,扬起头,朝山娃子笑了。
风大了,草地上发出“呜--呜”的风啸声,云迅速涌上来,蓝盈盈的天霎时变得混浊不清了。
“我们团在后面,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山娃子说。
“我真的乏了,天天走路真乏。”她说,在草地上坐下来。他也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坐近点儿。”她说。
他红着脸往她跟前挪了挪。“再近点儿。”
他又挪了挪。
“我冷。”她说。
“把我的衣服穿上。”山娃子动手解衣扣。
田妹抓住了他的手:“不,我要你像小时候那样搂着我。”他迟疑着,脸涨得通红。田妹咯咯笑着,倒在了他的怀里。
“山娃子哥,你想过我吗?”她问。
“想过。”他红着脸说。
“我可是常想你呢,刚才还想来着。”
“想啥子呢?”
“我要你娶我呢……”
风声大起来,满眼的红花绿草被大风摆弄着,齐刷刷地伏下去,又齐刷刷地站起来,无数个水洼被风吹皱了,掀起混浊不清的波纹,太阳躲到浓重的乌云后面,草地又变得阴森可怕起来。
田妹蜷缩在山娃子怀里,她从山娃子身上闻到了成熟男人才有的那种味道,那味道让她迷醉。
“真的,刚才我还想你了,我要给你当媳妇。”她喃喃着说。
他紧紧地搂着她,没有说话。
她从他怀里抬起眼睛,看着他说:“怎么不说话,我给你当媳妇你不要吗?”
“你胡思乱想。”他又红了脸。
她看着他,固执地问:“你真的不要吗?”
“你还小着呢。”
“你说实话。”
“革命成功了再……”他咽下去后半句话。“那得好久好久哟!”
田妹依山娃子坐着,看着云在天上疾走,草在地上摇动,她觉着自己心中正在燃起一团灼人的烈火。搂着她的山娃子一动不动,像一截木头。她想让他亲一下自己,把嘴唇向他凑过去。就在这时候,她觉得那个地方热了一下。
她的心有点慌乱有点紧张,在那一刻,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体验。
她听剧团的女同志说过那是咋回事。她从山娃子的怀里坐起来。
“把脸转过去。”她对他说。
“做啥子?”他不解地看着她。
“你把脸转过去嘛!”她又对他说,脸上浮出一片红晕。
山娃子把脸转了过去。
她用手在那儿摸了一下。她的指尖沾上了一点红。她惊悸不安,激动不已。从这时候起,田妹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以后她就和世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了,她要结婚,她要嫁给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红军,她要给他生娃儿,她要生一个男的再生一个女的。如果在老家,如果妈还活着,妈会像过生日一样给我煮一个红鸡蛋,她会给我一块红布让我把那个地方裹起来,她会说你长大了你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姑娘。可是没有妈妈没有红鸡蛋没有红布没有那些温柔的祝福,眼前只有望不到头的草地、阴云低垂的天和这个背朝着我的山娃子。你知道吗山娃子,你的甜妹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了,她在你的怀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几滴雨沉重地落了下来,打在她的头发上、脸上和手上,冲去了指尖上的那点红。她觉着又流出来一些,就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垫在。山娃子问干啥子哟我能转过头来吗?她说不能你再等会儿。他说下雨了你在搞什么鬼。她说我不能告诉你。她垫好布从草地上站起来,这时候他转过了脸。雨点很重但不密集,打到身上很舒服,风依然在稠密的野草上匆匆走着,低垂的乌云裂开了一条缝,一片明亮的阳光从那条缝隙里漏下来,照亮了一片晦暗的草地。田妹脸色绯红,在草地上跑着跳着,像一个快活的精灵。过了一会儿,她拿着几朵血一样的格桑花走到山娃子跟前。山娃子看着她脸上的绯红和手里捧着的红花,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喜欢血的颜色?她笑着说从今天起我已经长大了。山娃子眨着眼睛寻思她的意思。她歪着头把兴奋得发着光的脸对着他。他莫名其妙地摇一摇头说,你搞什么鬼看你高兴的?她红着脸说哥哥你真傻。她说她想唱一支歌儿。他说你唱吧我好久没有听你唱歌儿了。她问他想听啥歌儿。他说就唱《打刘湘》。她想了想说今天我不想唱《打刘湘》,山娃子哥,我还欠着你一支歌儿呢。他问什么歌?她说那年你让我唱我没有唱。他又问哪支歌?她朝他笑笑,没有说话,放开嗓子唱了起来:高高山上一棵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看槐花几时开。风把田妹的歌声远远地送到了正在艰难跋涉中的红军指战员耳朵里,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
那是田妹第一次唱这支家乡的情歌。
山娃子在这熟悉的乡音里看见了妈妈愁苦的脸。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妈说他有过一个父亲,妈说他的父亲在他过满月的时候离开了家就没再回来,妈说他的父亲是个好男人。妈每次说过父亲以后都要唱这支歌,那时候他和妹妹就趴在妈的腿上静静地听她唱。
“山娃子哥,你把这花给我别到头发上。”田妹唱完歌把那几朵花递给他说。
“戴花影响不好,地主小姐才戴花呢。”他犹犹豫豫着说。
“不要紧这阵没人我就戴一会儿。”
山娃子给她把花别到头上。
“我好看不好看?”
“好看。”
“要我做媳妇吧?”
“要。”
她又紧紧依偎在他的怀里,他用胳膊搂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