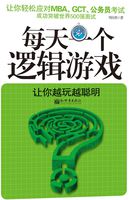或许我们从来不曾拥有什么。父母,金钱,灵魂,肉体,朋友,情人,爱人,都是虚幻不存在的,出现和消失只是轻淡的一抹缘,最终会化为乌有,一代一代如房檐水滴向下流传。
老人的七纸烧过后,任家玲回去自己家。家里养的几头猪早卖成钱给老人看病用了,粮食也粜卖了不少。原本残败的家,显的更贫穷了。
贫穷,往往不是因为我们吃不起饭,而是我们的收入只能有一少部分拿来吃饭。拖累农村人贫穷的不是收入的多少,是负担的大小,农村人的父母不是父母是负担。城里人的富裕,在于城里人家庭组成小,父母不是父母是富裕。
任家孝懂得这样的道理,任家孝日子过的比别人滋润,任家玲不懂,任家玲一直在贫困线和劳累中挣扎。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那么最大的公平就在于我们活的很辛苦,但我们干净。
家里只剩下任凡一个人的时候,恐惧肆无忌惮的张扬开来,在白天在黑夜,在家里的每个角落。自任静去了学校后,再没有人每晚蹦达着咯咯笑着来陪他说话聊天。王桂花倒是白天过来,带一些饭给任凡吃,晚上却门也不出,早早上了闩。
奶奶的影子还在半空中荡漾,有时候微笑,有时候哭泣,有时候鼓励任凡,有时候谩骂任凡不听自己的话自己死不瞑目。这种错综复杂的阴气或电磁波萦绕在任凡家的屋顶,让任凡越来越迷茫,越来越不知所措。
家里的粮食还有好些,这是家里唯一也是最值钱的财产。任凡不担心如何处理它们,任凡只想自己的路在哪儿,自己要去哪儿。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圣人,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和走过的路多一些,所以能够告诉别人哪条路好走,哪条路适合什么人走。但即便这样的人,在任凡身边似乎都很难找。大家都觉得上学是唯一也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但如果不上学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谁也不知道。
人无路可走的时候,都喜欢跳墙,那是因为墙低,要是悬崖,估计也就没有几个真勇士了。任凡还没有到要跳墙或悬崖的地步,任凡想像大多数村里不读书的孩子一样,出门打工,赚钱糊口。
任凡赚钱不仅是为了糊口,更多的是为了还债。照任凡的现状,任凡完全可以像亲叔叔任家孝一样对所有欠钱的人和银行赖账,做不要脸的事情,但任凡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奶奶不是,姑姑不是。
上学对任凡来说,是一个再美丽不过的梦,但奶奶的离去让这个梦成了噩梦。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无能为力让亲人们幸福的活着,但一定要让亲人们清白的离去。这也是一种孝道,是对长辈的爱。所以债要还,并且要尽快还。
任凡来到姑姑家。任家玲正从地里干活回来,满脸满手是泥。任凡帮忙打了盆清水,对任家玲说:“姑。家里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前两天我买了几袋肥料在地里撒了,麦子过几天种。家里还有几条翁粮食,我想给你拉过来。其它的就没有什么了。”
“放家里就行了,你以后还回来呢,拉来了,你回家不吃饭了么?”
“留一些就行了。”任凡做出开心的样子。
任家玲坐到院子石凳上,问任凡:“你准备去哪儿?”
任凡蹲到任家玲对面,说:“我想去西安。西安离家近,有什么事能及时回来,再说西安也是个大城市。”
“那你有门路么?”任家玲不无担心的问。
“我勇叔说,他有个朋友在西安的一家建筑队干活。听说好像有一点权利,能给我找到不错的活。”
“你看姑跟着你姑夫那没出息的,别说找个熟人,就连西安城在哪都不知道,也给你帮不上什么忙了。”说着任家玲将洗干净的手在衣服上抹抹,起身进了房子,顺便说,“你等一下。”
任家玲很快从屋子里出来,手上拿了三百元钱,说:“这却是有些少,你先拿着,过两天姑给你再找一些,你到西安去带上,出门在外能叫钱受罪,别叫人受罪。”
任凡回绝道:“姑,我有钱呢,不用了,你留在家里用吧,快种麦子了,需要钱。我前几天买了麦子,手里还有一些钱。”
“拿着。”任家玲眼里浸出了泪水,“不要嫌少。”
“姑,我不是那意思。”任凡急了,赶忙解释道。
“我知道,我知道。姑也没有什么意思。拿着吧。”
任凡看看任家玲看看手里的钱,接过来,说:“姑,我知道,这一次为了我奶,你花了不少钱,等我出去赚了钱,一定还给你。”
任家玲费力的摸摸任凡脑袋,说:“你奶不是我妈?我给我妈花钱还要别人还?”
任凡不再说话。
任家玲说:“你先坐到房子去,我去给咱们做饭,你姑夫一会儿就回来,咱一家人吃个饭你再回去。”
“不用了,姑,我先回了。勇叔家要瓣包谷,过两天还要挖红薯,说让我帮忙,给我发工资。我也趁这个机会锻炼锻炼自己,免得去了西安,人家工地老板不喜欢我这刚从学校出来的人。”
任家玲无奈的看着高她一头的侄儿,不知想哭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