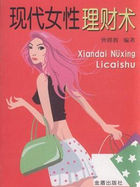因此,纵观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眼光的睿智广阔、心灵的丰富深邃,都体现在他们对存在世界的多重视界透视上。当然,艺术表现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是通过艺术家的个体敏感性来体现的,艺术创造无疑具体体现在结构的制作、语言和技巧的运用。但是艺术对人类精神、对存在世界的宏伟把握以及时代精神在文学艺术作品里的存在方式和形态,无不在视界融合里以整合原则表现出来。因此,视界融合就是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在人类文学艺术的整体景观上尤其如此。我们称之为艺术表现力的那种东西,并不只是技巧如语词的单纯运用。现代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拓展,人类精神的复杂性、深邃性和隐秘性,恰恰表明了用统合的文化观念来看待现代人生活的必要性。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在艺术表现技法上,很难确立一种线性的进化规则,然而在对世界存在、对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取向上,具有不断拓展“视界”的趋向。首先是政治上的反思,限定于对十年动乱的政治社会学批判;然后是审美观照,某种表现形式上的革新,汲取西方现代的艺术经验,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方式是新的,感情和思想都是陈旧的,然而,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视界,同样令人激动不安。历史视界和哲学视界的展开,使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寻根热”消退了,但它的意义决不是暂时的。尽管这里面有许多的褊狭、附会,但它显示了缺乏历史感的中国人正在开拓自己的历史视界,并且,这个历史视界一开始就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展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终究抵挡不住世界潮流的冲击。部分作家、诗人企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民族的文化心理,企图找到民族进步的现代精神依据。杨炼声称要“争夺历史空间”,在积淀的现实里获得一种历史同感。他的《半坡》、《敦煌》、《诺日朗》等诗,那些“发蓝的梦”,“孕育青铜的土地”,“成千上万座墓碑像犁一样抛锚在荒野尽头”,我--“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在这里,一个广袤的历史空间在古老的地平线上绵延,历史涵盖了一切,获得了无限性的证明。然而,杨炼的历史,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结,因而也没有归宿。那是一块“巨大的历史表象”--存在的幻象。历史没有现实的根柢,因而没有结果,困惑与迷惘是必然的。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总是企图获得某种历史的、文化的背景。拉美文学在当代的盛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重视,根源在于人们又一次意识到(并且是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站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人类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成为“地球村”的“村民的集体意识”。拉美所提供的一个古老文化的范本,高度压缩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可以说为现代文明提供了一个超历史的框架。因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导致了文学艺术偏向于“历史文化视界”。
三、文学视界的深度进向
文学视界有着自己强大的内在结构(二维结构)、历史跨度与深度进向。文学对存在世界的感悟,是对人类存在的“现实情态”的领会,说到底,文学视界的多重融合,也就是对这个“现实情态”的全面展示。这个视界有坚定的“历史”或“传统”在支配着。人类的文明既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也有无穷循环的深度性,因而,它表明了主体的现存状况,也抛离了主体而无限“伸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视界”,无疑有超主体的“客观”有效性。主体在历史中的活动通过现实延续下来,“视界”并不只是主体在特定境况中的自我观照,“视界”具有“巨大的历史跨度”--极其广阔的历史视域,标明人类“进步”的有限性。全部历史融解于现实之流,而现实总是蕴涵着所有的历史隐含。因而,人类对自身现实存在的感悟,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历史心灵的领会。因此,“文学视界”不过是主体现实情态的客体文化样态,--它形成了那样一种传统,那样一种结构,那样一种方式,仿佛从遥远的“彼在”俯视着“此在”。“视界”涵盖了“此在”,然而又不属于“此在”,它总是一如既往把“此在”置于它的支配之下。人类所有的现实的实际活动,终究都要转为一种观念形态而获得它的确实性,而人们的那些活生生的感情,具体的情境生活,反倒是在“视界”里才证实了它的存在的有效性和无限性。“希腊人”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希腊城邦的那种生活,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才获得了某种“真实性”的氛围。同样的,我们的现实,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无所谓于它的“真实性”和“实在性”,只是到了未来,“现在”成了历史,并已融入了历史,才获得了某种根柢。“现在”是历史的无花果,“文学视界”无疑是人类这一创造主体的创造物,然而“人类”在这里,只能是一种“历史主体”,也就是说,它是“历史地”生成的。它只能与主体的历史过程相对应,任何个体的现实行为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小视域),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构成了那样一种传统,构建起文学视界的基本结构,而那些杰出的非凡的心灵,一再地在视界里显现,预示着某种征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很难在“视界”里断然划出“历史区域”,视界总是不断地拓展。尽管在这里一种“视界”总是为另一种“视界”所超越,但是,一种“视界”从来没有为另一种“视界”所代替,它们都没有超出视界的“跨度”,不过是拓展了“跨度”而已。因此,我们称之为“风格演变”与“艺术创新”的那种情形,完全取决于看待问题的历史视角。在欧洲艺术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从罗马到哥特式到巴洛克再到洛可可的风格的演变,我们可以说从荷马到尤奈斯库,艺术观念和技巧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历史的终结”,有一种强大的历史延续性贯穿于其中。在兰德尔看来,希腊人建立了一个理智的世界,他们发明了各种特质,而且以它们为依据建立了有秩序的理智生活。自那时以来,很多人进行了一连串的尝试,想用希腊思想解释新颖的和陌生的经验。当然,现代人未必就那么拙讷,希腊人也未必就那么伟大而不可超越。只是人类的观念从来没有抛弃什么,它只能是“发展”了什么;在文学视界里,它只能是“拓展”了什么。“拓展”就是获取“跨度”,它充分显示了文学视界是人类作为一个创造主体与世界历史不断对话的特殊方式。
文学视界企图对人类精神的能动里程做有效的全面把握,造成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跨度。然而,人类精神走着自己的路,文学(艺术)不过是精神的象征性的语言,它的隐秘的动机、它的心灵、它的痛苦、它的意志,只有到了人类精神的边界上才有可能被理解。正因为此,文学视界在冥冥之中探求精神导向。有形的世界仿佛都是暂时,只有那无形的、不可见的世界是永恒的。它只能被想象和体验到,却是无边的神力的总和--精神的深度进向。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爱琴海上的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和迈锡尼世界,各自怀着不同的心灵,前者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默默地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而后者在热烈和光辉里不可遏止地奔腾向前,它把所有的重大的问题都抛在自己身后。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然而各自显示了自己的深度性。确实,“风格”是在自己的文化里获得了坚实性,风格并不是静态地维持它的形态。正是“视界”所蕴涵的那样一种深度进向造成了风格。因此,我们理解文学视界里的深度进向基本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