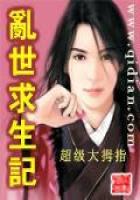第二日一早,天色朦亮,穆勃便被一群人押至府台衙门。三声威喝之下,刺史大人已然端坐于高台之上。穆勃打眼望去,这位刺史大人黑黝面皮,一对三角眼,颌下三缕短须,未及穆勃开口,手拍惊堂之木,一口山南土音,喝问穆勃道:
“堂下犯人是哪里人士?叫做什么?有何功名?所犯何事?”
听此言语,穆勃虽然跪地,但却傲然挺身朗声答道:“在下穆勃,字嗣业,山南道人士,出身乡野,虽暂无功名,但在下一向清白守法,今日就要投奔河西军镇,誓要戍边立功。昨晚在客栈夜宿时搭救一位受当地恶霸欺辱的女子,将其安置在客栈当中,寻思着今日护送她到府衙,求募兵的军爷帮她在此处寻个营生,却未料到昨晚竟遭此大祸。那女子惨死实乃遭歹人陷害,非我所做,请大人明鉴!”
刺史大人低声沉吟片刻,并未回应穆勃,只是喝道:“带小二来。”
店小二刚被衙役带上来,立刻双腿扑通跪下,直叩响头:“大老爷在上,受小人一拜。大老爷,我是客栈伙计,因老板不在,店中一切由小人打理,------。”
堂上的刺史面露厌烦之色,连咳两声,打断小二的话,说道:“本官断案,只需知道昨晚发生何事,莫要啰嗦。”
店小二一听,复又磕头,哆哆嗦嗦说道:“大老爷明鉴,这个汉子,强留客栈,不但不给房钱,还调戏民女,夜宿客栈。半夜我等听到惨叫声赶到时,只看见这个无赖拿着凶器在屋里,他要行凶害人,不,他害死了人,还要害我,与小民毫无干系,毫无干系,大老爷要给小民做主呀,严惩这个恶犯。哦,对了,他还欠我房钱。”
穆勃一听,怒火愤然,听到这个小二不仅语无伦次,还为了给自己洗脱干系,随意颠倒黑白,顿时想上去猛揍于他,但未及起身,便被两旁衙役用水火双棍死死按住。
刺史一见,手拍惊堂木,喝道:“大胆人犯,我看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寒士,又无功名,看着供人之词,想必实有其事,若再敢在公堂行凶,当堂杖毙。”
言毕,刺史问堂下的长史:“那女子的尸首和犯人的证物情况查验的如何?”
那长史起身,朝刺史微微一躬,答道:“大人,经仵作查验,被害女子全身赤裸,头颅不见,身上多处剑痕,但非致命之伤。案犯随身包袱一个,宝剑一把,良马一匹。经查,剑上血迹与尸首相符。”
穆勃听完,忙呼声叫冤:“大人,那剑上血迹是我进房时用剑挑起帷帐查看时沾上,此事并非小人所为,还请大人明鉴。”
“住嘴,大胆案犯。你说你是清白的,可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另外,我且问你,我看这宝剑良马都是不俗之物,你又不是当今十二世阀大家的良家子弟,怎么会有此物件,想必也是偷盗而来。来人,让此案犯画押,打入死牢。”
穆勃一听,顿时如五雷轰顶,心中想到如此官吏只看出身门第,功名家室,不问世事原由,不愿思索细琢,只是粗潦判案,黑白颠倒,草菅人命,怎能不让人激愤不已。穆勃大喝一声,挺身站起,掀得两边的衙役直刷刷的弃棍踉跄摔倒。刺史一见此情形,神色慌慌张起来,颤颤说道:“堂下人犯莫不是要造反吗?”
穆勃朗声答道:“大人,在下绝无此意,此案冤枉,请大人再度明察!”
见穆勃没有动粗之意,这位刺史正了正身,一拍惊堂木,却又低头沉眉,半晌未有发话。一时堂中静默。
突然刺史大喝一声:“众衙役,将人犯拿住,当堂杖毙!”两边衙役听此号令,一哄而上,准备动手之时,只听见外边一声炸喝:“慢!”。
衙上众人一抬头,只见外面一位虬须满面,虎姿勃勃中年军汉扛着一个麻袋走进衙内。穆勃一见,来人正是赫连直。
只见这赫连直大步流星,来到堂前,放下肩上麻袋,抱拳向堂上刺史行军礼,出声如雷:“大人,小人安西节度使麾下碎叶军镇折冲三府果毅都尉赫连直。奉都护府军令前来贵地募兵。今日堂下犯人曾来过府衙,和当地一个叫做阴半城恶人交手,被我撞见。我料那个姓阴的不会善罢甘休,特暗地跟踪于他,让我发现了他们干下的害人勾当。”
言毕,打开布袋,堂上众人定眼相看,只听到一声“啊,有鬼呀。”那个小二当场晕倒。原来那袋中装的不是旁人,正是众人以为遭到毒手的菊儿姑娘。如今却又死而复生,才惊得那小二直晕过去。
穆勃也是吃惊不小,心中暗暗想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惨死在床上的又是何人?不及穆勃细想,赫连直开口说道:“昨日下午,我跟踪阴半城,见到这个妇人,她不过是那个姓阴的姘头,却心如蛇蝎,为那个姓阴的出谋划策,两人做戏,先引这个年轻人上当,以为此女子受到欺凌,留她在客栈过夜,半夜用她人尸首置于房间,再以声响引得穆勃进房上当。那个姓阴的先前贿赂店小二并哄骗其半夜会让女子遁走以诬陷穆勃。谁知这二人一不做,二不休,弄个尸首在店铺里欲置穆勃于死地,真是害人害己。今日本都尉路见不平,本想将那个姓阴的擒来,不料让他逃脱,只将这个恶妇捉来,请刺史大人详加盘问。”
那店小二此刻已经醒来,听到赫连直所言,颤颤巍巍,忙不迭捣蒜般叩头认罪:“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小人不过是贪图几两碎银子,不,小人是被那对恶人所逼,迫不得已,才按他们吩咐办事。没想到惹来这么大的祸端。真是有苦说不出。全怪那对狗男女,他们做下此等恶事,跟小人无关,望大人明察,大人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