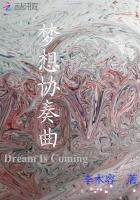一个大院子里容易出产两种人
烂混混和好书生。
就像是离开了兰若寺,从此以后天涯千里,聂小倩要去转世,而宁采臣只能在心里留一个淡淡的影子罢了。
所以苏文微和凌越即使从小就一起长大,两个人有相守的心,却没有相守的能力。有缘无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同一个院子里出产两种人并不稀奇:譬如烂混混和好书生。
大院子简直像是兰若寺,里面什么都有。捉妖的燕赤霞,懵懂的宁采臣,纯良的聂小倩,张狂的黑山老妖……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我是那个口耳相传的烂混混,只不过我是一个女孩子,所以背负着这种好名声,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一个女孩子要做混混,比男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一些吧。其实也不外乎就是打架,逃学,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
而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人。一个书生,一个很漂亮的书生。他长相当真秀气漂亮,据说他长得很像日本漫画里的美少年,尖削的下巴,冷淡的眉目,一张脸堪比大功率发电机,上到院子里只会搬板凳出去晒太阳的孤寡老太,下到楼上不懂世事咬着棒棒糖流口水的年幼萝莉,都觉得他好看。他就是大众情人。
那是凌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本院考上一中的第一人。他在长辈中素来以头脑聪明、得体有礼出名,而在同龄女孩子中则以相貌酷似某某英俊明星享誉于世。
我却只觉得,也许我们院子真是风水不好,于是这么多年才出产了一个上了一中的人。当然他家里不是这么想,他们觉得凌越太他妈出息了,简直都可以当选国家元首了那么把牛都逼死了的牛逼。
你说这么厉害的人太阳系行星怎么还不以他为中心进行公转?
偏偏那天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他不在家,邮递员倒很精明,懒得再跑一趟,就按了我家的门铃。是啊,我考上的高中简直报道就可以去,哪有什么录取通知书。所以现在我是待业青年,无所事事。
我帮他签了字,签下“凌越”两个字的时候我有些别扭。
其实我的字和他的字一点都不像。我写字才像一个男孩子,不会连笔,规规矩矩都看起来有些凌乱,而他的一笔一划犹有风致,不愧是跟着本县县太爷——好吧,县长大人学过几年书法的人,他的草书看起来都工整平实。
他爸妈回到家,很惊讶地说别人的通知书都到了,怎么我们家小越的还没到。当时我真的很想就此不把通知书给他。结果他特别淡定地跟他爸妈说,没事的,反正一中那边就算没通知书老师也认识他。马勒戈壁的啊,成绩好就那么了不起么?
等晚上他下去倒垃圾的时候我也下去了,把通知书递给他。
给他的一瞬间,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悄然滑过我的心底。那是一种怅然若失,无数次,和他相遇的无数次都在咬噬我的怅然若失。就连他和我的区别,哪里仅仅是一封录取通知书呢,还有很多很多,全部归于这个世界的三六九等人设,全部都在我们之间划下一道银河。也许牛郎织女什么的还能一期一会,我跟他的银河却是一辈子都不能跨越的了。
他还是伸手接过来,手指擦过我的指尖,他的手指一向很凉,偏偏是我的手在发烫。他细致地看了我一会说:“就知道是你拿了。”
“为什么?”
凌越半低着头说,语调波澜不惊:“因为你今天在家。通知书一般不可能会寄丢,超时这么久,一定已经收到了。如果没人收下,邮递员应该会打我爸妈的手机,我留了电话。可是没有,我想应该是你签收了。”
逻辑真好。这小子的确是凭非凡的头脑才可以考这么好的。而且他一样一样对我分析出来,这人话真多,他对别人可不是这么多话的。
我笑了笑:“那么,恭喜你。”
“有什么好恭喜的?”凌越仍旧没有抬头,语气里有些愤怒,“就是有高中可以念而已……每天三点一线,没什么不同。”
“拜托,大爷,你还想怎么样?”我自哂,“难道和我们这种人一样,每天吃吃喝喝嫖嫖赌赌勒索小学生打架闹事很有趣么?知足吧你。好日子过惯了,怎么着,您青春期了叛逆了啊?还要有多不同啊。”
凌越把垃圾丢进垃圾桶,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也一并扔了进去,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喂,你干什么!”
他冷淡地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教室就开始读书,实验班的学生连厕所都不去,也不喜欢和同学交谈,习题可以堆得比人还高,考上清华北大就觉得自己出人头地了,怎么不觉得自己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呢?”
我又好气又好笑:“你还会开玩笑?我以为你的脑瓜子只会读书。”懒得理这人,我把垃圾桶倾了一个角度,他很诧异:“你要干吗?”他的通知书就在最上面,我用两个手指头捡出来,还好上面只沾到了一条丝瓜皮,我将它拈下来扔掉,再用手指擦掉了通知书上的痕迹,“喏,给你,你别跟自己较真啊。少不懂事了。”
凌越皱着眉不肯接:“很脏,你干嘛这样?”
忘了,这个王八犊子有洁癖。真是惯坏了的毛病,一看从小就穿金戴银生活得不同凡俗,快不食人间烟火了,才有这种矫情无比的癖好。
“凌叔叔陆阿姨不会觉得脏。他们就期待看着这张大红纸高兴高兴、炫耀炫耀了。你别自己清高,就不管你爸妈怎么想的。”
凌越沉默一下,接过录取通知书,谨慎得只用两个指头拿再离自己两拳的地方,我看得好笑,他却问我:“那你……那你呢……要去哪里?”
我知道他问得很感慨,我也有点尴尬地笑:“得了吧,凌大人,我们这种人还能去哪里,职高混日子吧。”
凌越勾着半边嘴角,自以为很讽刺其实跟偏瘫似的笑了起来:“什么叫‘你们这种人’?我在想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地和我说话。”
我偏了偏头:“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装作不懂这个道理,还要我自己亲口说出这些客观事实来。
“那我们是什么?”
我有点慌,那边正好有个人影,估计是晚上出来散步消食的街坊邻居:“我不跟你说了。你看有人来,小心别人看见我跟你说话了,多不好。”
我也不等他说什么,就匆匆忙忙地跑掉,而凌越也没有伸手来拉住我。
是啊,是啊。因为他没有来拉住你,所以苏文微,你跑得如何跌跌撞撞,脚底流脓,也不能够停下来,不能够回过头去。
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