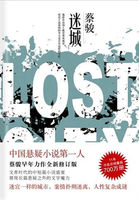第四十章一次公开的争吵:一个最后的呼吁
后来并没有实现散场后的游乐,至少对嘉莉来说是如此。她往家走,一心想着她没有回家的事。赫斯特渥特已经睡了,不过她走过他身边往她自己那张床走去时,他坐起来望了一眼。
“是你啊。”他说。
“是的。”她回答说。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她觉得该道个歉。
“昨晚上我实在赶不回来。”她说。
“啊,嘉莉,”他回答说,“这样说有什么用?我并不在意。你不用跟我说这个。”
“我回不来,”嘉莉说,脸上泛起了红晕。然后,见到他那个神气仿佛在说“我心里有数”,她就嚷道:“哦,好吧。我并不在乎。”
从这以后,她对这个家的冷漠就越发加深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了谈话的共同基础。她只是等着被要求负担开支。而他呢,对于要自己开这个口,也恨得什么似的。他宁可在肉店和面包店赊欠,他在奥斯洛格杂货店欠下了十六块钱的帐,贮藏了不少食物,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必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又换一家杂货店。对肉店和其它若干店家也如此办理。嘉莉从没有直接从他那里听到过这些情况。他能讨多少就讨多少,如此的局面一直拖得相距越来越远,最后只会有一个下场。
就这样,九月份过去了。
“杜雷克先生打算开办他的旅馆么?”嘉莉问了好几回。
“要开的。不过,如今他在十月份以前不会开。”
嘉莉变得厌恶起来了。“这么一个人!”她时常心里这么说。她说去访友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她多余的钱多半花在衣服上,这毕竟是个惊人的数字。后来,她参加演出的那个歌剧,宣告要到外地巡回演出四个星期。“喜歌剧大获成功,最后两周上演——”如此等等,这样的海报到处张贴,报上也登着。当时,她还没有采取行动。
“我可不去外地巡回演出。”奥丝蓬小姐说。
嘉莉跟她一起去找另一位经理,向他提出申请。
“有过什么经验么?”这是他提的问题之一。
“我眼下在卡西诺剧团。”
“哦,是么?”他说。
结果是订了另一个合同,每周二十块钱。
嘉莉很高兴。她感觉到自己在这世上有了个地位。人家承认了她的才能。
她的境况这样一来,家里的气氛便变得无法忍受了。在那里,只有穷困和烦恼,或者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它只是一种负担。它成了避之犹恐不及的去处。可她还睡在那里,还干不少家务活,搞得井井有条。那是赫斯特渥特坐的地方。他坐着,摇晃着,看着报,把自己泡在自己命运的阴暗气氛之中。十月份过去了,又是十一月。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严冬降临,而他还坐着。
嘉莉情况好些了,这他知道。她的衣饰有所改善,甚至可说是漂亮了。他如今见她来来去去的,有时候也曾在心里描画着她发达的光景。吃得少了,他多少瘦了些。他胃口不开。他的衣服也是穷人的衣服。寻找活儿干的话已经变成陈腔滥调,成了对他的嘲讽之词了。于是,他就叉起双手,静等着——等着什么呢,这他自己也不可能预见到。
后来,烦恼变得越来越多了。债主的催索,嘉莉的冷淡,家里的寂然无声,冬天的来临,一齐合起来形成了高潮。直接触发的,是奥斯洛格亲自登门,当时嘉莉也在家。
“我上门是为了我的帐。”奥斯洛格先生说。
嘉莉只是略感诧异。
“多少钱?”她问。
“十六块钱。”他回答。
“哦,这么多?”嘉莉说,“是这个数目么?”她转过身来朝赫斯特渥特问。
“是的。”他说。
“嗯,我从没有听到你说嘛。”
她那神情仿佛表示她认为他花了不必要的开支。
“嗯,我们是欠了这些钱,没有错,”他回答说。然后他朝门口走。“今天我可什么都付不出来。”他和颜悦色地说。
“嗯,那你什么时候能付呢?”杂货店老板问。
“反正星期六以前不行。”赫斯特渥特说。
“嘿!”杂货店老板回答,“这倒好。我非得收这笔钱不可。我急需钱用。”
嘉莉正站在房间的那边一头,全听到了。她非常难过。这太糟了,也太无聊了。赫斯特渥特也很懊恼。
“嗯,”他说,“眼下讲这些没有用处。请星期六来吧。到时候我总付些给你嘛。”
杂货店老板走了。
“你怎么付这笔帐呢?”嘉莉问。她对这笔帐颇为吃惊,“我没有力量。”
“嗯,不用你付,”他说,“他拿不到的,他得等。”
“我不懂我们怎么会欠这么多的。”嘉莉说。
“嗯,我们吃的。”赫斯特渥特说。
“真怪。”她回答说,心里还是疑疑惑惑的。
“你这样站着讲这一些,有什么用?”他问道,“你以为是我独自一个人造成的?照你说的,仿佛是我得了什么?”
“嗯,反正这太过分了,”嘉莉说,“不该叫我付这笔钱。我眼下也没有这么多钱付。”
“好吧。”赫斯特渥特回答说,一边默默地坐了下来。这样折磨人,他也受够了。
嘉莉出了家门,他坐在那里打定主意要干些什么。
当时报上盛传勃洛克林的电车工正酝酿罢工。工人对工时和工资,普遍感到不满。按照老规矩——理由何在也有点说不清楚——工人挑冬天对老板施加压力,要求解决问题。
赫斯特渥特一向在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消息,心想随之而来的罢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在他和嘉莉产生纷争以前的一两天,罢工开始了。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天灰沉沉的,像下雪的样子,报上说,所有各线上全都罢了工。
赫斯特渥特完完全全闲着什么事都没有干,加上心里尽是有关今冬工作机会少、金融市场恐慌等等无数的预言,所以他非常注意地读着这些消息。他注意到罢工的司机和售票员提出的说法,说过去他们每天工资两块钱,不过,一年多来,实行了“论班临时工”制度,把他们赖以生活的机会砍掉了一半,把苦役时间从十个钟头增加到了十二个钟头,甚至十四个钟头。这些“论班临时工”是在忙碌或者“高峰”时间安排上的。只开一次的车,这样开一次车的报酬只付两毛五分钱。忙碌时间或高峰一过,他们就给撤下来。最糟糕的是一个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车。他必须一清早到车厂来,不论天气好坏,等在那里,一直等到需要他的时候。这样等候的报偿,通常是出两次车——三个钟头多一点,五毛钱。等候并不算钱。
工人抱怨说,这个制度还在推广开来,很可能不用多久,七千工人中只能有少数人能干到每天两块钱的活儿。他们要求取消这个制度,每天工作只应是十小时,无法避免的迟误除外,工资每天两块两毛五分钱。他们要求立即接受这些要求,而各家街车公司则加以拒绝。
赫斯特渥特开头同情这些工人的要求的——是啊,他是否一直同情他们到底,这可是个问题啊,后来他的实际行动可拆穿了他的谎话。他把所有的新闻都看遍了,最早是被《世界报》上惊人标题下所载罢工消息吸引住的。他看得很全面——有关的七家公司的名字、罢工的人数,等等。
“这么一个天气闹罢工,那太傻了,”他心里这么想,“不过,可能的话,还是让他们获胜吧。”
第二天,出现了更大的新闻。《世界报》上说,勃洛克林的居民步行上街。“劳动骑士团拦住了街车过桥”、“七千人左右失业”。
赫斯特渥特读了这些新闻,自己心里形成了可能会如何结果的观念。他是一个坚信公司的力量的人。
“他们不可能获胜,”他说。这是指的罢工工人。“他们什么钱也没有。警察会保护公司。他们不能被保护。公众须得有车坐嘛。”
他倒并非同情公司,不过力量在他们一边嘛。财产和公用事业也如此。
“这些家伙赢不了嘛。”他想。
在各种事情当中,他注意到了其中一家公司所发的一张通告:
大西洋路铁路公司特别通告
鉴于本公司司机、售票员及其他职工人等突然弃职,凡违反其意志而罢工的一切忠于职守者,如能在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钟以前申请,均可重新任职。雇佣的先后以申请的先后为准(给予安全保障),并据此安排车次与职务。否则以解职论,所遗空缺,由即将招用的新雇工补充。
总经理朋杰明?诺顿(签名)
赫斯特渥特又注意到,在招工广告中有一则是这样:
招聘——五十名熟练司机,要求懂得西屋机车性能,能在勃洛克林市内行驶美国邮政车;保障安全。
他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广告中都有“保障安全”的字样。在他看来,这表明了公司不可侵犯的权力。
“他们有民团在他们的一边,”他想,“这些工人是无法可想的。”
当他心里怀着这些想法的当口,和奥斯洛格以及嘉莉发生了冲突。过去曾有不少事引起他的反感,不过这一回可说最严重。过去从没有人责怪他偷窃——或者很接近于这类事的勾当。可她却怀疑这一大笔帐单的可靠性。何况他如此艰苦,力争减少开支呢。他一直在“哄骗”肉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为了不致向他讨帐。他又吃得很少——几乎什么都没有吃。
“去它的,”他说,“我能找到些事儿干干。我还没有垮呢。”
他想想,如今确实是非得干点儿什么了。人家这么挖苦,还一直坐在这里,那也太不值钱了。哈,再歇一会儿,他会什么都顶得住。
他站立起来,望着窗外凛冽的街道。他一边站在那儿,一边心中慢慢地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到勃洛克林去。
“为什么不?”他心里这么说,“谁都可以到那儿去干活。每天可以赚它两块嘛。”
“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说不定会受伤啊。”
“哦,那算不上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已经招来了警察啦。任何人要开一次车,都会得到保护。”
“那你并不懂得开车啊。”那个声音又说。
“我并不打算申请做司机,”他回答说,“我能够售票嘛。”
“他们要的主要是司机。”
“他们什么人都要,这我知道。”
他在内心里赞成、反对争了好几个钟头。他觉得,这样稳稳的有利可图的事,需马上采取行动。
到了早上,他穿起了他最好的衣服,其实那是够旧的了。他开始忙碌起来,把面包和肉放在一张报纸上包了起来。嘉莉看着他,对他这个新的动作饶有兴趣。
“你哪里去?”她问道。
“去勃洛克林,”他回答说。后来见她仍然有些疑惑,便接着说,“我想在那里能找到工作。”
“在街车上么?”嘉莉大为惊诧地说。
“是的。”他回答。
“你不怕?”她问道。
“怕什么?”他回答说,“有警察保护他们嘛。”
“报上说有四个人昨天受了伤。”
“是的,”他回答说,“不过你不能根据报上说的话。他们照样开车。”
他眼下像是下了决心似的,样子有点儿凄然的光景,嘉莉也觉得很难过。这里表现出了赫斯特渥特当年的某种特色——当年精明、强干、快乐的某些小小的影子。外边云层很低,正飘扬着几片雪花。
“挑了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去那儿啊。”嘉莉心想。
他在她之前出了门,这可是一件难得的事。他朝东到第十四条街和第六条街,在那里搭上了车。他在报上看到,有几十个申请者到勃洛克林市铁路大楼办公室,并且被接受了。他是坐了马车,再搭了渡船——他这个黑皮肤的沉默的人——到那边的办公室去的。路很远,车又不开,天又冷,不过他还是吃力地步行前往。一到勃洛克林,他看得很清楚,是在举行罢工。在人们的行动举止上就看得出来。有些轨道上没有车行驶。在有些拐角和附近的沙龙,有小堆的人在游荡。有些敞篷货车在他身旁驶过。车上放着普通的木椅子,标着“佛拉蒲什”或者“普罗斯贝克特公园。票价一角。”他注意到了一张张冷冰冰的甚至阴沉沉的脸。工人在打小型战争啊。
他走近有关的办公处那儿,见到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还有几个警察。远远的拐角处另有些人——他认为是罢工工人——正在监视着。房屋一律很小,是木结构,街道崎岖不平。见过了纽约,勃洛克林就显得委实太穷、太艰苦了。
他朝一小堆人的中央走过去,警察和已经在那里的人冷眼看着他。其中有一个警官对他说话:
“你找谁啊?”
“我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位置。”
“办公室在台阶上面。”警察说。他的脸不露声色难以捉摸。在他的心底里,他是同情罢工工人,痛恨这个“工贼”的。在他的心底里,他也感觉到警察的尊严与作用。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至于它真正的社会意义何在,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生性不是这个料。有两种感情混合在一起——彼此间中和了起来,对他也如此。他会为了某个人斗,就像为了自己而斗一样。不过得按照命令办事。剥掉了他身上的制服,那他就会很快便选定站到那一边。
赫斯特渥特走上了满是灰尘的台阶,走进了一间灰色的小办公室,室内有栅栏,一张长桌子,有几个办事人员。
“先生,你好?”一位中年人说,一边从长桌子上抬起头来望着他。
“你们要招雇人么?”赫斯特渥特问。
“你是干什么的——驾驶员么?”
“不,我什么也不是。”赫斯特渥特说。
他并不以自己的境况而感到害羞。要是一处不收他,别处会收。收他,不收他,随他的便好了。
“嗯,我们当然宁可要有经验的人,”那个人说。他停了一下,赫斯特渥特则漠然地一笑。后来那人又接着说,“可是你可以学嘛。你叫什么名字?”
“惠勒。”赫斯特渥特说。
那个人把命令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把这个拿到我们的车库去,”他说,“给工头。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干的。”
赫斯特渥特走了出来,下了台阶。他直接朝指明的方向走去,警察在一旁看着。
“又有一个人要试一试。”警察基里对警察马西说。
“我相信他准会吃尽苦头。”马西态度平静地说。
他们从前参加过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