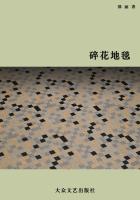第四十六章把已经混浊的水搅得更加混浊 (2)
她这个人甘于孤单、内向的性格确实有点儿特别,她在公众眼里成了个有趣的人物——她这么沉静而含蓄。
没有多久,管理部门决定改到伦敦去演出。在这里,第二个夏季看来生意不会怎么样。
“你试试看去征服伦敦,你看怎么样?”经理在有一天下午问她。
“也许正好是伦敦征服我呢。”嘉莉说。
“我看我们要到六月份去。”他回答说。
匆匆走的时候,把赫斯特渥特给忘了。他和杜洛埃两人全都发现她已经走了。杜洛埃来过一次,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失声叫了起来。于是他在厅堂里站着,咬着胡子尖。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往昔的时日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她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不过在心底深处,他也并不相信这句话。
赫斯特渥特在长长的夏天和秋天,凭了稀奇古怪的办法糊了一张嘴。在一家舞厅当个看门人这样的小差使干了一个月。更多的日子是靠了乞讨,有时候就饿肚子,有时候睡在公园里。其它的日子是求告那些特定的慈善事业,其中有一些是他心急如焚到处寻找时偶然碰上了的。到了隆冬季节,嘉莉回来了,在百老汇一出新戏中出现了,不过他却并不知情。有好几个星期,他在市里到处流浪乞讨,而灯光照耀的广告,入晚在熙熙攘攘的游乐区大街上,光彩夺目地向大众宣告她将上演的戏。杜洛埃倒是看到了的,不过他不敢冒那个险。
大致在这个时候,阿姆斯回到了纽约。他在西部略有成就,如今在乌斯特街上开设了一个实验室。当然罗,他是通过万斯太太介绍而遇见过嘉莉的。不过两人并无什么声气相通之类的事。他还以为她是和赫斯特渥特结成一体的,到后来才知道不是的。他不知道事实情况,不想装作很了解,并且不愿加以评论。
他和万斯太太一起去看了那出新戏,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不应该演喜剧,”他说,“我看她能演得比这个更好些。”
一天下午,他们偶然在万斯家相遇了,开始了一场友好的谈话。她说不清为什么一度对他的强烈的兴趣如今不见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刻,他代表了她当时所没有的什么一种东西。不过这她并不理解。如今事业的成功使得她一时间有一种感觉,她眼下拥有了他会加以赞许的很多东西。而按诸事实,她在报上的一点儿小名声,对他来说是什么都数不上。他认为她有能力表演得更好,而且好得多。
“这样说来,你还没有演正喜剧啊?”他说。
他回忆起了她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
“没有,”她回答说,“迄今为止,还没有。”
他异样地望着她,这叫她认识到,她自己是失败了,“不过,我是想演的。”
“我想你会演的,”他说,“你的气质适宜于演正喜剧。”
他竟然会谈到气质,这可叫她吃了一惊。难道说,在他的心里,有个清晰的她么?
“为什么?”她问。
“嗯,”他说,“依我看,你天性里富于同情心。”
嘉莉微微一笑,也有点儿脸红。他对她如此真诚,使得她对他的友情更深一层。往日里追求理想的愿望又在心里燃起。
“我不知道。”她回答,可是很高兴,那是无从掩饰的。
“我看过了你的戏,”他说,“演得很好。”
“你喜欢,这我很高兴。”
“确实很好,”他说,“对于一出喜剧来说是如此。”
这是当时说的全部内容了,后来话给人家打断了,不过再后来,他们又见过面,他在晚饭后坐在一个角落里,眼睛瞪着地板,这时嘉莉和另一位客人走过来,辛苦的工作使得他脸容憔悴,这其中自有一种叫她动心的东西,只是嘉莉自己并不清楚。
“就一个人?”她说。
“我正在听音乐。”
“我一会儿就来。”她的伙伴说,此人看不到这位发明家有什么了不起之处。
他这会儿抬起头来望着她的脸,因为她是站着,他是坐着。
“这不是很悲怆的调子么?”他一边听,一边问。
“哦,很悲怆。”她回答说,也听出来了,便认真注意起来了。
“坐下。”他接着说,一边把边上的一张椅子推给了她。
他们在沉静中听了一会儿,都深受感动,只是在她来说是通过心灵深处听的。音乐还是像往日一样叫她着迷。
“我不懂得什么叫做音乐,”她开始说。有一种莫名的渴望在她胸中激荡,叫她深受感动,“不过这总是叫我感觉到仿佛我在追求着什么——我——”
“是啊,”他回答说,“我明白你是怎样感觉的。”
突然他又转而谈到她的气质的特点,把她的感觉说得很坦率。
“你不该伤感。”他说。
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谈到了一个仿佛不相干的事,可又是符合他们的感觉的。
“这世界充满了令人向往的情景,不过不幸的是,我们只能在某一个时刻处在一种情景之中。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扼腕叹息,这对我们可没有什么好处啊。”
音乐停了,他立起身来,在她面前站着时的那个神态仿佛是要休息一会儿似的。
“为什么你不演些好的坚强的正喜剧?”他说。他这会儿是直望着她,端详着她的脸容。她那大大的富于同情心的眼睛和含有痛苦意味的嘴巴,在他看来足以成为他判断的证据。
“也许我会的。”她回答说。
“这是你的天地。”他接着说。
“你这样想么?”
“是的,”他说,“我这样想,我看你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你的眼睛,你的嘴巴,叫你适宜于这样性质的表演。”
嘉莉因为这样被认真看待而心卜卜地跳动。一时之间,孤独感消失了。这样的夸奖既真切,又富于分析性。
“正是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他比较抽象地说下去,“我还记得我第一回见到你时就想,你的嘴巴有点儿什么独特的东西。我想你像是要哭。”
“多怪。”嘉莉说。这正是她心里所憧憬的。
“然后我注意到了,这是你自然而然的神情,今天晚上,我又一次见到你。你的眼睛里也有那么一丝阴影,这使得你的脸容有了这同样的特色。我看,这是在深层次里的东西。”
嘉莉直瞪瞪望着他的脸,简直全身心都震动了。
“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接着说。
她望着别处。他能这么说,她是高兴的。她一心渴望能配得上那在她脸上刻着的表情。这打开了她那追求新的憧憬的大门。
她有理由要好好思量这些,一直到他们再一次见面——那是几个星期以至更长时间以后的事了。这表明,她正在游离开那旧日的理想,而那正是从阿佛里剧场的化装室以来长时间里一直充塞着她心头的东西。为什么她已经失去了它啊?
“我知道为什么你会成为事业的成功者,”他在另外一次说,“只要你能担任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角色。我已经研究出了——”
“那是什么?”嘉莉说。
“啊,”他说,仿佛因为猜谜而十分高兴,“你脸上的表情是在不同的场合都流露出来的东西。在一支悲怆的歌子里,或者在叫你深深感动的任何一张画面里,你都有这同样的东西。这是全世界喜欢见到的东西,因为这是世界的渴望的自然流露。”
嘉莉一味凝视着,仿佛没有能真正领会他所说的话的含义。
“这个世界总是力争要表现它自己,”他接着说,“多数人没有能耐表露自己的感受,他们得依仗着别人。天才就是为此而生的。一个凭着音乐表露了他们的渴望,另一个凭了诗歌,再一个凭了戏剧。有的时候,造物凭了脸——造物凭了脸容表露了它全部的渴望。你的脸容正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望着她,在他的眼睛里洋溢着他所说的话中种种的含意,这她领会到了。至少,她得到了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她的脸容代表了这个世界的渴望。她认为这是件荣耀的事而十分感动。接着,他又说:
“这叫你身上挑起了一份责任的担子,恰巧是你拥有了这个东西。这并非是要归功于你——我是说,也可能你并不能拥有这个东西。你并没有为此而付出过什么。不过如今你既然有了,你就必须为此而做点儿什么。”
“做什么?”嘉莉问道。
“依我说,转到戏剧领域去。你如此洋溢着同情心,又天赋如此好听的歌喉。让这些造福于人们吧,这样能叫你魅力得以持久不衰。”
嘉莉对最后这句话并没有领会。至于其它所有的话都表明,她在喜剧方面的成功,价值很少,甚至没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什么?”她问道。
“啊,正就是这样。在你的眼睛里,嘴巴里,在你的天性里,你有这样的素质。你知道,你是可能失掉它的。要是你背离了它,光只为了满足你一个人的生活,它便会很快消失。你的眼睛会失掉那个眼神,你的嘴巴会变形,你那种表演的力量会消失掉。你也许以为不至于这样,可是会这样的。造物主会主宰一切的。”
他是如此热心于宣扬有益的主张,有的时候简直变得兴奋起来,便大大地宣讲起来了。嘉莉身上有些什么打动了他,他要叫她振奋起来。
“我知道了。”她茫然地说,她因为自己忽略了而不无负罪的感觉。
“我要是你的话,”他说,“我就会改变了一下。”
这句话的效果仿佛是把无助的水搅浑了。(意指:弄乱了嘉莉的心境,使她很想改变目前的处境,但又无能力,徒然心乱,就像河水一样只能无助地随波逐流。——译者)嘉莉有好几天坐在摇椅里摇晃,一边为这而苦苦地思量着。
“我不相信我会在喜剧里再呆这么久。”她后来对萝拉说。
“哦,为什么不啊?”萝拉问。
“我看啊,”她说,“我演严肃剧能演得更好些。”
“你脑子里怎么装上了这么一个念头?”
“哦,没有什么,”她回答说,“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可是她还是无所动作——只是发愁。要达到更好一点儿的境界——或者仿佛如此的境界——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呢——而她的生活已经是舒适的了,因此之故,便懒着不动,而又渴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