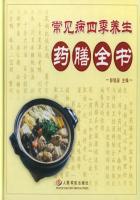第二部8
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经历让迪克极为不满意。病理上的根源和处理上的失败让他感到一种金属般的单调味道。尼科尔的情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利用——要是换了他自己,他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一段时间的痛苦——梦中他看到她在诊所的小径上步行,摆动着她那顶宽大的的草帽……
有一次他实实在在看见了她。那是在他步行经过王宫饭店时,一辆罗尔斯牌豪华轿车转弯驶上半月形的门前车道。巨大的车身和几百马力的功率,把车里的人比得十分渺小。里面坐着的是尼科尔和一个年轻女人,他猜想,那是她姐姐。尼科尔也看见他了,有一刻,她的嘴唇微微张开,脸上现出惊恐。迪克抬了一下帽子,便走开了,然而有一刻,他周围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来自格罗斯明斯特河上的魔鬼发出的喧闹声。后来,他想把自己在她面前的庄重表现详细记载下来,凭借记忆写一个备忘录,记下病人受到再次“冲击”的可能性,这种压力不可避免总会再次遇到。这个备忘录要对任何人都有说服力,只是没法说服他这个写备忘录的人。
这项努力的全部价值在于,他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已经深深卷了进去;在这之后,他决定以其他方式来调整自己的感情。一种方式是找奥布省巴尔城那位电话接线姑娘。她正在欧洲旅行,从尼斯到科布仑茨周游,身边围着一帮奋不顾身的男人,那是她在无与伦比的假日中结识的;另一种方式是作出一种安排,八月份趁政府的交通便利回家探望;第三种方法是集中精力搞工作,找到证据写好书,今年秋天就把它呈献给讲德语的精神病学专家们。
迪克的情绪激越,简直要撇开这个作品了,他想要做更多整理准备工作;假如他能找到个伙伴与他进行交流,便能指望那个人为他做大量的日常工作了。
与此同时,他规划出一个新的课题:根据当代不同的分类术语在一千五百例克拉帕林前与克拉帕林后检查基础上对神经病和精神病统一和实用的分类的一种努力——他拟出另外一个响亮的段落——在长期细致的研究中独立发展形成的深入看法。
这个标题翻译成德语,读起来会显得具有划时代的气魄。
进入蒙特勒伊后,迪克减慢了蹬车速度,只要有可能就朝迦根霍恩瞅上一眼,透过湖滨旅店之间的小巷看到湖水的耀眼波光。一群群英国人让他觉得十分显眼,他们四年之后再次出现在这里,目光中都带着侦探故事里那种怀疑一切的神色,仿佛在这个值得怀疑的国度里,德国人训练出的匪徒随时都可能袭击他们。在这片由山洪冲积成的碎石地上到处有建筑物和正在建造的楼舍。迪克在到南面来的路上,在伯尔尼和洛桑曾经急切地打听过,今年是不是有美国人,“要是六月没有,那么到了八月有没有?”
他身穿皮夹克,内穿美军衬衫,脚上穿着登山靴。在他的旅行背包里,还放着一件棉布外衣和替换用的内衣。在格里昂索道站,他检查了一下自行车,在车站小吃店的阳台上喝了点儿啤酒,同时还望着索道车从山坡上以八十度的倾角缓缓爬下来。他的耳朵里满是佩尔兹路程中渗出的血渍,一路上他感觉到自己要当一个运动员已经没希望了。他要了些酒精揩净皮肤,这时索道车滑进了车站。他看到自己的自行车装到车上,便把旅行袋投进车子下层,然后上了车。
缆车斜挂在索道上,仿佛一个人不愿让人辨认出来,将帽檐斜压在面孔上一样。看着水从缆车下面的储水舱涌流出来,迪克对整个设计的别出心裁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面那只缆车正在山顶灌水,只要放松刹车,就会由于重力的作用将这个变轻的缆车拉上山。这一定是产生于一个了不起的灵感。在对面的座位上,一对英国人正在讨论这缆索。
“英国制造的从来都能用五六年。两年以前德国人压价投标,夺走生意,你知道他们的缆索用了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一年零十个月。然后瑞士人把它卖给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对缆绳没有严格的商品检验。”
“我明白,假如缆绳绷断,对瑞士来说实在太可怕了。”
乘务员关上车门,给自己的同事打了个电话,缆车猛地抖动了一下,向前移动,朝翡翠色的山巅驶去。缆车离开低矮的屋顶后,沃州、瓦莱州、瑞士萨沃伊州和日内瓦的全部俯瞰景色展现在旅客面前。被罗讷河冰冷的水流降低温度的湖心是西方世界的真正中心。湖面上漂浮着像小船一样的天鹅,以及像天鹅一样的小船,二者都融进这烟波浩渺的美景之中了。这是个晴朗的日子,阳光在下面的青草上和娱乐宫白色的庭院中反射出明亮的光芒。庭院中的人都留不下自己的影子。
奇龙和萨拉农岛屿宫殿映入眼帘时,迪克将他的目光转向车内。缆车已经高于湖滨最高的楼宇,两侧不时擦过交织在一起的树叶和花朵,让人看到片片斑斓的色彩。那是个索道旁的花园,缆车内有一条标语:不得采摘花朵。
虽然人们不准在车上采摘花朵,但是缆车经过时,花儿却扫进车厢里来,随着缆车缓慢的移动,多萝西?珀金斯玫瑰扫进缆车的每一个厢座,最后又摇晃着恢复到玫瑰丛中。这些花枝一再扫进过往的缆车。
在迪克上面和前面的厢座里,一群英国人站起身,为蓝天背景而欢呼,突然他们中间起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为一对年轻人让路,那对年轻人一边道歉,一边朝缆车后部的一个厢座爬去——那就是迪克所在的厢座。那个年轻人是个拉丁人,眼睛又大又黑活像玩具鹿;那姑娘是尼科尔。
两人爬上来后累得喘息了片刻。他们笑着在座位上坐定,把英国人都挤到角落里去,尼科尔打了个招呼说:“你好。”她看上去十分可爱;迪克立刻就发现某种东西有些不一样。他立刻就意识到那是她精心梳理的发卷,摆动起来活像艾琳?卡斯尔的秀发,发卷蓬松抖动着。她穿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球衣——她就像五月份第一个明媚的早晨,诊所的一切痕迹全都消失殆尽了。
“砰!”她气喘吁吁地说,“唔,那个卫兵。他们要在下一站逮捕我们。这位是戴弗医生,这是马莫拉先生。”
“哎哟!”她喘气吁吁地摆弄着自己新理的头发。“姐姐买到了一等票,这是她的原则。”她和马莫拉交换一下眼色,喊道:“后来我们发现那个一等票是个司机座后面的棺材架,四周为了防雨拉下帘子来,这下你什么都明白了吧。但是姐姐十分有派头……”尼科尔和马莫拉再次以年轻人的亲热笑了起来。
“你们上哪儿去?”迪克问道。
“考克斯。你也去那儿吗?”尼科尔望着他的装束。“前面那是你的自行车?”
“对。星期一我要去海边。”
“带我坐在你的车梁上?我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吗?我想不出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
“可我要抱着你下去,”马莫拉强烈抗议道,“我滑旱冰送你去,要不就把你抛下去,让你像根羽毛一样飘下去。”
尼科尔想到自己要变成一根羽毛,而不是一只铅锥,要飘下去,而不是栽下去,不禁喜形于色。她看上去就像个狂欢节上的中心人物,时而腼腆,时而矫揉造作,时而颦蹙双眉,时而指手画脚 。有时候,过去痛苦的阴影再次落到她身上,一直能涌流到她的每一根指头尖上。迪克真希望自己能离开她,因为他害怕自己在场会提醒她已经留在身后的那个世界。他打定主意,要住另一家旅馆。
缆车停下来后,不习惯的人们看到不同的蓝色调发出一阵怀疑的骚动。这只不过是上行和下行的缆车更换了一下乘务员。然后,升啊升啊,飞越一条林间小径和一条峡谷,然后继续向山丘上升去,这时由于能看见山丘上生长的水仙,已经在旅客与天空之间看到了实在的山丘了。在蒙特洛伊湖滨球场打网球的人们这时变得像针尖一样小。空中有了新鲜的东西,新鲜体现在音乐上。他们的缆车滑进格里昂后,人们听到花园饭店传来一阵管弦乐之声。
当人们换上山地列车后,音乐被储水室的水涌流的声音压倒了。考克斯几乎在头顶上,一家旅店的几千个窗户正在傍晚的阳光中反射出燃烧般的光芒。
但是旅行的方式不同——一台皮囊机车将旅客顺着螺旋形车道一圈一圈往上拉,升啊升,上啊上。它们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穿过低垂的云彩,有一阵儿,在轻便机车拉着他们倾斜向上时喷出的雾气中,迪克看不到尼科尔了。他们乘着一丝风向上,每过一个索塔,旅馆就变得大一些,最后,在一阵惊讶赞叹声中,他们到了阳光明媚的山巅。
在到达后的纷乱之中,迪克将自己的旅行包甩到背上,举步走向站台,取自行车,尼科尔已经跟在他身旁了。
“你不住我们的旅馆?”她问道。
“我要节省钱。”
“你愿意来跟我们共进晚餐吗?”取行李的时候人们有些混乱。“这是我姐姐——这位是苏黎世的戴弗医生。”
迪克朝一位二十五岁的女子鞠躬致意,只见那女子身材高大,态度自信。他回忆起另外一些嘴巴像花朵、一次吃一丁点东西的女人们,他认定,她既可畏,又脆弱。
“晚饭后我来拜访,”迪克许诺说,“首先,我得适应这儿的环境。”
他跨上自行车离开,感觉到尼科尔的目光在追逐着自己,感觉到她那没有意义的初恋,感觉到那段恋情在自己心中扭曲。他蹬车爬上三百码外一个山丘,在上面一个旅馆里订了个房间,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十分钟之内什么念头也没有,只有一种潮涌般的感觉,其中夹杂着刺耳的声音,那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声响,那声音并不知道他受到怎样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