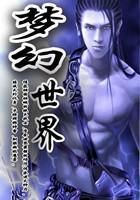最终的处罚,不过是一顿军棍。军棍长三尺,方一寸。手握的部分呈圆形,黑色;打人的那段是三棱形,下面扁平,中间微曲,红色。这顿军棍好似笑话,打人的那个一边打一边笑着飞快地报数,数目很虚,无法坐实:“二三四五,七八九十——”
报得快,打得更快。一百军棍,真正能打六十也就不错。但无论如何,挨打总是痛的,尤其是冬天,气温低皮肤紧缩,双方可谓硬碰硬。挨打的一边数数一边骂,也不知道骂谁。但是等挨完打,他挣扎着爬起来,还是要规规矩矩地向长官敬礼:“谢师长大人教诲!”
后来才知道,这样被掳走的良家妇女不在少数。为防止逃跑,一抓进去首先剃发,而且剥掉裤子。就像宋朝的军兵刺字。若无目击证人,陈其泽的儿媳妇不可能脱离牢笼。
可这个无辜的信阳女人的噩梦远未结束。回家之后,她目光呆滞神情悲凉,没有一滴眼泪,几如死人。那天夜里,她要求洗澡。该想法之奢侈,可以想见。城内有井,水倒不缺,但柴火十分金贵。很多人早上讨厌凉水,干脆脸都不洗,遑论洗澡?
最终她用了凉水。这些日子衣不蔽体,她似乎已经习惯严寒。洗好之后,她换上干净衣服,像正常过年那样,穿得喜庆而且艳丽。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陈其泽习惯于早起。次日一早,他发现三儿媳妇静静地悬于厨屋梁上,斗篷的帽子戴着,但未能完全遮住头顶的耻辱。伸手摸摸,她浑身已经凉透。
大老先顿觉如释重负。
无棺材收敛,无道士作法,无响器奏乐,甚至连个埋骨处都没有。过去死了人,大户人家埋到家族固有墓地,平民百姓一般送到城西。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那里反正山多林密,处处皆可埋身。但是如今不行,西门外边就是战线。
死无葬身之地,便是信阳百姓的命运。家便是埋身之所。虽然山区的信阳已经沦为孤岛,但县知事程羽宵还是竭尽所能,组织慈善会与商会全力维持。每日都有百姓死伤。枪炮击中的,冻死饿毙的,盗匪劫杀的。这些死尸全部拉到西城墙下,草席裹身,就地掩埋。
但谁也想不到,陈家在那种情形下,依旧操办了一场程序完美的葬礼。年满五十的信阳人,人人都自备有棺木。陈其泽让出自己每年都要晾晒涂漆、沉吟抚摸的柏木棺材,用于收敛儿媳,并重金聘请刘景向撰写诔文。
刘景向文名在外,但交稿之后陈其泽却不满意,要求修改。因为文章的笔力所向,都是老陕的暴虐酷烈。也就是说,刘景向并未回避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而且尽管主顾不满意,他也坚决不肯修改:羊山或可改移,此文一字不易。
作为大老先,写篇诔文陈其泽自命绰绰有余。然而这事他不能包办,必须倩人捉刀,名望越高越好。既然刘景向不肯配合,那就只好付出润格,另行聘请。请谁呢?小长辈儿。他的诔文,颇合陈其泽心意。几乎通篇都在赞美死者之节烈妇德。至于如何受辱,受的何辱,春秋笔墨,语焉不详。
也不知道陈其泽从哪里请来的道士仙与吹鼓手。他们抬着灵柩,在城内转一圈儿,然后重新回到家中,厝于堆放杂物的偏室。那时人们本来也不急于安葬,如果尚未寻到可心的墓地,或者不想就近掩埋,举哀之后多厝于寺庙。然而信阳的寺庙多数已被毁掉,虽有残存,奈何无法出城。按照道理,城隍庙也是个选择,可如今的门窗屋顶也已荡然无存,棺木停在那儿不保险——棺材本身便会招祸。
城隍庙街本是李世日最喜欢的去处。因为文魁书店和冯瞎子。可如今庙已拆毁,书店停业,冯瞎子也已亡故,与城隍庙同日被难。那天一队老陕前来拆庙,冯瞎子试图阻拦:“列位大人老总,这是城隍庙,万万不能拆呀。”他脸上一直带着笑,笑容像布景般搭在浑浊空洞的眼球前,显得分外滑稽,老陕不觉哈哈一笑:“为啥拆不得?”冯瞎子道:“这是元代留下来的老建筑,历史五六百年了呀。”老陕道:“还瘪代呢。已经五六百年,正好该拆掉嘛,日后再盖新的。”冯瞎子意识到此刻自己的确活在评书中,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赶紧改口道:“城隍老爷保佑全城平安。你们每日里上阵厮杀能安然无恙,都赖城隍老爷保佑。现在你拆他的庙,那还了得?”
城隍的本意只是护城河。班固在《两京赋》中有句:“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后来逐渐演变成主管阴间的神灵。从南北朝到唐代,城隍神信仰日盛,宋代正式列入国家祭典。元代封为佑圣王,明代则细分王、公、侯、伯四级爵位。城隍多数都是当地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比如柳州城隍柳宗元,杭州城隍文天祥,苏州城隍春申君黄歇。上海的老城隍是霍光,新城隍则是民族英雄陈化成。冒名顶替刘邦而被项羽处死的纪信,也被郑县奉为城隍。信阳城隍则是岳飞。因为他出师北伐,曾在信阳一带激战建功。
这些话当然没机会跟老陕掰扯。他们哪有这份心情听呢。老陕甲道:“我不管保佑不保佑,我只要烤火!”老陕乙暗含杀机:“瞎眼的,听你那意思,我今天要是拆了庙,明天就会挨枪子?”冯瞎子道:“现世报,现世报。城隍老爷岳元帅是有天眼的。”
老陕乙砰的一枪,将冯瞎子撂倒:“奶奶的,看看我挨枪子,还是你挨枪子!城隍老爷真在,我就打不死你!你说呀,你还说呀。哈哈哈。”
老陕丙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城隍老爷,请您老千万原谅小的。小的本不敢冒犯您老,可是上头有令。您要是怪罪,就怪罪城外的鄂军吧。”
老陕甲踢了老陕丙一脚:“罗唣个啥,快点动手!”
每天夜里,都有老陕手持令箭沿街巡逻:“奉师长将令,抢劫财物调戏妇女,一律就地正法!”那些话越琢磨越像暗示甚或鼓励,对抢劫强奸的隐性提醒。经此提醒,抢劫强奸都已不成新闻。新闻不是即将落花,只是花落谁家。比如这一回,就轮到了陈其泽。
陈家遭遇抢劫,很可能与葬礼有关。葬礼场面大,人员杂乱,而他当初反对田赋整理,又结怨不少。陈家有一只青铜鼎,不大,但却是西周古物。葬礼当天,那只鼎拿来作香炉,来宾只要长着眼睛的,都能看见。结果几天之后的夜里,便有蒙面人手执刀枪,将之抬走,本意用于煮肉熬汤的部位,盛满金银细软。不几日,城东古玩街上收赃的商店也向县署报告遭抢,失物也是周代青铜鼎一只。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年在岳维峻麾下,曾经有位黄埔一期毕业的团副,名叫徐向前。他看不惯部队的腐败,挂职而去。类似李世登。这就是气场的选择。而留下来的,自然都是适应腐败习惯于军纪废弛,在堕落中能体味到快感的人,故而越发暗无天日。而最终的结局,则是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将岳维峻俘虏。这虽是后话,但为时不远。
邓东藩对此深有体会。他脱离部队回来后,又在武装警察队补了个队长。他最清楚那段时间盗抢现象的严重与普遍。多是盗匪勾结老陕所为。本地盗匪熟门熟路,充当线人,提供信息。你即便告官将他们拿获,也不顶用。他们很快就能重获自由,继续作乱。正因为如此,起初还有商店压价收赃,很快古玩宝贝便无人问津,无论价格多低。因为你下午收购,晚上就有可能遭抢。古董珠宝都不值钱,值钱的是粮油食物衣服被褥,以及木炭柴火。
一句话,对生存没有直接帮助的,统统稀烂贱。
李家也不是没碰到过盗匪。只是赵明远与高继古早已严阵以待。兄弟俩劈死一个,砍伤一个,全部连夜报官,由邓东藩拉走处理。从此以后,盗贼再也未曾光顾。
当时城中的多数商店,都被老陕占据。李玉亭的茶庄以及北门外的和盛钱店,无一例外。每到晚上,老陕们便聚众赌博。吆五喝六,酒气熏天。大概知道来日无多,他们赌得都很大,而且只认现洋,不收纸币。尽管军饷伙食费都按照纸币结算。消息传开,李玉亭心里颇为不安。虽然满城饥饿四壁寒冷,但李家毕竟是李家。粮油食物他们向有储备,柴火只要肯出高价也能买到,大不了拆屋扒檩。至于烤火的木炭,真是再巧不过,他们突然从库房深处,发现了几包当初炼化银子所用的银炭。这玩意儿多年不用,没有搬到北门外的店铺,一直扔在库房深处。
银炭比木炭贵好多倍,燃烧值与热量自然也远非木炭所能比拟。有了它们,李家夜晚的火炉从未熄灭过。石膏大王、土耳其与龚先生等人,也常常过来打麻将。说是打麻将,其实主要为了烤火,享受此间难得的温暖。某日竹戏间隙,李玉亭让龚先生占卜,结果得到的是这样两句:“知进而不知退,知来而不知往。”
彼时李玉亭正为柜上成堆的豫票忧心。一见这个,不觉心里打鼓,赶紧追问何意。龚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已经说得很是清楚,还说什么?”他始终没说半点别的,无论为人还是生意。但李玉亭认定,这必定与生意有关。当时和盛钱店的本部还在营业,尽管生意清淡,但并未中断。事后李玉亭立即吩咐夏先生,不再收豫票,无论折扣多低。但可以收台票,以便对冲风险。
那时寇英杰的主力已经绕道北上,由刘玉春的偏师监视信阳。刘玉春的司令部设在羊山,宋大霈的司令部设在铁路以东的曹家花园。他们主要采取围困战术,大规模进攻并不多。城中百姓困顿已久,人人都想出去透透气,在结冰的浉河上走一走,或者砸开冰层,钓条活鱼下酒。冬季冰封,河中缺氧。只要砸开冰层,必然会有鱼儿上钩,成为美餐。卧冰求鱼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说明那人傻。
可是,谁能出得去呢?
时间越久,大家对蒋世杰的了解越多,心情也越发绝望。程羽宵说,这蒋世杰本来就善于守城。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进攻三原的靖国军,蒋世杰为胡景翼坚守相桥镇。他率一营之众,扼守相桥长达四十八天。靖国军能支撑到最后,与相桥镇始终在握密切相关。
这话益发令大家丧气。当时路上的倒毙者已随处可见,信阳要是当真也被围上四十八天,那满城百姓只怕得饿死一半。那天从县衙出来,身裹皮裘的李玉亭穿行于街道中,忽觉浑身冰凉。皮袍似乎毫无作用。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辛亥年所受的枪伤,正像霉菌一般快速繁殖。疼痛并不剧烈,但是无处不在。你就想想霉菌的样子吧。
前面的街角有家油酱铺。李家茶庄的掌柜,最早是这里的学徒。某日他错将一壶醋倒进酱缸,被老板暴打一顿,逐出门墙,最终进了李家的茶庄。此刻,被炮弹击中的油酱铺已经房倒屋塌,人去室空,破碎的酱油缸下面结着黑色的薄冰。走过街角,只见醋缸的另外一侧躺着两个人,一生一死,另外还有条野狗。活人与野狗,正在分享那具死尸。那人虽然活着,但也是气若游丝,神情呆滞,正用最后的力气,缓慢地切割同胞的大腿。冰冻的死尸切割不易。他要间歇几次,才能切下一块惨白的髀肉,在黑冰上擦擦,然后放入口中。野狗动作较快,偶有越界,或者撕咬动作过大,那人只是挥挥手,像是要赶苍蝇。
李玉亭不觉啊的一声,吐了满地。可他万万想不到,那人竟然顺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呕吐物,径直朝自己口中塞。他的手已经冻僵,各个部位配合不灵,那些没有完全嚼碎的米粒,多半抹在嘴唇上。李玉亭再也不敢看,转身落荒而逃。
这情形李玉亭对谁都没有说过。他无法忍受那种恶心。他连续两天吃不进饭,看见食物就想吐。第三天晚上,柳媚要请胡泰运过来把脉,被李玉亭制止。他很清楚症结何在。唯一奇怪的是,尽管两天没吃东西,但他始终不觉得饿,只是烟瘾越来越大。抽完鸦片上了精神,便喊口渴。此时此刻,要是有颗冻梨多好,可他只能舔舔嘴唇,喝点凉茶。
正在这时,北门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炮。从窗户看过去,那一带异常光亮。五门紧闭的次日,袁家骥创办的光华电灯公司便毁于战火,夜晚因此更加黑暗。此时窗户边上的亮光,尽管是由爆炸引起,依然令人感觉到本能的宽松。
李玉亭来到窗前,只见李世业跟几个同学站在窗下,对着远方的炮火指手画脚。李玉亭心里一动,悄悄下楼,来到他们背后。从这个角度看去,远方的枪炮拖着道道曳光。经过黑暗的过滤,不像炮火连天的战场,倒像是精心安排的庆典:枪炮类似烟花,火灾如同篝火。
李世业正在不断地叫好。嗓音不知是受枪炮的震动,还是被微微摇头拖曳所致,有点颤抖,更有点沉醉:“多么绚烂的景致!真美呀。”
火光照亮了远方的城墙。老陕们顾不得短枪,纷纷操长枪还击。弹雨虽然可以想象地密集,却无法显示弹道的痕迹。只有黑暗才能呈现那种流星一般的完美弧线。李玉亭不得不承认,这景致的确当得起绚烂二字。
同学们显然无法苟同:“绚烂?这是战乱!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因此丧命,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果然是钱鬼子的少爷!”
“这是军阀混战!他们彼此残杀干净,正好减少革命障碍。”
“胡说!你看看到底死的军阀多,还是百姓多?”
李世业没再回答同学的质疑。显然,他已深深地被景致打动,沉醉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良久未能出来。直到同学们发现李玉亭,纷纷跟他打招呼为止。
李世业盯着父亲,满眼戒备陌生。但李玉亭只是笑笑。要搁以往,李世业少不得要挨顿教训,为他的没心没肺。可那天却没有。远处伴随着剧烈爆炸的火光,突然让李玉亭浑身一激灵。这与当年在炉房炼化银子的银炭火花,何其相似。那时他常常在火花背后,像看戏般无数次地深入剧情,深深为之感动。为那些像童年和尿泥一般不足为外人道的些许乐趣。如今,他想起这些场景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想起,虽然依旧亲切,依旧感慨,但乐趣已经很淡。彼此之间已有无形的大幕阻隔。他只能旁观,而无法进入。可此刻经过儿子的提醒,他突然发觉,这种大火熊熊燃烧照彻方圆的壮观景致,的确是美丽而且绚烂,不可多得。它能毁灭一切,也就能铸造一切。毁灭是铸造的基础。与化铸银子,甚或治理国家,道理相同。
李玉亭对儿子说:“冷,回去吧。”说完不等他回应,便转身进了生着银炭的房间。
五门关闭前夕,蒋世杰来了不少帮手。老陕的帮手,自然就是百姓的对头。他们要是不进来,信阳的饿殍将会减少许多。当然,这帮人不可能吃白饭,还是想要发挥作用。鹞子高三的那个旅长徒弟杨瑞轩,竟要跟鄂军前敌总指挥刘玉春单挑。
杨瑞轩是陕西富平人,跟随鹞子高三的亲外甥姜老五习武多年,主攻红拳。他生得魁梧健壮,善使大刀。当时陕西主要有两路本土人马,一路是郭坚,另外一路就是胡景翼,均有刀客背景。已被冯玉祥捕杀的郭坚,麾下号称有四大刺客,胡景翼部下则有四大猛士,杨瑞轩乃四分之一。
杨瑞轩名气很大,刘玉春来头不小。
刘字春霖,号铁珊,静海独流镇人。天津历来有习武的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是霍元甲。刘家也是世代习武,刘玉春先后师从李登第、李登善和杨学士,学习太祖门、苗刀以及合一通背拳,跻身“太祖门四杰”,江湖人称“大力神通天教主”。当时各路人马都很重视武术,曹锟本人也善使护手钩。他发迹之后,在军中特设武术营,招收沧州一带有武术根基的士兵,聘刘玉春为总教习,专授苗刀。该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苟全性命于战火的,多数都在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