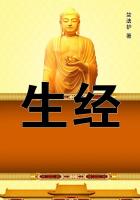苏斥川一面说着,一面将手中的匕首越发的刺入到了那垂暮老者的脖颈间皮肉中。尖刃刺入,登时就有了鲜血从其中涌了出来。而他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只好像这一刻他的身心都被这殷红的鲜血给调动得兴奋起来了。
他缓慢而细致的用匕首的刀刃蹭了些许那殷红的血,而后用那尖刃好似漫不经心的在日息谷谷主的脸上的划过。冰冷且尖锐的触觉会叫人胆战心惊,他时刻在刻意折磨着眼前已在擒在手中之仇人。
“当年,正因为你是南疆蓝氏的留下的血脉。”苏斥川怀着恶意的笑说着这些话来,他手中的匕首极其锋利,几乎是游走到哪里,哪边的肌肤就会被轻巧的划破了。
丝毫不废气力,他手腕灵活的翻转着,不出片刻,那老者脸上就被划得一道道血痕纵横交错了。
可即便是这样,苏斥川仍然不满意,他略微愁着眉,似乎在寻找着一处干净的地方下手着。怎会有人比他的心思更加冷漠歹毒的?
蓝氏?肆肆怎会想到自己当年的遭遇竟然会和蓝氏有所牵连?
“日息谷当年协助先帝铲除苗疆异己,更是有能人献计献策,若不是如此,光是凭着几万大军岂能够将这些施蛊的寨子都灭干净?”苏斥川不禁轻微的嗤笑了一声。
床上之人在这种苦楚的折磨下,依然是不能开口说话,纵然是有滔天的怒气都不能发出来。他只能是双手抓着床铺,怒恨之下将铺在上面的绫罗绸缎都一件件扯了裂开。
苏斥川连瞥都不去瞥一眼,好似这个叱咤风云的日息谷谷主早就入不了他的眼了。他回转过头来,那双眸子分明还是的一如既往的阴郁,“当年你娘是是蓝氏唯一遗留的血脉,被逼无奈之下不得不逃匿到出南疆。”他漠然一笑,声音冷冷的,宛如是秋夜中降下的霜露。
“蓝氏的蛊术绝冠天下,日息谷又哪里会肯杀有遗漏?呵呵……。”
肆肆听着他的话,心头有些迷惑,她早知南疆蛊寨曾经被朝廷派兵清剿倾覆。而关于蓝氏为何会被仇人杀得一个都不留,她娘当年也只讳莫如深的只字未提。
如今……苏斥川却口口声声的说蓝氏是那日息谷去一同剿灭的!
——为的只是忌惮南疆的蛊术坐大?
仔细想后,她心中倒也没有多大的震惊……是了,蛊术这东西原本就妖异得让人侧目。她也早就隐隐觉察到了这日息谷和苗疆有脱不开的干系,却没有想到将蓝氏一族剿杀干净的是日息谷的势力。就算是她娘辗转逃到了京都,都没有能逃脱得掉这追踪。
肆肆这才始知,原来就算是没有自己当日当街拦车怒斥那一事情,她根本也就已经是被人盯上了。
此时她目光直直的看着床上的男子,分明上一刻还在和温香软玉销魂着,这一刻却已经如同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杀了。威风八面的日息谷中竟会有今日下场,生死皆不由自己。
忽然间,苏斥川眸中瞬间冷了下来,他残忍的笑起,迅捷的握着那匕首,银光一闪,只见一抔鲜血立即从那老者的腹下飙了出来。
一丑恶之物登时软塌塌的滚落了下来。
“谷主大人,我总也不算亏待你了。”他的声音邪佞,带着得逞的快意。
无奈那称为谷主的老者口不能言,身子也像是被固定了一样,只能紧咬着牙齿闷哼,面色铁青。他的手指恨极了一样抠着木质的床沿,几道下去后指甲断裂翻飞,指尖已经殷红一片。
苏斥川竟然是……竟然是将这人那子孙根也一刀给削了下来。
肆肆余光瞥见了一眼,顿时胸口处一阵翻涌,她几乎立不住想要寻个东西来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苏斥川却毫无异色,他缓缓的直起了身子,脸上半点的神情也没有。他半垂着眼眸看着床榻上之人,口气漠然的说道:“放心,谷主大人的养育教导之恩,我是不会忘记的。”
话音未有落下,他手中的匕首却哐当一声落了下去。他并没有存了杀心,死从来都是最好的解脱,而他又怎么会让日息谷的谷主轻易的去死?
肆肆怀有身孕,见了这场面后一直隐忍压抑,此刻终于是捂着唇,干呕了两声。
这屋中各种气味夹杂在一起,郁结不散,人呆在其中滋味并不好受。
“呵……。”苏斥川转过头看了一眼,扯了扯唇,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他离开了那床榻的两步,越发靠近了她。“你可知道当日你爹宋怀世宋大学士,先帝曾经委任过他什么的密令?”他突然发问,似乎也并不在意肆肆的回答,继续声音低缓怪异的说道:“这事情确实隐秘,我也是经过了诸方打探才知道的……当年先帝任命宋怀世追查蓝氏遗孤的下落。”
肆肆脑中轰鸣一声,她爹受了皇命要追查甚至是要诛杀最后一个蓝氏血脉!陡然间,她觉得一切都通透了起来,当日宋父在牢中说那些意味不明的话也都一下子明朗了起来。
原来她爹反复所说的有负先帝有负皇恩是指这个,直到这一刻,肆肆心中反而是不能平静。如同是一面光可鉴人的湖水,被苏斥川接二连着三的投入了溅起涟漪的石子。
这些事情,她原本都不知道,如今却是一件紧着一件告诉给她听了。
他为何如此?
苏斥川似乎是看明白了肆肆此时眼中游移不定的原因,他侧转过身,声音阴沉沉的继续张口说道:“这些事情,我总是会让你知道的,就是连着裴湛故意泄露你地宫内的行踪一事,我不也立即就同你说了?”
其实他这说话的口气并没不低沉,还带着几分和气。
可苏斥川的狠毒是名声在外的,就方才手底下动作的决然也不是没有凭证。
他反反复复的提着肆肆之所以让他在那地方是守株待兔般的逮住,是因为裴湛故意泄露了两人的行踪。
肆肆从头至尾都未有将这事情放在心上,见他从来都不是多话的人却反复的提及,不禁让她眸中积聚着恼意。“苏大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不如直接告知肆肆,何必兜兜绕绕。”她口气不善,甚至是带了几分不可抹去的厌恶。
苏斥川身形如同鬼魅一样,还没见到他移动,就已经是到了肆肆的身后。他一抬手,几乎就已经能掐在肆肆的后颈上。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凑近了她的耳边,笃定自若的说道:“是——不——是——待会就会有分晓。”
当真是……笑话,怎么会是裴湛?又怎么可能是裴湛?
肆肆半个字都不信他!
苏斥川眸中带着怪异的神情,他退了几步,他也不去管肆肆有没有将他的这话放在心上,开口低低的说道:“准备的怎么样了?
随即有人从门后转了进来,也如先前那进来之人是同样的打扮衣服,他毕恭毕敬的跪了下来,“一切都准百好了。”
苏斥川曲着手指,似乎是随意的算了一算,才开口道:“好。你先退下。”终于是笑了一笑,他容貌阴柔,如今却是像是明朗了几分。
人退了出去后,这石室内,又重新只有他两个和那躺在床上那日息谷谷主。
就算是日息谷谷主如今就在近处,诸多问题都能一一核实,但那人偏偏也不能开口说话。所以倒头来这一切,仍旧是都只是苏斥川做者说的。
——他那手下所言的准备,到底是什么?
肆肆只觉得心都被提到了嗓子口,有大事情要发生了一样。她下意识的揪着自己的衣裳,难懂这地宫中的一切都已经是被掌控在了苏斥川的手中了?
苏斥川只需一眼就看透了她眼中所想,索性挑明了说道:“我叫你来又岂是看一个要死的老头的?”他径自走了两步,而后稍稍微转了身子看相肆肆。只见他面前是一张古壁画,刺啦一声,那字画被当即全部撕了下来。
而这字画后面别有洞天,竟然还是隐藏着另外一间石室,往里头探上一眼都觉得十分诡秘。
只见室内大大小小有着成千上百的木棍子,不过是都是两根拇指的粗细,并不是竖直到底,而是在末尾的地方上翘着。顺着木棍看上去,则会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从屋顶上面的垂下来的。
乍一眼看过去,密密匝匝的,人人看了心中都要啧啧称奇。
那些粗细相同的木棍的下端,竟然又都是用细细绳子悬挂了一面小巧的牌子。苏斥川伸手去撩起了离着手边上最近的一个木牌子,只见上面用下潦草的笔迹写了什么。
他将那木棍尾端伸手一拔,竟是拔下了一个木塞子,这是一个空心的木棍!
此刻周围甚是悄然安静,但肆肆却好像耳边萦绕着一些若有似无的细杂的交谈。
那声音的源头……不正是苏斥川手中拔开了的空心木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