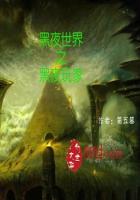杨昳开车赶往机场的时候,顾里斯正躺在大厅的一排座椅上,脑袋上盖着顶帽子,看样子是像睡着了。
双手插腰,无奈地看着那个快三十岁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自觉的男人,掀起他脑门上的帽子,朝他的当顶狠拍了一下。
顾里斯忙从座椅上翻了下来,踉跄地站好,拉拉身上凌乱的外套,嘿嘿地给了一个笑脸:“哥,你来了”
“怎么在这躺着,不自己先回去?”
“钱包忘那边了,没带。这不是没钱打的嘛,怕被人轰下来”
“你可以先去我那儿再付车费,这点事应该不需要我来教你。”杨昳把他扫到一边去,自己坐了下来。
顾里斯是一个超级不能独立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懒到极致的懒汉。在国外的时候,有父母照顾,他还能管个温饱。若是伯父伯母出去走访亲友,那他就凄惨了。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打游戏的他,别说自己动手做饭了,就是出去买一下都是不愿意的。
杨昳常常想,要是伯父伯母外出个几天不回来,待他们回来一看,他们的儿子可能就这么没了。
顾里斯委屈地看了他一眼,“哥,我也想啊,可我不是怕你房子里没人嘛,到时候没钱给司机先生他会拿刀劈我的。”
杨昳正准备说什么,忽然想起来一件事,焦急地问道:“你往我住的地方打过电话了?”
“啊,是啊对了,哥,你房子里什么时候藏了个女人啊”
“你知道有个女人?”杨昳更加吃惊了,钟情根本就不懂这些,怎么知道如何接听电话呢?
“是啊,就是那个女人,我打了许久的电话都没人接,后来好不容易有人听了我以为那人是你,就让你赶快过来接我就在这时,你屋里有个女人,发了疯一样的大叫,把我差点吓死。”
顾里斯后怕地拍拍胸口,幸亏他电话挂得快,否则自己的小心脏还得遭受那可怕的荼毒。
杨昳沉着脸在想着些什么,突然惊叫一声,“糟了!”
他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哥,什么糟了?”
“别说了,快上车!”那小古董,哪见过这些东西。空房子里陡然听到说话声,指不定以为是闹鬼了呢。
都怪他,她好歹也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两人将在一起共度五年,就算没什么感情,总得对她负起一点责任。她初来乍到,对什么事都处在摸索状态,他每天就把她一个人丢在屋里,迟早会出事。
这么想着,杨昳急打方向盘,向离弦的箭一般飞快地往别墅驶去
“哥,你慢点要死人啦”疾驰的烈风中,只能看见杨昳严肃的眉角以及那消散在风中顾里斯的惊呼。
半个小时之后,两人已经回到了杨昳的别墅。
车子来不及开回车库,杨昳忙跳下车来,往大厅跑去。
因为他一向不喜欢有人打扰,也不喜欢家里总有陌生人转悠,没有雇阿姨。除了每个星期会请专人来打扫外,这个大房子里是没有其他人的。
屋内没有开灯,钟情自昨天来到这儿,还没有接触过现代的灯光。尽管她早从外婆那儿得知,那里晚上会比她们那里明亮上百倍、千倍。
杨昳没有迟疑,推开门走了进去。在推开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有一些难言的紧张。
他怕看见那张布满泪痕,眼里尽是委屈和控诉的脸。
说一点都不内疚是假的,他承认,向来蛮有风度的自己,这两天尤其是对她,确实没有风度极了。
他嫌她麻烦,他怕她缠上她,更怕自己会一不小心在与她的朝夕相处对她生了别样的心思,他承担不起那个后果
门还是被推开了,是紧跟在他身后的顾里斯推开的,这小子一直都很冒失,看他站在门边自以为很好心地帮他推开了门,尔后还笑如春风地回眸看着他道:“哥,门开了哟,我们进去吧。”
说着,腿一伸,人已跨了进去。
“喔”刚迈进一只脚的顾里斯突然站直,瞪着眼睛指着里面半天说不出话来。
杨昳心中一紧,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推开挡在门口的顾里斯,临风而立的杨昳看见了那个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抱着身子宛如黑夜中孱弱的幽灵一般的钟情。她瑟缩着身子,尽可能地缩在角落里。夜风吹起,白色的纱帐在夜色中狂乱的起舞,飘浮在她小小的身体上
黑色的发丝配合着白色的纱帐茫茫起舞,铺天盖地的寥落和凄凉,无形地刻进了杨昳的心间。
安静的空气里,隐隐的啜泣声传来,时高时低、时轻时重、时断时续钟情害怕得发抖,脚心冒冷气,一颗心因为恐惧阵阵发凉
“啪”,杨昳按开了大厅里的灯,明亮的光线刺花了他的眼,眯着眼看着窝在角落里的妻子,心中复杂一片。
钟情仍然没有抬头,从开始到现在,她害怕得一直不敢睁开眼睛。
动静,她听到了动静好像有什么人进了屋,还听到了说话声她想,一定是可怕的东西来了,他们还是来了,还是不肯放过她。
身子绷得更紧,泪水落得更急,却不敢发出声响。这是人的本能,即使她知道逃不掉这一劫,还是会这般笨拙的祈求着在黑暗中能逃脱他们恐怖的眼睛。
有一双手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那把手很热、很暖指尖震颤,是紧张还是担忧?
钟情没办法想这些,在那双手落在她的肩膀上,她最后的理智和忍耐破裂,撞开挡在身前的“鬼怪”,崩溃地尖叫着逃离开去。
“别怕”悠远但却坚定的声音穿破尖叫声,直达她的耳际。
钟情身体一震。
“是我。”漆黑的眸子深不见底,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一抹关心,泄露了他真实的情绪。
钟情站在原地,还是不敢回头,不敢睁开她那双眼睛。
“我是你相公,你忘了吗?你就是这么叫我的”很不喜欢的一个称呼,出自她的嘴里,却也不是那样令人讨厌。
顾里斯讶异地看了杨昳一眼,没有说什么,转眼看向了呆愣在大厅正中的钟情。心中讶异更甚,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总觉得面前的那个女人很怪、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