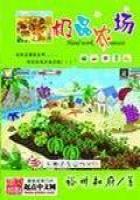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败与治理黄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起义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史·河渠志》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度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真是有力的一问。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压迫相当沉重。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年)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陡增为“四百余处”。对那时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可成为注脚。《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的父亲是“勤俭忠实”之人,靠佃种地主的几十亩地为生,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荒年月,粮食歉收,生活就越发困苦。怪不得朱皇帝忆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泪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官员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基层官员的品质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的官方代表,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借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事实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员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百姓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接触的机会则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说:“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真是明智之语。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基层官员的操守,与他早年的生活大有关系,严厉惩罚贪墨者,也可以从元末地方官员的贪鄙行为的泛滥中找到原因。
吃尽人间穷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国之初并没有搞起义,因为那时还能忍还想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着,才参加了义军。有人把朱元璋与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汉相比,细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汉,根本不存在忍受饥寒的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被逼”,朱元璋们却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似乎很难与他们同日而语。朱元璋举义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权,而梁山好汉追求的是政治权利。
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定,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们。
监督似奴婢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过一句我们听起来有点气馁的话。他说:“御史台、按察司弹纠贪污,申明冤滞,实省部诸司之药石也。省不知与己为助,反视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来当是任者全身远祸,闭口不言。”这可能是针对地方不理解监督所发的感慨。他又说:“按察司今已三四岁,不过翻阅故纸,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不闻举动邪正,劝激勤惰。”监督的领域极其宽广,法律规定了监督者的各种权力,如言事谏诤、弹劾官吏、司法监察、财政监督等等。胡祗遹发出的慨叹,初看与理论有些许相悖,实际却透出一种无奈,是现实的一种写照。我们常说监督之难,究竟难在何处?不是理论上难以表述清晰,而是实际执行起来掣肘于无形,不能对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不能监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监督样子的时候,就只能翻读一下旧书报,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过许多官职,以精明干练著称,颇具声誉。他的叹息,不仅仅说明元朝监察官员的生存状况,更是专制社会监察体制的境遇。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监察官员常被驱如奴婢。譬如唐景云二年(711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撑腰,为非作歹,逼夺百姓店铺,州县官员见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谦光,觉得此时正该他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于是上章奏弹,不料反为太平公主诬陷,被贬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叹连连:“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比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监察官员要行使正当权力,非得依靠皇权的保护才行,否则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盘中餐,这种情景下监督者除了寻几处“小吏细过”之外,还能做什么?
谈到古代监督,人们常常称赞它如何独立,其实那是“张冠李戴”。凭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监督,只是专制制度内部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在聪明颖悟的君主那里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仅自束,而且给监督者更多更大的权力,可以独立思考、判断,然后直接向皇帝汇报。因此,明君统治时期的监督者,往往给人“独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权贵,具有一般监督者没有的特殊性,他虽有“独立”之名,但那“独立”是依附高层人士的“衍生物”,与一般监督者并不沾边。《大唐新语》载,唐长安四年(704年),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责问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萧至忠对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表面说来,萧至忠此举体现了监督者的独立性,但萧氏另外一些工夫,则让人怀疑这种“独立性”到底有多少独立可言。萧至忠最初依附于武三思,武三思败后又投靠韦后,韦氏败后,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来投靠去的投机行为,与“独立”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三,当君主昏庸无道的时候,或者君主虽然不算昏庸,却不喜欢监督的时候,监督者就不仅谈不到“独立”,个人的命运也很凄惨。明代御史蒋钦三次疏劾刘瑾,遭三次廷杖,最后被活活打死。劾奏严嵩者皆得祸,人们益缄其口。
中国古代的监督,是帝王对朝臣的制约,是一种单方面的制约,目的是皇权不至于旁落或衰落。这种监督,与社会各阶层对统治者的制约不太相同。因此,监督发生“畸变”是迟早的事。所谓“畸变”,就是脱离正常监督轨道,而使用非常态手段进行盯梢、跟踪、谋杀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务监督大臣,使用太监监视官员。这样一来,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监察制度本来为了杜绝非法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时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坏殆尽。明朝万历中期,监察御史汤兆京亲眼目睹太监污辱礼部侍郎,汤兆京以为自己是御史,于是上书弹劾太监,结果触怒了特务,被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会有监督?
实际上,在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太监也好,特务也罢,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别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里,监督者如奴婢一样,升迁贬黜一个人说了算,生杀予夺,也与别人无干。“盛世”帝王看重监督,那是监督者的福气,而不是监督制度健全了进步了;末世皇帝胡乱监督,那正是专制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大暴露,正是专制者所谓监督具有的本质属性。
后来呢?
西哲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国历史来说,有一千个读者,恐怕也会生出一千种观点。有人说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用“专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则大加赞颂,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不可简单否定。谁是谁非,还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实充作论据。
皇权统治,是不是一定与落后勾连起来,专制社会是不是一定停滞不前、毫无发展,读者诸君自有论断,在下不必饶舌。不过世人切不可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刚刚接近百年;第二,中国社会封建历史有几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历史多了十几倍或二十几倍,发展速度却落后许多,原因何在?是中华民族人种不行吗?是这片土地贫瘠吗?都不是。显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瞩目,且多以“奇迹”加之于上。寻其源,还不是民主空气渐浓之故?
何兹全在《中国文化六讲》中说,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也出现了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
谈及民主和专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即在于民主之下也会找出专制的事例,专制体内也有民主的幼芽。《老学庵笔记》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此处的“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即杀掉岳飞的那位皇帝。在专制社会,宋高宗算不上特别昏庸无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对宰相的意见竟然如此重视,可见专制之下,某些时候臣子也不是张不得口,尤其唐宋时代之前。不过,不仅每个朝代不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让人难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厨把馄饨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送进了大理寺。
在专制社会,各个朝代虽有区别,但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也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巨细,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经他过目。清代皇权比明代集中程度还要高,嘉庆皇帝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专制集权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记录。在事件众多,头绪繁杂的记录中,寻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难,不能凭此轻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对传统稍加增删就以为违背了祖训,就以为远离了国情,那样不仅显得太幼稚,也太草率。后人对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顶礼膜拜。虚无不好,会变成无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则会陷入自恋之中,无端陶醉。下结论之前问一声“后来呢”,可能会冷静一些。
“专制文化”塑造了统治者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实行独裁统治并宣扬专制独裁合理化,一种是阉割民众独立精神并宣扬奴才思想合理化。这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使人们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战争时期多奸细,和平时代少党论,无不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国、家界限的消失,使专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间无规律跳跃。专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会就会吹拂凄风惨雨,如果人们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会显现,各项事业就会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体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禁锢了人的创造力。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被装入坛子的人紧缩手脚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坛子被打碎以后,那个人却毫无舒展手脚的欲望,仍然缩手缩脚蜷着身团在那里。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长久浸泡于某种氛围,人就会由不适变为习惯。专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对人都有这种作用吧。
“冷拒”与“酷拒”
纳谏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拒谏则各有各的不同。“冷拒”与“酷拒”作为常见的拒谏方式现于市面的时候,你会非常同意这一点。何谓“冷拒”?又何谓“酷拒”?且容我先摘抄几段旧事。
周厉王做天子的时候,好利又近佞臣,大夫芮良夫劝他不要与百姓争利,也不要任用小人,并讲述了一大堆理由,结果“厉王不听”,还是继续他所做的一切。(据《史记·周本纪》)还是这个厉王,见人民议论他,便派了暗探监视,“以告,则杀之”,用这种方法禁绝了人民的声音。于是召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两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据《国语》)这番话很有道理,结果却还是“王弗听”。
这是拒谏的一种方式。
1519年,明武宗决定南狩,百余名大臣极力劝谏,其中医士徐鏊还用南狩有碍养生之理上谏。武宗却把他们有的下诏狱,有的罚跪。大理寺的10名官员“自以职在平狱,请停止诸臣留驾之罪,且上疏极留”。
皇帝大怒,下诏狱不算,又降旨这10人和以前的几个人一同戴上枷锁,罚跪5日。不想又有二十多人“上疏极谏”,当然还是下诏狱,并罚跪5日。可能是谏者太多侵犯了皇威,也可能“囚徒满前,观者辄泣下”
的景象使皇帝失了面子,这位武宗不仅怒得杖笞了各位谏臣,而且动用了调任、降级、夺俸、削职等手段,最后有十几个人因杖而死。(据《明武宗外纪》)明武宗和周厉王拒谏的方式是不同的,明武宗以强力拒谏,自己想做的,别人就不能持否定意见,否则就行使自己的权力,让人不死也要脱层皮。此可称为“酷拒”。周厉王的拒谏方式是“不听”,没有采纳芮良夫和召公的建议,但也没有毒打他们,没有扼杀他们的生命。当然,周厉王最终仍是我行我素,你讲了也白讲,说了也白说,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拒谏之法没有强力参加,只有冷漠,我称它为“冷拒”。历史上拒谏的事,这种“冷拒”可以说占了大多数。
从谏者的角度说,谏而不用比谏而获咎要好;从社会效果论,无论哪一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都不利。以强力拒谏,使人生惧怕之心,难有后继者,“冷拒”则易使谏者产生怠惰之情。人浸入这种感情虽然如雾里行人,衣裳不会大湿,但此时之衣已失了干爽,日积月累必有湿透的一天。《国语》记述,厉王不听召公的谏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尤其重要的是,进谏者如果多次劝谏,“冷拒”者常生厌烦之心,此时若有奸佞者从中挑拨,情势就会发生变化。伍子胥屡谏吴王不听,又加上伯嚭的谗言,吴王便“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要“子以此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从“不听”到“子以此死”,变化可谓很大,粗看是伯嚭之言起了作用,其实还是吴王自己对伍子胥早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