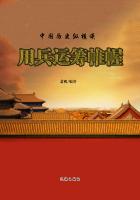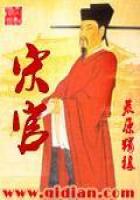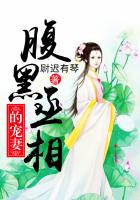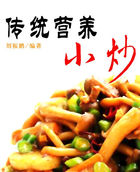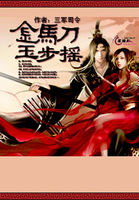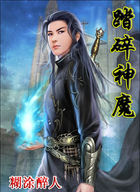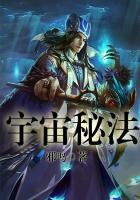一、汉族风俗研究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风俗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时,就有了“采诗之官”,他们到各地收集有关风俗资料,以供统治者“知得失”、“自考正”。春秋时的大思想家孔子,针对风俗的特点,提出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著名论点。到了汉时,朝廷更是专设了乐府,它虽系以采集各地民谣为主,但仍不失为我国最早的风俗研究机构。此后,风俗研究日趋受到重视。历代历朝的官修史书都把风俗当作记录的内容之一;各种文人笔记也喜欢以一定的篇幅用于载录风俗事项。到魏晋南北朝时,则出现了第一本风俗专记。以后各种风俗著述不绝于世。风俗研究这一优良传统始终得以继承,并被发扬光大。考察汉族社会的风俗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风俗研究基本上以采录和记述为主。而这种采录和记述又有附录式、兼录式、专录式、汇录式等区别。
附录式,即古人在叙事、说理时附带记录了一些风俗资料,如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著作对风俗事项的载录都是附带性的载录。
兼录式,则时载记载朝代沿革、帝王变更等历史大事时,也兼顾记录当时的风俗。如《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其中就兼记了当时汉族社会的许多风俗文化,主要集中于《货殖列传》和《乐书》中。其中《货殖列传》对当时各地的民情和习俗的记载颇为详尽。如它总结当时各地的生产风俗道:“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 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之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又如《汉书》,其中的《地理志》和《礼乐志》就记载和论述了当时各地的民风,及婚礼、乡饮礼、丧葬礼等风俗内容。此后,各种史书、地方志对风俗的采录军均属兼录的范畴。
而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录式风俗著作。记录了两晋南北朝时楚地的岁时节令和风物掌故,内容包括历史事件与人物、农事、生产、防病治病及卫生、祭祀祖神、婚姻和家庭、文娱、体育及旅游活动、迎新去恶等方面。 谭麟:《荆楚岁时记释注》,《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它保存的当时的岁时风俗习惯,为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的地方风俗提供了最翔实的材料,也是中国第一本有关岁时节日方面的专门著作。至于宋代出现的《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也属于专录式风俗著作。《梦华录》全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被后人誉为是“先秦迄宋第一部系统、全面记载城市市民习俗的书籍。” 刘德红、盛义:《中国民俗史藉举要》,第14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梦梁录》则详记南宋都城临安建制、人物和风俗民情,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
唐宋时期出现的《岁时广记》则是一部汇录式风俗著作。《岁时广记》采集宋代及宋代以前诸书的岁时风俗内容,如《月令》《尔雅》《淮南子》等,按目分隶,载录元旦、立春、人日、上元、中和节、社日、寒食、清明、佛日、端午、天贶节、三伏节、七夕、中元、中社、重九、下元、冬至、交年节和岁除等节日的各种节俗活动。对后人研究宋代或宋以前的岁时风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明清时期则有大量的考索式风俗著作出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日下旧闻》,全书分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风俗、物产等十三个门类,其中“风俗”为第十一门,重在岁时节日从立春直到腊日,引书上到先秦的《周礼》,下到明清的《野获编》《帝京景物略》《北京岁华记》《燕北小记》《燕都游览志》等,可谓集了清代中叶以前燕地风俗书籍之大成。《日下旧闻考》扩大了原书的篇幅,“风俗”就用了3卷的篇幅,将原书的60余条扩至180余条,使之成为清代记述和考汇北京风俗的最完整的资料总集。在汉族风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另外,还有《通俗编》,记录和考索我国丰富的民俗用语和风俗事象,系编著者多年用力搜索有关书籍和见闻积累所得。其中分时序、伦常、仪节、祝诵、行事、交际、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俳优、故事等卷,记录和考证风俗最详。而清代余怀的《妇人鞋袜考》、蔡子嘉的《历代服制考原》、俞敦培的《酒令丛钞》、毛先舒的《常礼杂说》等则分别对历代服饰、礼仪、娱乐等习俗资料加以汇集和考证,均具有独特的风俗学术价值。
从附录式,到考索式,这反映了我国古代风俗研究所走过的基本历程。而到了近代,直到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的出现,则表明我国的风俗研究已进入系统、综合、思辨的新时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风俗学研究真正出现。
二、汉族风俗史的研究
汉族风俗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经十几年努力探索,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1.在汉族风俗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风俗的民族性
18年前,我们刚开始策划开展风俗史研究时,定的方向是“中国风俗史”,但是几经考虑,发现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那就是中国有56个民族,如果耍写中国风俗史,那么必须包括56个民族的风俗史,这在目前的学术条件下,以我们的能力是难以做到的。20世纪初,张采亮撰写的《中国风俗史》,在开中国风俗史研究的先河上无疑是功不可没的,但其内容由于缺少少数民族的部分,实际上只是汉民族的风俗史。因此,我们研究中国风俗史,不能重犯了张采亮的“错误”。
仔细想来,张采亮为什么会以汉族风俗史作为中国风俗史呢?其根本原因正如我在《汉民族研究再议》中所说;“汉民族研究之所以被视而不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一些同志习惯在中国通史与汉民族史之间划等号,似乎研究中国通史就是研究了汉民族史。……究其根源,形成这种习惯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庸讳言,恐怕还是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在历史上,由于封建正统思想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占统治地位,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的传统观点,在封建史家中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徐杰舜:《汉民族瓦史和文化新探》,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因此,为了避免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我们深感在中国风俗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风俗的民族性。于是,我们在能力和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改变了初衷,将风俗史研究的方向从中国风俗史改为汉族风俗史。
方向确定以后,在汉族风俗史研究的内涵上如何把握风俗的民族性呢?
众所周知,所谓民族性是渗透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精神或意义,它是某种在苎族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它具体地表现为民族心理和由民族心理构成的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风调。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这就是说,民族性是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性的东西,其具有认同性,即“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一种意识;相对性,即在与其他民族的相对比较中,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特性;内聚性,即本民族团结起来的一种向心力;稳定性、即把本民族与他民族相比较而明确区分的一种心理定势。彭英明、徐杰舜:《从原始群到民族——众共同体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0—281页。而风俗一般来说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其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活灵活现地反映和表现一个民族的风姿、风貌和风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费孝通:《关于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风俗是一面镜子,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展示出自己的风俗,不是像镜子一样地照出了自己的风姿,风貌,乃至风韵吗?又因为风俗是一个模特儿,无论谁要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最佳的途径就是先了解其风俗,看一看这个民族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看一看这个民族如何种田、如何种树,如何饲牲口,如何经商;看一看这个民族婚仪如何进行,葬仪如何进行;看一看这个民族过些什么节日,信仰什么神怪,便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概貌。有人认为风俗习惯具有同一性,许多风俗在各民族中间普遍存在,对此,我们并不否认,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仔细分析、比较和研究,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大都有只属于它自己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风俗。对此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语家和哲学家别林斯基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议论,他在《文学的幻想净中说:
“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些差别性之间。习俗恐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构成着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那采取顶礼膜拜形式的宗教理解;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为一切阶层的共通的语言,尤其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为一切阶层的共通的语言,尤其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特殊的、仅属于它所有的习俗。这些习俗,包括着服装的样式,其原因应该求之于这国土的气候,包括着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其根源隐藏在这民族的信仰、迷信和理解之中;包括着不可分割的国家相互间的交换形式,其浓淡色度是由社会法制和阶层判别所造成的。一切这些习俗,被传统巩固着,在时间的流转中变成神圣,从一族传到一族,从一代传到一代,正像后代继承着祖先一样。它们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汉族风俗中的研究中注意汉族风俗内涵的民族性,对各个时期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作了概括,如先秦汉族风俗的特点是原始、滥觞重礼和神秘;秦汉汉族风俗的特点是急进、奢侈、迷信和儒化;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的特点是叛古、趋时、突变和多元;隋唐汉族风俗的特点是开放、奢靡、胡化和务实,五代宋元汉族风俗的特点是逾制、侈纵、尚乞和定型;明代和清代前期汉族风俗的特点是违制、重商、奢侈和趋新:清代后期和民国汉族风俗的特点是承启、融汇、非衡和西化。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汉族风俗的基本特点是农本、儒化、兼容和神秘。
2.在汉族风俗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风俗的历史性
风俗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是动态的,变化的。任何一种风俗事项都有它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因此,对风俗史的研究就不同于风俗志的研究。风俗志的研究着重强调风俗的现状,告诉人们某一个时期或时代的风俗是怎么样的,是一种定型的描述。而风俗史则着重强调风俗演变的过程,告诉人们某一风俗事项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这样,推而广之,研究一个民族的风俗史,则必须把握这个民族各种风俗事项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为什么有些风俗史著作名虽为“风俗史”,但由于缺乏对风俗事项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的研究,即缺乏历史性,故而给人的印象不是风俗史,仅仅是风俗志而已。
研究汉族风俗史为什么要强调要注意风俗的历史性呢?
这是由风俗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决定的。拿我们研究的汉族风俗史来说,其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汉族,而汉族本身就有一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研究的内容是汉族风俗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通俗地说今天的汉族是昨天和前天汉族发展的结果。那么今天汉族的风貌、风情和风韵与昨天和前天汉族的风貌、风情和风韵是一个样子一成不变地发展下来的,还是历史沧桑,几经变异而发展下来的呢?这就是风俗史研究的任务。在今天,面临2l世纪的新挑战,要认识今天的汉族并预见其明天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是怎么样的。这样,在新世纪的移风易俗中才可能自觉地把握风俗发展和变迁的方向。所以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59页。这句话对于我们研究汉族风俗史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