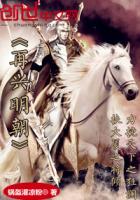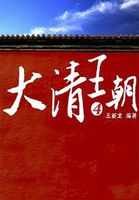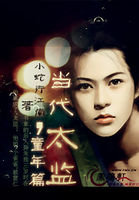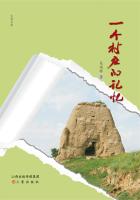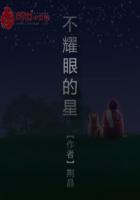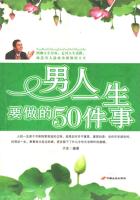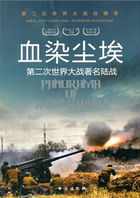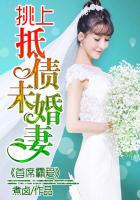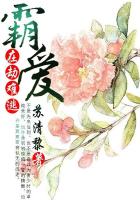“关于徐杰舜先生的报告,用台湾的话来讲是企图心很大的。用一个计划来研究汉民族,没有任何人否认,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听了您的报告,我有一个问题——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汉民族研究究竟跟汉人社区研究一样不一样?因为你提到了闽台惠东人研究计划,闽台惠东人研究计划是汉民族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吗?因为那是我们所说的标准的汉人社区研究。那个时候,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基本上是运用应用人类学来研究汉人社会。我们来看看研究汉人社会的方法,从费先生他们提过,从RobertPark,Redcuebruth,把这个communitystud夕观念介绍进来以后,我们就逐渐逐渐地在大陆、在台湾运用,而且有他们这几位,像王斯福先生他们,提出闽台研究计划的AuthorWolf啦,PassNark啦,MarrineCoine啦,或者早期的MorrieField,ModernFried他们这些人,还有Skinner,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我们可以说是研究汉人社会的,这里头,大部分人是用人类学的或者是功能学派的观念,结构学派的观念,社会学上的一些统计方法。我们回过头来对比,跟汉学研究,Sinology研究对比,就显然看到汉人社会研究跟汉学研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以为就不能叫这种研究,像王世福先生的研究啦,AuthorWolf的啦,或者李亦园先生、庄英章先生的啦,他们这些人的研究,汉人社区研究,而不是汉学研究。所以说,您现在提倡的汉民族研究,因为您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创始人之一,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创始人,在方法论上是不是要有新的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地想一想的问题,而我感觉到在方法上是应该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方法上应该是:首先把汉族当作一个整体,就像我们研究苗族,研究瑶族,研究台湾的比如说阿美族、泰雅族等这样的研究,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看它的起源啦,看它的迁徙啦,甚至于分类啦,它的语言啦,甚至于可以这样子,更宏观的‘种研究,因为这些东西,说汉人社会的研究也好,说汉学研究也好,都没有接触它,是一个空白,所以说,我想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做到一点,您提到汉民族它的文化是世界少有的,有这么长的一个传统——不间断的一个传统,这是一个事实,但怎么样去了解他的连续性,怎么样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持续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需要一个新的方法来做这一门工作。我想,既然已经提出了汉民族的研究来,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方法论的问题,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
李先生和乔先生的评论给我以深刻启示,是啊!我开拓汉民族研究方法论是什么呢?为此,我又读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书,整整思考了一年多,向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高级研讨班提交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和方法论》的论文。
这一次的学习和思考,对我正在进行的“汉族历史文化”课题研究起了关键性的根本性的改造作用。我完全放弃了原来按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的框架,对其作了彻底的改造,运用在研讨班上学到了有关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决定按七个不同人文地理区域分别论述其历史、方言、族群和文化,即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的分析。
为了能顺利地完成“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这个课题,我于1996年12月,1997年12月分别在南宁和上海召开了两次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尤其是在上海的会议上,课题组内对是否运用和如何运用族群理论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进行解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知道要接受一个新的理论是很不容易的,我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大家。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认同和努力下,在1997年初稿的基础上,1998年上半年大家又作了全面的修改,终于于7月5日按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订的约稿协议所规定的时间交出了130余万字的书稿《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1998年7月6日中午,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施宏俊两位编辑在讨论我的书稿时,施宏俊提出现在的书名太直,能否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全书的内容加以提炼、概括,取一个像《菊与刀》这一类的书名。我听后很受启发,经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审视后,我提出用“雪球”作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副标题。为此,我撰写了一篇《题识》,对《雪球》书名的缘起,以及为什么要起这个书名作了解释。这样,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9年8月,《雪球》一书终于问世,并赶上了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汉民族研究的一棵树终于有了一个伴,此为汉民族研究“见林”的第一步,一首名为《有伴》所言:
阳光
雨露之必要
暴烈狂风之必要
我们手拉手
肩并肩
以更广阔的胸怀
迎接更多根植土地的人群
七、成 林(下)
话分两路,我的汉民族研究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这棵“树”落种、萌芽、抽枝、扎根、成树的同时,另一棵“树”——《汉民族风俗史》也早在1983年就落种了。1983年,当我与周耀明合作编撰《金华地方风俗志》,以及后来的《浙江风俗简志·金华篇》时,我们就曾有过合作编撰“中国风俗史”或“中华民族风俗史”的动议,但由于当时我们的身份都是中学教师,一个在东阳的中学教书,一个在武义的中学任教,每天备课上课,忙于应付学生的高考,且不说当时的学术素养尚不足以担此重任,就是在精力、时间、图书资料等方面也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所以,议了一番也就将此事搁置一边了。但在我们的心中已播下了研究“中国风俗史”的种子。
1985年4月我从武义调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并于1986年底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就开始把思路和兴趣集中到了对汉族风俗史的研究上。1990年5月,我应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之邀,给该系畲族班的学生讲授中国民族史的课程。乘此机会,我请当时还在浙江工作的周耀明和浙江师大学报编辑部的陈顺宣到浙师大招待所商讨研究“汉族风俗史”的方案。由于我已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开展中国风俗史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汉族风俗史进行研究,建议以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为线索,全面、系统地研究汉民族风俗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撰写一本原创的《汉族风俗史》。我的建议得到了周、陈的支持。说干就干,周耀明提出趁热打铁,请浙师大中文系的陈华文(现为教授)、周少雄,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郑元者(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虞县委党校的阮其龙、丽水市方志办的唐乐平以及杭州的胡缨一起来讨论并分工。好在浙江不大,除陈华文和唐乐平因故不能来以外,其他几位接到电话后就纷纷赶到了地处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
在浙江师大招待所举行的《汉族风俗文化史》研究和撰写分工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汉族风俗史》全书分绪论、原始社会风俗、先秦风俗、秦汉风俗、魏晋南北朝风俗、隋唐风俗、宋元风俗、明代风俗、清代风俗、民国风俗和当代风俗等11章,篇幅大致在100万字左右。当时的具体分工为:徐杰舜负责绪论和先秦风俗、秦汉风俗,郑元者负责原始社会风俗,陈华文负责魏晋南北朝风俗,周少雄负责隋唐风俗,陈顺宣负责宋元风俗,周耀明负责明代风俗,唐乐平负责清代风俗,胡缨负责民国风俗,阮其龙负责当代风俗。心仪多年的中国风俗史终于萌芽了。
学术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汉族风俗史的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的因种种原因退出了,而有的又加入了进来,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万建中教授一加入进来就挑起了重担;
——有的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完成研究任务,如郑元者、胡缨和阮其龙,他们虽然都写出了自己负责部分的初稿,但因体例不同和内容简略,而又不能进行修改而放弃了;
——有的因种种原因虽然写出了初稿和二稿,但没有参加后面的修改。
虽然如此艰难,但我和周耀明仍然坚持不懈,一直到1997年,章目经过调整的《汉族风俗史》的初稿总算基本完成:
徐杰舜——绪论、先秦汉族先民风俗
万建中——秦汉汉族风俗、隋唐汉族风俗、民国汉族风俗
陈华文——魏晋汉族南北朝风俗
陈顺宦——宋元汉族风俗
周耀明——明代汉族风俗、清代汉族风俗
《汉族风俗史》初稿120万字,各章极不平衡,而这时万建中、陈华文、陈顺宣都因学务和教务缠身而不能参加修改,这时周耀明挑起了全面修改的重担,他对从秦汉到民国的各章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从体例和行文风格上向徐杰舜撰写的先秦汉族先民风俗靠拢。周耀明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努力,于1998年10月完成了200万字的《汉族风俗史》第二稿,《汉族风俗史》在中国学术的沃土上顽强地扎下了根。
《汉族风俗史》第二稿杀青后,我们为了该书的出版而历经了艰难。
在我们还在撰写《汉族风俗史》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即向一家师范大学的出版社报了选题,但如石沉大海,沓无音信。第二稿杀青后,1999年6月我乘到昆明参加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五届高级研讨班演讲之便,与云南一家出版社联系。在该出版社的P编辑办公室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汉族风俗史》也表现出了兴趣,要我回南宁后将目录寄他审阅。我回邕后立即将《汉族风俗史》的目录用特快专递寄给了P编辑。但是很遗憾,过了近半年后,我打电话向他询问结果,他竟说没有见到目录!于是我又用特快专递寄了一份,但是以后的多次电话询问他都支支吾吾地打发我。
在与云南的这家出版社未果之后,我们就将书稿送广西一家出版社审阅,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多后,书稿在该出版社睡了一年多的觉,编辑根本没有看过。在这种态势下,该社的R社长认为篇幅太长,要出版必须压缩到80万字。据说是被出版社奉为“衣食父母”的作者,这时面对“牛高马大”的出版社,只好忍痛割爱,将200万字的书稿压缩到了80万字。但是这样还不行,出版社还要我们砍去一半,全书必须压缩到40万字才可考虑出版。而对这种情况,我们反复斟酌了以后认为这样也好,出一本40万字的汉族风俗史虽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但用另一种方式使我们对汉族风俗史的研究成果能够问世,在无奈之中也是一个出路,于是便有了《汉族风俗文化史纲》的问世。
但是我们并不死心,“天生我材必有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们坚信,《汉族风俗史》是原创性、开拓性的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她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必然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一定会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会衷情《汉族风俗史》出版的。
果然,《汉族风俗史》的伯乐终于出规了,他就是上海学林出版社的社长曹维劲先生。2000年7月,我与我的夫人徐桂兰到上海、苏州、天锡、南京一带去考察时,为了《中国民俗丛书》的审查问题,我们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徐华龙先生一起去拜访了位在上海钦州路出版大厦的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曹维劲先生。
上海学林出版社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经常读他们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心中对学林出版社存在着一份敬意。进入上海出版大厦,我们一行三人进入曹社长的办公室。曹社长是一个爽直的人,三下五除二地谈完了有关“中国民俗丛书”审查问题。我怀着对学林出版社的敬意,向曹社长谈及了我主编的《汉族风俗史》。果真名不虚传,学林出版社不愧是学术名社,曹社长一听了简要介绍,立即表态肯定《汉族风俗史》是一部创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要我回南宁后尽快将全书的目录、样稿,以及钟敬文老先生写的序寄给他,以便他向社委会提出讨论。曹社长的果断给了我的极大的信心。我的材料寄出不久就得到了回音,曹社长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林出版社决定与我签定一个意向协议,要我根据我们社里的意见作一次修改,待书稿定稿后再送出版社审阅,然后再定出版协议。在我们修改书稿期间,曹社长经常在电话里了解我们的进度,并及时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或提出建议。这样从2001年2月开始,历经8个月,到2001年11月,我们按照学林出版社提出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并补充插入了200多幅图片,使得全书生动、活泼起来了。写到这里,我们从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感激之情,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曹社长及学林出版社能高瞻远瞩,站在学术的前沿,大力支持《汉族风俗史》的出版,这不仅是《汉族风俗史》及其作者们的大幸,也是汉民族研究的大幸,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幸。如果出版界中像曹维劲社长这样的出版家多一点、再多一点,那不是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吗?所以,我一与学术界的同仁说起此事,我就激动,就感慨万分,而同仁们也大都有此同感。因此,我们衷心地感谢曹维劲社长和学林出版社。虽然“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如果不是及时得到曹社长和学林出版社的认同,《汉族风俗史》出版要等到何时,我们真的不敢去想!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响起了一首小诗《见林》的吟颂声:
当万千种子
纷纷吐芽
我将祈愿
所有学术同好
悠然梭游
在汉民族研究的绿色海洋
八、挖井与种树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学术研究却是无限的。从1961年到2001年,在我治学汉民族研究40年学术生涯中,我选择和坚持了汉民族研究的方向,从1962年提出汉民族也是从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到1985年出版《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到1992年出版的《汉民族发展史》,到1999年出版《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到2001年出版《汉族风俗文化史纲》,以及2001年11月杀青的《汉族风俗史》。好像挖井一样,积40年的功夫才将汉民族研究这口井挖好、挖深。正因为深挖了井,才广积了水,从而浇灌出《汉民族发展史》、《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和《汉族风俗史》这三棵大“树”,造成了汉民族研究的一片小树林!回顾40年治汉民族研究的经历,我感到欣慰,也感到骄傲,因为怏怏恢宏汉民族的学术之林是由我这个小小布衣栽种,浇灌和抚养成林的!
2001年10月11日
于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办公室
时22时4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