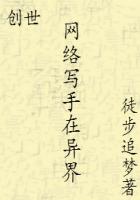被押来受审的是贾母,贾王氏和薛王氏,刑夫人和迎春,探春并没有被押过来。黛玉坐在宗正寺大堂后的暗房之中,在这里可以看清大堂上发生的一切。贾母被带上堂来,她身着红色的罪衣罪裙,一头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松松的面皮垮下来,看着好不狼狈。黛玉看着如此狼狈的贾母,心中五味杂陈,不由轻轻叹息了一声。
“贾史氏,你可知罪?”水沏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
贾母面向水沏跪倒,哀声道:“太子殿下,犯妇知罪。”
水沏冷喝道:“你既知罪,便从实讲来。”
贾母伏声哀声道:“回太子殿下,犯妇儿媳王氏利欲薰心,贪占犯妇女婿的家产,犯妇知情不举,反而处处为她遮掩,犯妇包庇有罪,愿受太子殿下惩罚。”
黛玉听了贾母的话,轻轻摇了摇头,低声道:“她竟还不知悔改。”
水沏听完贾母之言,气得一拍惊堂木道:“贾史氏,孤王问你,你院子东北角地下所埋尸骨是何人的?”
贾母身子一颤,伏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向水沏,急忙道:“犯妇愚昧,不知太子殿下所言何意?”
水沏淡淡道:“紫英,将老国公的书信拿与她看。”
冯紫英躬身称是,拿着老国公的信走到贾母面前,展开信纸喝道:“你看仔细了!”
贾母颤微微抬起头,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贾母顿时如五雷轰顶,她双眼定定的盯着那封信,良久之后大叫道:“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水沏沉声道:“孤王已经找出老国公生前的奏章核对过笔迹,贾史氏,你再否认也没有用。”
贾母大叫道:“不,这不是真的,这是有人故意陷害我,能模妨笔迹的人多了去了,当年我的敏儿就能模仿她父亲的笔迹,当日老国公在时也说过敏儿模仿他的笔迹足可乱真的。”
主审的水沏陪审的水溶听审的林成和黛玉,听了这话都气得火往上窜,黛玉攥紧双拳拼命的控制着自己,才没有冲出暗房去同贾母理论。她转过头对兰心说道:“娘亲说过外祖父的笔力苍劲刚硬,大有铁马金戈之风,她能模仿许多人的笔迹,却唯独模仿不了外祖父的。你去告诉沏哥哥,免得被她骗了。”
兰心在暗处招手将卫若兰叫过来,将黛玉说的话一字不错的告诉他,卫若兰又去告诉水沏,水沏一拍惊堂木喝道:“大胆犯妇竟敢胡言构陷林夫人,孤王随林先生学习之时,师母便说过老荣国公一笔一字都透着肃杀之意,旁人绝无法模仿。来人,上拶子,不给这老刁妇几分颜色,她不会说实话。”
一个衙役到贾母背后压住贾母的双肩,另有两个衙役将拶子套在贾母的双手上,勒紧之后便向两边拽,十指连心,贾母疼得“啊……啊……”大叫,两个衙役只用了三分力气,贾母已经疼得满头大汗,整个身体瘫软在地上。
水沏沉声道:“贾史氏,孤王劝你从实招来,也免得皮肉吃苦。”
贾母瘫在地上喘息一阵子,抬起头道:“殿下,您要犯妇招什么?犯妇没有做过,怎么招?”
水沏冷声道:“你既不知孤王要你招什么,又怎么说没做过?看来你是知道孤王要你招什么。”
贾母只觉得十指之疼疼入肝肠,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心思听水沏说的话,只反复说道:“犯妇什么都没有做过。”
水沏见贾母死扛着不认,便沉声道:“贾史氏,已故林夫人贾敏可是你亲生骨血?”
贾母想也不想便叫道:“她当然是犯妇十月怀胎所生的孩子。犯妇命中无子,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可怜她竟先我而去,只留下玉儿这可怜的孩子。”贾母已经知道水沏对黛玉有心,所以此时竟拿黛玉做说辞,希望水沏能看在黛玉的面上放过自己。
听到贾母之话,不论是堂上的水沏水溶还是暗房中的黛玉林成,都气得几乎难以自制,水沏大喝道:“堂下犯妇,孤王再问你一遍,林夫人可否是你亲生?”
贾母一口咬定道:“敏儿是犯妇亲生。”
水沏大声道:“来人,请绛仙县主,与堂下犯妇滴血认亲。”
贾母顿时怔住了,她没想到黛玉此时竟然就在这大堂上。这可怎么办,贾敏不是自己亲生的,黛玉的血不可能和自己的血相融,怎么办?怎么办?贾母急得出了一身汗,还没等她想出什么说辞,黛玉已经暗房中走出来,站在公堂下面。
冯紫英端过一只托盘,盘上有一把刀和一碗清水,他先将贾母的血滴到碗中,又将托盘送到黛玉面前,黛玉拔下头上的银簪刺破手指,挤了一滴血滴到碗中,只见那滴血之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排斥力,怎么都不靠近,更不要说是相融了。
看了这样的结果,黛玉转身向水沏跪下,一字一字说道:“回太子殿下,臣女与堂下所跪之人的血不能相融。她不是臣女的外祖母。”
贾母急忙叫哀声叫道:“玉儿,我是你的亲外祖母,你怎么能这样狠心,连外祖母也不认,你娘亲若是知道,定然会伤心死的。”
黛玉站起来,转过身看着贾母,沉声说道:“我狠心?老太太,你们在我服的药中下毒,强占我爹爹送给我的东西,爹爹刚去世,你就强逼着我借银子给你们贾家,给没有一个贾家人的贾家。如此种种,到底是谁狠心?难道我非要任你们宰割,直到不明不白的死了,才叫不狠心么?老太太,难道我要象你们一样,才叫不狠心?”
贾母被黛玉问得哑口无言,黛玉那双清澈的目光喷射着无法遏止的怒火,逼视着贾母,贾母一阵心虚,她不敢看黛玉那双好似能看透一切的眼睛。
黛玉回过头来对水沏说道:“太子殿下,请您为臣女外祖父,外祖母,小舅舅做主,还他们一个公道,让他们能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