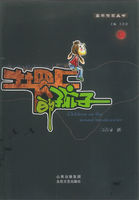劳伯先生是公司里的噪声专家,在技术问题上发个话,平辈晚辈们都敬让三分,只是在公司里混了三十多年,才熬到今天这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虽说整个实验室唯他独尊,手下不过二三后生晚辈。眼看退休年限已近,再升迁的机会渺然,自然牢骚满腹。牢骚多了,就有些怒发冲冠,一头早白的银发就总是不驯服地直立向天。前些时公司不太景气,老先生站在办公室中央发牢骚,几十年的老账都被他翻出来数落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这些人不能退休,没有了我们的监督,那些头儿脑儿们还不得更肆无忌惮地胡搞?这公司非让他们搞垮不行。俨然一副主人翁兼家长的姿态。可也是,老先生半辈子的生命贡献给了公司,剩下的年头自然与公司的荣辱兴衰休戚相关,更何况,退休后的生活还得仰仗公司的福利。
说归说,怨归怨,终究还得替自己打算。去年春天,劳伯在附近的乡村勘探了一块百十亩大的风水宝地,于是利用公假私假病假大兴土木,然后将几十年积攒的盆盆罐罐搬了过去,准备种一些农作物、养几只牛羊,过神仙的日子。每天来办公室打打照面,填填计时卡,就没了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从此便要退隐了,谁知过了半年他又回来了。问他怎么又还俗了,他说他毕竟只是个凡夫俗子,耐不得神仙般的清净。整天面对一张看了几十年的老脸和一群不懂人语的动物,让他心烦。空有满腹牢骚,只能对老伴发。老婆可没有公司领导们的修养和耐性,几次下来,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起来。劳伯男不和女斗,就又躲到办公室来倚老卖老。
劳伯不在的那些日子,办公室的确冷清了许多,也着实让众人怀念他那神侃胡聊。老先生吃不住人的尊敬,只要有人请教,事无巨细,不分公私,一视同仁,拖把椅子坐下开聊。大概是怨气积胸多年之故,开口句句不离“他妈的”。谈私事家事还好,不过一句一个“他妈的”,论到公司之事,哪怕是技术问题,必定以“他妈的”做各名词的形容词,于是一句话便带出几个来。也许是话多容易引起口干,手中便不离他那只硕大的咖啡杯。杯子不知用了多少年,外面的咖啡垢几乎遮盖了杯子的原色。老先生聊到兴处也总不忘呷一口或冷或热的咖啡。初识之人见景免不了望而生畏,公司里有年头的人都早已见怪不怪,不过背地里少不了拿来做笑柄。
另一个让人公开或背后取笑的是劳伯的办公桌。劳伯在公司里有些地位,便占了两个工程师应有的桌面。那桌上除了满是污垢的咖啡壶和计算机外,就是各种各样的纸头,堆得有一寸厚,只在键盘前有一块巴掌大的干净地,还常摆着他的午饭和零食。公司调整后,科里来了一批极爱自己干净又爱周围环境整洁的人。那些人时不时地从劳伯的桌前经过,觉得忍无可忍,一状告到了新科长那里。科长去实地考察一番,也觉得脏乱得不堪入目。但劳伯资格老,科长也不敢当面指责,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柄上方宝剑,开会时宣布公司里有了关于整洁办公室的新规定,把那规定拿出来煞有介事地宣读一番,制定了目标,规定每周五个人清理自己的办公桌,下班前值日小组长检查记录,下周二科室列会上公布结果。于是会后人人立即动手,清除废纸灰尘,唯劳伯不理那套,照样我行我素。接连几周,劳伯名列脏乱榜首。众人虽有不满,不愿吭声。有一个极爱整洁的小组长跳出来扬言说组长有权清理手下组员的桌子。但劳伯不属他管,他也是敢说不敢动手。瞅准劳伯忙乔迁新居之时,还是忍不住叫了一个泼辣的同事去帮劳伯清理了一番。劳伯回来后,越看那桌子越不顺眼,拖把椅子坐在过道里,两脚往邻近桌上一翘,开始发牢骚:“什么他妈的人订的这他妈的条文?看人家公司,台球桌摆在办公室当地,职工们工作累了就去打几下,也没见人家影响月月盈利。咱这鬼地方只盯着他妈的办公室整洁不整洁,咖啡壶干净不干净,股票照样他妈的往下掉。我他妈这桌子倒是干净了,几张重要的纸头不见了,谁他妈负这责?”从此没人敢再去动他的桌子,也没人再在明处抱怨他的办公桌影响了整个办公室的美观。不过劳伯的桌上还是利落了不少。科长趁机往上报了一功,说这项活动大有成效,连劳伯都改变了,本科的工作效率必会大有提高。这劳伯的不拘小节可是远近闻了名的。
劳伯的桌子够乱的,咖啡杯够脏的,肚里的牢骚也够多的,技术上也确实有一套。劳伯天生好记性,桌上的零乱与他脑子里的条理,就像他身上那高档西装上衣吊带裤和手中脏兮兮的咖啡杯一样极不相称。经他手做出来的实验一个个都漂漂亮亮,有理有据。实验数据是不屑处理的,都交给晚辈干。劳伯的任务就是指挥指挥。数据整理出来,他拿去看一看,拣重要的装在脑子里,懒得细细地保存那些纸头。谁要用时去问他,他稍一思索,就从脑子的哪个角落挖出来给你,一点不含糊,颇像公司里噪声技术资料活百科。按说,这样的技术功底,退休前再升一级也不为过。劳伯琢磨得大概也是这件事。年前,科里一个几年难遇的大项目上马。上马伊始,各路人才争显神通,劳伯也挤上去凑一手,出谋划策,忙里忙外,很是热情了一阵。开会时,牢骚少了,“他妈的”没了,手里的咖啡杯也换了个新的。新项目张张扬扬了一阵子后,建议听过了,大框框定了,人马安排就绪,按部就班,分析,实验,设计,再分析,再实验,再设计……劳伯闲了,又开始坐在过道里开聊,“他妈的”又挂在了嘴头上。
适逢高科技腾飞的年代,劳伯把公司里噪声上用不了的脑子精力用在了高科技上。家里一连买了几台计算机,下班没事就鼓捣。把几台计算机联成网,各种软件也都试用了一遍,裁定出优劣。实验室的计算机更是被他更新换代,硬件软件搞得条条理理,连公司里专职搞软硬件的工程师也对他刮目相看,时不时来向他讨教几句。于是劳伯又多了个“计算机专家”的业余头衔,办公桌前又很热闹了一阵。
前一阵子,办公室里很安静,听不见劳伯的声音,看不见劳伯的身影,说是去收秋蓄冬了。那天从他桌前路过,老先生正坐在计算机前聚精会神玩扑克游戏。我悄向旁人打听,人说,劳伯看开了,反正升级无望,乐得清闲,谁也不能开除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乐乐呵呵过他半年一载,混到退休,归隐田园。“你不见,退休倒计时表已挂在墙壁上了?”
这劳伯要是退了休,少了劳伯的神聊,没了劳伯的脏乱,办公室里也缺就了一景。
注:“DAMN”应直译成“该死的”,此处篡改成“他妈的”,纯粹为了文章顺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