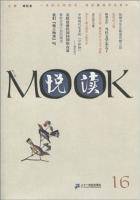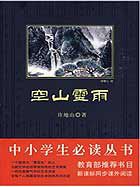当我握着母亲的手,感到母亲的体温渐渐消失,我意识到母亲走了。从此,握手告别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忆引来无数个夜深人静时的思念,而每次的思念都是从最后痛苦的握手追忆到最初甘甜的日子。
初识母亲的手是在懵懂的童年时代。每晚钻进被窝,一边听母亲讲童话故事,一边享受着母亲的抚摸。母亲用手抚摸我的背,酥酥痒痒,舒服极了。我总是强睁着眼睛撒娇:再讲一个,背还痒痒。原来那舒坦的感觉源于手的粗糙,难怪父亲那光滑的书生之手,摸得不痛不痒,像是敷衍了事。
能造化成母亲那样的手是要经过数十年如一日、寒冬酷暑的千锤百炼。那时候,家里没有煤气、暖气、洗衣机,厨房里没有冷热水,一切都得靠母亲那双手。清晨,母亲第一个起床,热水打扫生火做饭;白天,除了操劳三餐之外,母亲还要打扫洗衣缝纫做鞋;入夜,我们都进入梦乡,母亲在灯下边做针线活边等还在办公开会的父亲。日复一日,母亲的双手经受碱面洗碗、肥皂搓衣的摧残;漫长的寒冬里,户外水管上的洗衣洗菜,刀子般的冰水寒风更给双手划出道道口子。
母亲的双手经千锤百炼,变得如同寒山冻崖上的老树,饱经风蚀雨浸,温润细嫩不再,只落得枝节突出、筋脉显露、粗糙变形。
正是因为家里有了这双粗糙的手,全家人的饭桌摆上了精致可口的一日三餐。母亲的饮食哲学是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在那物质食品匮乏的年代里,母亲粗粮细做,变化着花样。每天早晨,全家人起床后,用母亲准备好的热水洗漱干净,吃完热乎乎的早餐,各自上班上学。生病了,母亲的双手擀出的面又匀又薄,切成细细的面条,加上白菜心和鸡蛋花,香极了。为了饱享母亲做的精致美味,我竟然时不时盼望着得点伤风感冒。每逢节日,母亲的双手能变化出各种应节的食品。腊八粥、春节的各样菜品、点心,端午的粽子不必多谈,那七巧节的面人可不是每个母亲能做的活。我总是站在案板前,踮着脚边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传说,边看母亲双手下变幻出的面塑,其中有申猴、卯兔、未羊、丑牛、戌狗、金鱼等,而趴着、躺着、翘着腿、扬着头的各种胖娃娃更是形态各异、活泼可爱。
正是因为家里有了这双粗糙的手,全家人的身上穿着整洁合体的四季衣裳。母亲那双看似笨拙的手,却巧如天仙,是女红高手。家里大到父亲的中山装,小到我身上的花裙子、头上的蝴蝶结,都是母亲自己裁剪缝制的。姐姐有条店里买来的裙子,母亲便买块花布,仿照为我制成同样有白领边、白腰带、白袖口的漂亮裙子。母亲能创新,对色彩敏感。别人家孩子的棉手套是一种布料同样颜色,不是蓝布的就是黑布的。母亲从包袱里找出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做成黑灯芯绒手心,墨绿呢子手背的手套。母亲的剪裁缝纫手艺好,成衣后领子周正、肩袖松紧适度,针脚细密均匀,衣服平展,常常有邻家的大妈请母亲帮忙裁剪衣裳、取鞋样。母亲还会绣花,她不用花样,自己用笔大概画个样子,配上不同色彩的丝线,一朵朵深浅典雅的秋菊、玫瑰就栩栩如生。母亲总是用那双巧手装扮着姐姐们和我,让我们从小就对衣着有审美观,并充满自信。
初识文字,常向母亲求问,母亲总是边写边说:总不写字,很多字都记不住了,笔也拿不稳了。年幼的我,竟然因母亲变形粗笨的双手而对母亲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心想母亲的手大概只会做家务。第一次上剪纸手工课,老师给我们萝卜纸样,让我们回家照猫画虎地用红色蜡光纸剪出红萝卜。母亲建议我用红纸剪萝卜,绿纸剪叶子。开始我不同意,理由是老师示范的范本只是用一种红色纸。结果我那唯一的双色作品受到老师的赞赏,并被当成范本贴在了墙上。从此,我懂得艺术不要拘泥,要敢于创新。童年初涉绘画,画桌椅,画了四方的桌面,却不知该怎样画四条腿。母亲教我把四方形改为平行四边形,自然四条腿也有了摆的地方。会画桌子了,便能举一反三地画椅子和房子。我成了幼儿园班上第一个用透视概念画画的,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羡慕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手工和画画课使我的各种兴趣在享受中得到开拓和发展。中学里我对画画的喜爱和追求,大学里上制图课的轻松和遐意,都离不开童年时母亲那变形粗笨的双手带给我的帮助和启蒙。
母亲的双手好像从来不会疲倦。那时候的母亲,除了一般的家务外,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针线活上。做针线活是很辛苦的,劳力又劳心。其中工序最多,辛苦最大的大概就数做鞋。打袼褙、剪鞋样、沿白边儿;然后搓麻绳、纳鞋底、做鞋面;再就是绱鞋,将鞋底和鞋面缝合在一起;最后,将鞋楦把鞋衬好,大功才算告成。十岁前,除了夏天的凉鞋和运动的球鞋外,我穿的布鞋和棉鞋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常常是剁好饺馅,再敖夜完成新鞋。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枕头旁摆着新衣,新衣上放着新袜新鞋。身着新衣,脚踏瑞雪,随父母走门串户拜年,生活美得如皑皑白雪晶莹剔透,童心充满着灿烂的阳光。
母亲的双手似乎从来没有埋怨。母亲天天起早贪黑、无怨无悔地做着家中大大小小的琐碎事情。家务虽然繁重,但母亲从不让父亲插手,也不让我们学习分心。母亲常说:爸爸该做的事情是好好工作,你们该做的是好好学习,妈妈该做的就是把家务事做好。家里门后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父亲是先进工作者,我们是三好学生,唯独没有母亲的,一张也没有。母亲总是鼓励我们姐妹们好好学习,长大后上大学,成为自主自立的女性。从小我就有抱负和理想,上大学似乎是我理所当然要做的事。后来我和姐姐经历插队、工作,“文革”结束后一同考进大学,继而先后留学美国,不能不归功于我们有一位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母亲。母亲用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为我们经营了一个温馨的家,为我们求学上进添砖加瓦。母亲的言传身教成为我生命的影子,影响着我的婚姻观和家庭观,让我逐渐拓展出甘于牺牲和乐于付出的胸襟,拥抱我的孩子和家庭。
母亲的双手似枯树寒鸦,别误以为母亲的相貌如西风瘦马。见过暮年母亲的人,同辈说母亲有风度,长辈说母亲年轻时一定很漂亮。暮年时的母亲,端庄娴静,不胖不瘦,身材匀称,脸上除了一些轻微的皱纹和老年斑外,肤色、光泽都很好。母亲虽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却一辈子都很在乎衣着和仪表,且讲究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早年母亲着中式衣服,夏日炎热也不曾松开领口。甚至最后的几年,每日照常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梳妆打扮、穿戴整齐。
记得中学时,有一次几个女生一起比看谁的手好看,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手好看。小拇指长,有靠;手指长,可以弹钢琴;所有的指甲都是长形的,漂亮。回了家,母亲说我的手长得像她的手,母亲展开她的双手,手指偏斜,沟壑纵横。母亲说变形的手指是由于从前长年累月地做鞋,纳鞋底时用力造成的。和母亲的对比中,我看到了母亲当年手的模样。那艰苦的岁月给予我们母亲们太多的重担和辛劳,母亲的双手,便是那个年代母亲们生命的诠释。
母亲病危,蒙上帝怜悯,让我这个母亲的幺女从大洋彼岸赶回到母亲的身边,度过三天黑暗却珍贵的时间。之后的十四年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那双手。冥冥之中,我感到了那双手仍然抚摸着我,安抚我孤寂的心灵,擦拭我思念的眼泪。母亲走了,但母亲的手却始终都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