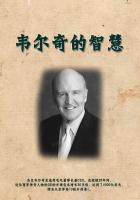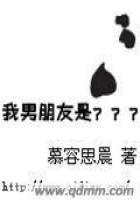祠堂在太平溪南坡后,祠堂前一座数十平方石砌台子。
午时,太平溪祠堂。
方隐仙坐在石台子中间的竹椅上,东溪乡六爷,西溪乡王二伯一早就在这里等他,两人在方隐仙面前唯唯诺诺,神情十分拘束。方隐仙知道自己此时在太平溪里的威望可能在里正这一职里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了。
东溪乡的七十户在东祠堂东边先集齐,西溪乡还差几户没有到来。
王二伯俯身在方隐仙耳畔说道:“里正爷昨晚您说了要寻出第一个煽动大伙换孩子果腹的人,本来大伙还不在意,就胡神师半夜带着两个徒弟鬼鬼祟祟上坛子岭,被我家几个逮个正着,我家几个小子正把他拉了过来。”
胡神师?巫师。方隐仙点着头,俊秀的脸上显出几分冷气。
正和马六爷王二伯谈话间,王二伯家的三个大汉叉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干瘦汉子胡神师,押到石台前。
胡神师极力仰头望向石台上安稳坐着的方隐仙,大声喊道:“里正爷,我是神明在太平溪里的使者,不能对我无礼!”
乡里诸茶户对鬼神极是敬畏,仅王二伯家与胡神师一直不睦,不信他那一套这才敢把胡神师绑着押到祠堂前。
方隐仙拍拍大腿,走到石台边沿低头端祥着胡神师,此时若不在众人面前把巫师治得服服帖帖,这病不求医的陋习还不知要遗毒多少年。
胡神师扬着下巴,向站在上方的方隐仙喊道:“里正爷,快给我松了绑,你不能亵du神明,可知乡里将有灾祸临头啊。”
方隐仙听得笑了:“你鼓动乡里吃自家孩子,也是神明的意思?”
“是,我句句代表神明旨意,绝无私念。”胡神师鹰鼻薄唇,说话间有着自然而然的蛊惑力。
方隐仙抬头望向王二伯家几个大汉:“王大哥,四哥,给他松绑了,让他上台来。”
继而大声向大伙喊道:“既然胡神师可以通晓神意,本里正让胡神师今天在这石台上请来神明,问神明胡神师什么时候死,死期由神明来定。来啊!给胡神师升坛了。”
方隐仙是一心要致这胡神师死地。若不把他给办了,接下来的事情会更加有难度。
两个胡神师的弟子抢了上来,帮胡神师把绳索给松了,又回家里去把胡神师请神的道具搬了过来。
方隐仙搬竹椅到一边坐着,让出石台中间给胡神师请神,六爷与王二伯退在方隐仙身后。
祠堂面鸦雀无声,数百名茶户望着台子上的胡神师披上牛皮,头戴牛角,左手牛骨,右手艾草,石台中间燃着一堆气味刺鼻的艾草,胡神师嘴里念着咒语,绕着艾草堆打转。
所有人,包括站在人群里的绿茗,都不知道方隐仙为何要胡神师问自己的死期。
胡神师在艾草烟里浑身解数,癫狂不已,令太平溪茶户觉得神明正在与他对话,更觉得里正爷再有能力也不可能与神明对抗啊。
胡神师尖着嗓子急骤念完一串咒语后,全身软了下来,坐在艾草堆旁,轻抚牛骨笑而不语。
两个弟子上台来把胡神师扶起,胡神师摆摆手,摘下牛角,回头望了望漠然坐在身后的方隐仙,眼里几分得意几分嘲弄。
胡神师举着牛骨向茶户大声喊道:“神明旨意,胡神师乃世间使者,渡三界轮回不休,本世阳寿八十七,还需在凡间渡劫四十五岁。”
听到这话,方隐仙从竹椅上站起,向王二伯轻声说道:“搭个手,找把刀给我。”
王二伯招手让三个儿子过来,叫他们递把刀过来。他们想上台帮手,方隐仙不许,只跟王大郎借了一把牛耳尖刀。
方隐仙提着牛耳尖刀,站在胡神师面前,大声问他:“神明说你有多少年可以活?”
胡神师见到方隐仙手里提着尖刀,惊疑不定,却绝没想到眼前这名文文弱弱的少里正已经对他动了杀意,大声回道:“尚有阳寿四十五,乃神明所诣!”
话音刚落,方隐仙反手执刀,在胡神师面前迅猛一挥,又退后几步。
‘哗’台上台下一时间都惊骇尖叫,只有两个人没有出声。
一个是执着尖刀冷然望着胡神师的方隐仙。
另一个就是被方隐仙一刀割断咽喉,捂着脖子瞪着双眼在台上打摆子的胡神师。
暗红的鲜血在太阳下迅速渗入石台的砖缝里,胡神师倒在台上抽搐着,眼睛一直没离方隐仙。
方隐仙冷冷与他对视,直至他鲜血流尽不再动弹。
整个祠堂空地上所有人忘了呼吸,心里像压了一块铅般,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就算平素对胡神师极为不满的王二伯,一时被惊得坐倒在地,不知所措。
原来杀人这么简单。方隐仙把尖刀插在腰间,走到台沿,浏目着空地上那参差不齐战战兢兢的茶户。
“若神明真的认为胡神师有着八十七岁寿命,怎可能被我一刀杀了?他一直来都在欺骗大伙!胡神师并非神明的使者!昨天本里正在山里得到神明旨意,此人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必须就地正法。”
方隐仙那朗朗的少年嗓音响在祠堂上空。
“今后无论有何病痛,均可上本里正处,由本里正替大伙医治。”
惊慌失措的茶户听到这话终于缓过神来,各各舒了一口气,原来里正爷才是真正的神师啊。
诸茶户开始交头接耳,但莫不喜形于色,里正爷是神师本是传统,但已经数十年没在乡里出现了,上天与神明没有抛弃他们。
“还有一事,南坡上的竹米各家各户不得私采,东溪由六爷做头,西溪由王二伯做头,所有采到竹米均交到祠堂,再由六爷与王二伯平均分配。灾年饥荒,大伙共进同退,不能藏私,有私采者,绝不容情!”
自昨晚开始茶户们已经开始上山疯割竹米,此时各人不敢出声,方隐仙一举手便杀了胡神师,这威慑力不容小觑。
“具体每户每丁多少口粮,由本里正与六爷王二伯定夺。无事,大伙回吧。”
茶户们三三两两在祠堂前散了。
胡神师是东川过来的外来户,在太平溪没有家室。方隐仙招呼王二伯及六爷,商量着如何帮他把后事给办了。
半晌后已经有着积极的茶户背着竹筐来上檄竹米,方隐仙让六爷与王二伯用斗量登记竹米数量,由他带着王家三兄弟把胡神师的后事给办了。
夷陵一带的丧事非常简单,无需棺椁,入水为葬。
王大郎三兄弟从胡神师家里拆来门板,抬着胡神师,由方隐仙带着,在长江旁把胡神师的尸体送入滔滔江水里。
方隐仙回到祠堂里时,各家各户开始把昨晚至今采到的竹花及竹米交到了祠堂,王二伯一斗一斗算着数量,六爷执着毛笔一划一划的登记着。
六爷不识字,但也登记得煞有其事极其认真。
就算不识字,算计加减分配也绝不是难事,只是比较费纸。
方隐仙嘱附六爷在登记完毕后,计算出总数,再按每丁口最低口粮分配,每丁户每日到祠堂来领竹米,包括方隐仙自己。
方隐仙这么一说,六爷与王二伯这才体会出上檄登记竹米的深意,心里对里正爷更是钦敬如滔滔江水。
方隐仙看着在祠堂左停里已经堆成小山的竹米,心里想着今后的生计,今年初春种下的旱稻颗料无收,东溪所有渔船均被归州刺史张瑭手下军吏扣下,民间不得捕鱼。
若不如此也不会闹得昨天想把孩子拿来果腹。
南坡上的竹米被各家各户一天间一轮抢割,已经荡然无存,此时上檄回来的竹米,实在支撑不了太平溪数百丁口一月时间。
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到夷陵峡州交易粮草。此时正是战时啊。手里这一年里收到的茶砖,能换多少口粮呢?
方隐仙站在竹米前发着怔,绿茗默然站在他身旁,不停瞅向方隐仙中午执刀杀胡神师的那只手。
“东家。”绿茗探试摸了一下方隐仙的那只手,又缩了回来。
“嗯?”方隐仙正在粮食危机的烦恼中,随口应着。
“神明就是祖师爷吗?”绿茗又摸了一下方隐仙的那只手。
“是。神明就是祖师爷。”
绿茗又想来摸,方隐仙反手握住她的小手。
“走,咱回家吧。”
方隐仙想起自己怀里的那本医书,心里升起一线希望。
黄昏,方隐仙搬了竹椅坐在篱院,双脚泡在水盆里,翻看着辛七娘留下的那本医书。
一册医书全是白纸,方隐仙傻眼了。推敲着这白纸医书到底有什么窍门。
绿茗坐在方隐仙身旁,双脚也泡在井水里,轻声哼着采茶曲。
两人都喝完了一碗竹米粥,在篱院里等着太阳落山,等着星夜来临。
“东家,你讲故事,绿茗想听小倩和宁采臣的故事。”绿茗望天空望得无聊,开始缠着方隐仙要讲故事。
“今天不讲故事,来,让我帮好茗儿把把脉,可别明天有人找上门都不知道怎么办。”方隐仙想起今天在太平溪诸茶户面前夸下的海口就愁得不行,辛七娘真是把他给坑苦了。
方隐仙抓过绿茗的小手,放在自己大腿上,两只手指煞有其事搭在手腕的通里脉上,装起神医来。
绿茗怔怔望着在自己面前嘻皮笑脸完全放松的东家,心里深处像是被什么动了一下般,又想笑又想哭,被东家抓着手掌,居然欣喜得心里堵得发慌,想大笑或大哭来发泄一下。自东家昨天早上下山来,这种感觉就一直不停在心里出现着。
方隐仙不知眼前这名与他相濡以沫的少女已动了春心,手指搭上绿茗手腕通里脉时,却被脑里出现的事物吓呆了。
当方隐仙手指搭上绿茗手腕通里脉,只觉得自己的意识随着脉膊的跳动,缓缓游入绿茗体内。
体里每一道经脉,肉身所有组织的运转,在方隐仙脑里慢慢呈现,清晰无比,那种在脑里既实又虚的影像,无法以言语传喻。
方隐仙意识在绿茗体内经脉器官运转一周只需一个弹指的时间,但这个时间里却已经把绿茗身上所有的小病小疼完全了解得一清二楚。
方隐仙抽回手指时,心里的激动难以形容,抱过绿茗狠狠亲了一口,哈哈大笑:“好茗儿,好茗儿!”
笑着翻开手里一直拿着当扇用的野狐医书,果然白纸上显出字迹:长期受饥,胃气不调,宜多吃油腻肉类或鱼汤。
原来只需把书拿在手里,再帮别人把脉,书上自动会显出病症及最佳治疗方法。
果然是宝书啊。这下在这个乱世里有了行走江湖的资本了。方隐仙乐开了怀。
方隐仙把医书塞到绿茗手里:“来,茗儿你帮我把把脉,看看我有什么病。”
绿茗脸上红晕绯绯,心跳快得不能自仰,手指被方隐仙拉着搭在他的脉门上,却只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东家,我哪里会把脉啊。”绿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欣喜激烈的感觉,心乱如麻。
“咦,你感觉不到我的经脉?”方隐仙大奇,拿过绿茗手里的医书,此时又变成了一册白纸,什么也看不到。
难道只有我一人才能用这医书?方隐仙心里产起一丝遗憾,自己有病还得找别人看,一想起这个气势就挫了几分。
——————————————————————
票啊票啊。。。。。您的票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步,是推动神州七号的燃料,是兰兰面前的摄像机,是希希手里的摄影机……伟大的票啊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