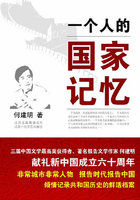寻找鬼师
何莉父亲当天中午就赶到了清海市,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见到了徐庆娣。
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虽然头发已灰白,眼角也有细细的皱纹,但身板依然笔挺高挑,,面容和何莉非常象,一样的高鼻梁,一样的浓眉大眼,但放在一个男人脸上,就更具有阳刚气,看上去风度翩翩气质高雅。
徐庆娣从没见过何莉的父亲,但却无数次听过何莉对自己父亲的描述,因此心里对这个男人很是不齿。
如果不是先入为主起了作用,仅凭第一印象她肯定会非常欣赏这个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具有迷人风度的老男人。
但现在她只是淡淡地叫了一声:“何伯伯来了。”连寒喧都没有一句就直接切入主题:“何莉现在昏迷不醒,上午做了脑CT和脑电图,医生说除了脑电波有些混乱外其它都没有什么异常,脑外科医生也说她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外力击打的痕迹,因此她的昏迷更可能的是受到了极度的刺激引起的……”
“受了极度剌激?她遇到了什么?”何父打断了徐庆娣的话,焦急地问道。
徐庆娣对他打断自己很是不高兴,但看到他脸上为何莉露出来的担忧不象是假的,就没有计较,继续说:“我想……这可能和前段时间她遇到的事有关……”
“什么事?她失恋了?”何父又追问道。
徐庆娣白了他一眼,心想,这个白痴,从何莉小时起就不大和她联系,父女二人形同陌路,现在女儿出事了,他猜到的原因就只有这种事么?
“不会!”徐庆娣断然说。“我和何莉情同姐妹,她的事我全都知道,据我所知,她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什么?小莉她二十七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何父吃惊地问。
徐庆娣又给了他一个白眼,你女儿这么大了没男朋友是很严重的事吗?姑奶奶我也二十七岁了也没男朋友好不好?不过,何莉不肯找对象还不是拜你所赐?如果你这个父亲称职一点她怎么会对男人有那么偏执的看法?她没有接何父的话,接着说:
“四个月前何莉值夜班时一个孕妇死了,那个生下来的小孩后来也死了,因为此事何莉受到了医院的处分,后来,何莉就辞职离开了这个医院……”
“什么,小莉辞职了?她难道不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何父更吃惊了,不由自主地放大了声音,使得不少路过的人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徐庆娣终于忍无可忍,恶恨恨地瞪着何父喝道:“闭嘴!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这真是一个大白痴!怪不得何莉说起这个父亲时从来没用过敬语。徐庆娣有些后悔通知这个人了,本来想和他商量一下何莉的事接下来该怎么办,谁知这人缠七搞八拎不清,反而使她在昨晚想了一夜的措词都忘了,真是个添乱的家伙!
这人是何莉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现在何莉出了事,不通知他怎么行?万一何莉再也醒不过,她徐庆娣可挑不起这个担子啊!
徐庆娣想到这里眼睛就湿润了。
何莉,你可千万要挺住啊!
何父受了徐庆娣的喝斥脸上不由汕汕的,低下头不说话了。
看到何父这般小媳妇受了气的委屈模样徐庆娣忽然觉得拳头痒痒的,有一种把他胖揍一顿的冲动。
“……大前天,这医院的产科又发生了一次孕妇死亡事件,这次也是连胎儿都死了。何莉觉得这次和她上次遇到的那一次是有关系的,她的直觉认为这件事和她有关,所以她想查出真相,但不知为什么,昨夜她从医院看望一位同事出来后竟然进了停尸房……”徐庆娣停了下,怕何父再次惊叫打断她。还好,何父只是默默地低头听着,不知是不是因为受到徐庆娣的喝斥觉得伤了面子还是被徐庆娣的叙述给震惊了。
“不知道她是想在那位死去孕妇身上找到答案还是被某种不知名的东西引到那里去的?总之,等到停尸房的工人发现时何莉就昏迷不醒,谁也不知道她昨晚在停尸房倒底遇到了什么,更蹊跷的是,那位孕妇的母亲同一时间居然在停尸房里莫名其妙地倒地死了。”
何父突然抬起头来望向徐庆娣,眼里忽然有一种凌利的光芒闪动了一下。
徐庆娣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个拎不清的老男人也有这样凌利的目光。但再细看,那目光已攸然不见,何父仍然是那副蔫蔫的样子。
徐庆娣暗笑自己,大半夜没睡,人有些恍惚,连眼都有些花了。
“何莉曾和我说过,想要寻找一个和能鬼通话的鬼师。我听我妈说过,在她老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我本来和何莉约好只要她定下时间,我就让我妈陪她走一趟,但现在何莉成了这个样子,肯定是去不了了,所以……”
“我也不行,我的单位里请不出假的……”不等徐庆娣说完何父又急急说道,唯恐徐庆娣说出让他去的话来。
徐庆娣心里那个气啊,你说这叫什么父亲?二十多年对女儿不闻不问的,现在女儿昏迷不醒生死不知他竟然还在强调自己的工作很忙。徐庆娣的拳头又痒了起来。
“没人要你去!”徐庆娣用了好大的劲才压制住了心里的怒气,“我会找人一起去找那个鬼师,但何莉这里离不了人,医生可能随时会有事找家属商量,因此,你留在这里看着点,等我们回来,听明白了没有?”徐庆娣一口气把话说完,最后的语气不容置疑,说完她的拳头已攥得紧紧的,如果这个男人还不答应或是有些犹豫,她就毫不犹豫地将拳头挥向他的面门。她可不管这人是不是个长辈。她实在是太生气了!
“那……好吧。我打电话去请假。”何父似乎觉察到了徐庆娣的愤怒,不敢再有异议,沉吟一下后答应下来。
徐庆娣松了口气,松开已有些缺血的指关节。
“不过……”何父又迟迟艾艾地说。
“不过什么?你说话一下子全说完行不行?别那么娘!”徐庆娣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倒好象对方是她的小辈。
“是这样的,我的单位请假只能请三天,所以你们最好是能在三天里回来,多了恐怕有麻烦。”这次何父说得很麻利。说完还眼巴巴地看着她,生怕这个要求会被驳回。
徐庆娣有气无力地白了他一眼,对这个男人,她已经连揍他都提不起心来了。当年何莉的母亲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徒有其表的男人呢?
看到徐庆娣点头,何父明显松了口气,在将头转向一侧时,眼中又闪过一道目芒,这被徐庆娣捕捉到了,她心里不由一动:难道这个男人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
*********************************************************************
第二天,浙南武宁县的公交车站,一辆长途汽车到站,从车上下来三个人,老中轻一男二女。
那个男人四十岁左右,隆鼻宽额,粗黑的眉毛,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高个子,头上扣一顶烟灰色全毛绒线帽,帽边翻下护住了两只耳朵;上身穿着烟灰色长及膝盖的呢大衣,下身是一条藏青色毛料裤,前面两条折痕笔笔挺;脚上一双沾满了灰尘的皮鞋,一下车,他就从大衣袋里掏出一块餐巾纸来仔细地擦拭着皮鞋。
中年女人细眉团脸,脸色红润,双眼皮大眼睛,眼角有细细的皱纹,上身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下身是一条黑色的弹力化纤裤,将两条腿包裹得圆润丰硕;脚上是一双白色旅游鞋,没有戴帽子,一头黑黑的短烫发被风一吹有些凌乱,下车后她就一直用手在理烫发,试图将它们理回原来的样子。
年轻的是个姑娘,肤色细腻白皙,高鼻梁大眼睛,鹅蛋脸上一抹红晕,好象搽了胭脂,更显娇艳清丽;上身是宝蓝色短棉袄,下身是蓝色牛仔裤,将一双修长浑圆的玉腿包裹得韵味十足,脚上着一双天蓝色皮面软底雪地靴,一头乌油油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马尾,走起路来弹性十足,全身的每个细胞似乎都在往外冒着青春活力。
年轻姑娘自然就是徐庆娣,中年的那个女人是她妈妈。
而那个中年男人,是四天前来清海市为顾丽华会诊过的那位省妇保专家宓教授。
宓教授全名宓成功,上海人,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八七届毕业生,是省妇保知名产科急诊专家。
省妇保的产科是省内技术力量最强最过硬的,因为它拥有一支闻名全省乃至周边省市的急救队伍,而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就是宓成功。
四天前的深夜,宓成功被电话从暖呼呼的被窝里拖出来然后被紧急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清海市急会诊。上路前他并没有太在意,这种会诊他已经历过无数次,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抢救成功。
不就是个前置胎盘吗?只要下级医院能及时把血止住拖到他赶到就行了。所以应该没有大问题,大不了把**一切把命保住就一切OK了!所以一路上他并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基本上睡了一路。
到了清海医院之后他赶到产房一看,孕妇的流血已止住,两个全血也输进去了,生命体症基本正常,心里就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就提议剖宫取胎,只要孕妇体内的妊娠物取出,没有了出血源,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孕妇竟然死了,而且是以那么诡异的方法死在了产台上!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在剖开腹壁后**上怎么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裂口?打了硬脊膜外麻醉的孕妇怎么能坐得起来?最关健的是,那位孕妇怀胎八个月了怎么硬得起心肠将胎儿扔了?
事后回想起来,在孕妇坐起来前他似乎看到一团黑雾从他右侧悄然飘到他左侧,在飘过麻醉架后就消散了。当时他以为是有谁在手术室偷偷吸烟,加上当时情况紧急也无暇多想,接着,惨剧就发生了……一切发生得迅速、混乱和荒诞不经,让他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就已经铸成了。当时那个生命明明是可以救得回来的,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自己面前被一种无名的力量强行带走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他很是愤怒,但又不知道这种愤怒该向谁发泄。也许结果早在他来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宓成功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不把一件事弄个明明白白他是不会罢休的。回去后他对整件事仔细梳理了一下,然后在昨天下午他给清海市医院产科打电话,本意是想了解一下那晚在场的一共有几个人,他想询问一下这些人中有谁看到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科主任向他提供了一份名单。王义妹是名单上的第三位。
通过王义妹,宓成功知道了何莉,也知道了发生在何莉身上的事,然后就联系到了徐庆娣,知道第二天她就要和她母亲一起去武宁县寻找鬼师。
宓成功立刻决定同行。昨晚他处理好一个危重产妇后连夜从省城驱车来到清海市,只在宾馆休息了三个小时就和徐庆娣她们一起出发了。
徐庆娣的妈妈是畲族人,姓盘叫玉兰。特殊时期初期,徐庆娣的父亲徐念风下乡插队在抬头就见山的武宁县,到了县里又弯弯拐拐走了大半天的盘肠道才到了被大山包围的盘家寨,到了盘山寨又被通知知青点还没造好,只能暂住在村民家里。就这样他被分到了盘玉兰的家。
徐念风的祖父解放前曾当过私塾先生,家里遗留了许多黄旧的老书,特殊时期时给红卫兵小将们烧了大半,余下的一小部份他父亲偷偷藏了起来。大串连时徐念风的父亲怕这独生儿子会在这动荡年月死在外面,所以死活不准他随同学一起步行去井冈山,无奈,徐念风留了下来,每天无所事事,翻看这些老书,什么《论语》、《诗经》、唐诗宋词,加上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书和报纸,全都看了个遍,真个有些博览群书的味道,到下乡时,他肚子里已装满了之乎者也、时事新闻和世界各地奇闻逸事。临下乡前,父亲再三关照他说话千万要小心,别将老书里的词漏出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他当时答应了。但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忌纬?时间一久就把父亲的嘱咐忘到了爪哇国里。
下乡住进盘玉兰家里后,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无事时他就和盘家人聊大天,说到兴起就会来上一句:“子曰……”“鲁迅先生说……”这让不识几个大字的盘父盘母非常欣赏。
盘玉兰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对她非常宠爱。当年十八岁的盘玉兰正是少女怀春时节,对这个来自山外的年轻人懂得那么多很是钦佩,因此只要有空就缠着他讲故事,一来二去的两个年轻人就有了那么点意思。
但是盘玉兰的父亲盘老汉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他虽然欣赏徐念风知识渊博,但要他把女儿嫁给一个外地人,他就不干了。他反对的理由是徐念风是汉族人,是个城里人,没有根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盘龙寨。
最后对徐念风下了驱逐令。
徐念风无奈让队长给他另外按排了人家搬了出去。人虽然分开了,但两个年轻人的心并没有离开,盘玉兰还是瞒着父母偷偷和徐念风私会,时日久了,村里渐渐有了风言风语,盘玉兰的父亲盛怒之下提着一根碗口粗的棍子追着徐念风就打,一直把徐念风打出了村子,回头又把盘玉兰送到了十里山路外的姑妈家,希望由此能斩断这根孽缘。
爱情的力量有时大得让人无法想象。一个月以后,徐念风养好了棍伤,就悄然失踪了,在知青点他的屋子里除了随身换洗的衣服外什么都没有拿走。开始其它两个知青还以为他去什么地方玩了,以往他也时有无故失踪的时候,过后就自个回来了,说是去山里转了转,这是常有的事,所以这次谁也没有往别处想。
但徐念风一直没回来。
一周后盘家姑姑心急火燎地赶来,说盘玉兰找不到了。原来就在徐念风失踪的同一天,盘玉兰对姑姑说要去镇上赶集散散心。盘家姑姑想来想去没找到拒绝的由头,再说盘玉兰在这里一直很老实,从不出大门一步,再闷下去也会把人闷坏,就同意了。为保险起见她还亲自跟着去了集上。谁知那天是个大集,集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挤成一团,她拚命抓紧了盘玉兰的衣服,但在十字路口,一阵人流拥来,硬是挤脱了她的手,盘玉兰就这样消失在了人堆里再也找不到了。七天来盘姑姑找遍了附近所有大小材庄,问了无数的人,连个人影也没找到,没奈何只好赶来盘家寨向哥哥报信负荆请罪。
盘父一听,和知青点里徐念风的失踪联系起来一琢磨,心里顿时全明白了:好你个徐念风,你竟敢唆使盘家寨的姑娘私奔!老头子当场暴走,冲到知青点将徐念风留下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气疯了的盘老头甚至还想一把火把知青点烧了,后来还是队长和几个壮汉上去把他制伏,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徐念风和盘玉兰失踪后四年,插队的知青开始陆续回城。此时盘老汉的观念早已发生了改变,对当年反对女儿婚事的做法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已有后悔,但四年来这两个年轻人音讯毫无生死不知,如果活着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想到女儿可能被他逼死,盘老汉心里就不是滋味,好几次乘赶集的机会偷偷地向人打听过,但是一直没有下落。此事就搁了下来。
盘玉兰和徐念风的下落也成了盘老汉的一个心病。
十年后,就在1982年的夏天,其时改革开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盘山寨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回来,说是在北方的清海市看到了徐念风和盘玉兰,当时他们正在街上逛店,两人还牵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此时盘母因思女成疾早已去世,盘父也绪病缠身,不能下地干活了。他自忖时日无多,想见女儿一面,但他也不知道那个清海市在哪个方向。当时大队部里有张全国地图,他特意去了一趟大队部,央求老会计帮他寻找清海,老会计戴上老花镜在那张图上划拉了好半天才在左侧的海岸线上找到一个小黑点,指着说,就是这里了!盘老汉凑过去一看,那里离海很近,用手指量了了量,离武宁县挺远的。他咂了咂嘴,怪不得当年他在周边县村都跑遍了也没找到他们,敢情这两孩子跑到这个边旮旯去了?呵呵,这徐念风不亏念了那么多书,真是好心计啊!
可是毕竟清海市离景宁太远了,带回消息来的那人也说不清盘玉兰他们的确切地址,因此盘老汉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