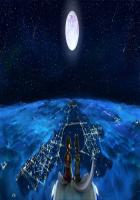“是吗,父亲要安排我去演武厅?”
“是的,五公子,老爷昨晚特意交代老朽,所以老朽一大早就赶来了,生怕耽搁了时辰,误了事。”牧府的老管家一大早便来到无竹阁,叩开了张小奇的门。
演武厅是张家习武之地,武学典籍,枪戟棍棒,无一不全,更有江湖高手被奉为府邸客卿,邀请其来授武教拳。但凡有一定修炼天赋的张氏子弟,无不渴望进入其中,既可以享用整个家族供给的资源,更可以在这方小小的天地得到几丝不为言说的虚荣。
无论你是正支还是旁支,在这里,我们都是学生,都是平等的。
无论你是庶出还是谪出,在这里,我们都是学生,都是平等的。
只要我修炼比你快,我就比你强。
不管你在外面如何呼风唤雨,在这里,你都比不上我。
大抵来说,若是修为过了练力境,得了“勇士”称号的,便算作出师,学业有成了。若还有天赋,过了抗膜境的,那便会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往军中历练。
所以一般修为过了抗膜境,便不会再呆在演武厅,更多的是讲究自我的修炼,或者去往圣地求学,比如学院。
似是察觉到张小奇的疑惑,老管家继续说道:“公子也许会觉得奇怪,不过这次不同以往,乃是为公子安排的一次特训。”
“特训?”
“是的,公子要参加学院考试,事关张家颜面,不可谓不重大。参加今年的弱冠之试亦是同样的道理,这也是关乎张家颜面的大事。老爷虽然给公子出了难题,不过老朽却是明晓老爷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说实在话,他的心底还是记挂着五公子的,不然也不会特别交代让你去演武厅。”
“原来父亲是这般良苦用心!”痛心疾首的张小奇拂袖掩面,头深深的低了下去,他的肩旁耸了耸,似是在垂泪抽泣。只有站立在他身后的阿呆能清楚的看到,自家的公子正就着茶杯里的茶渍往眼角下沿辛苦的抹了几把,一抬头便是一汪深情的眼眶,比戏台里的哭女子都要让人动容,他的衣襟之上有些湿。
确实湿了,茶水溅了出来。这种活计,张小奇毕竟还不甚熟络,一时之下,自然有些手忙脚乱,如今看起来效果好像还不错,有时候拙劣的表演并不一定就比圆滑老到来的差。
“既然如此,我稍后便去,绝不辜负父亲的苦心。”张小奇努力让自己的眉头蹙到一起,好使这番励志的话配上决绝的眼神更显几分真诚。
听完这番话,老管家却像个杵子,立在那里,没有告辞的意思。
顷刻间,像堆乱石挤到一起的眉头顷刻间更挤了,张小奇再问道:“老管家还有事吩咐?”
“吩咐不敢,只是老爷昨晚特意交代,要老朽一定陪公子去演武厅,以后每个上午,老朽都会来一次。”
“公子不要多想,这绝不是老爷想监视公子,都知道你之前懒散惯了的,虽说你有决心,不过年轻人好玩,难免有懈怠,老朽每日来一来,也起个督促,这也是为公子后面比试着想。”
“是吗,劳烦父亲挂心,劳烦老管家费力了。”
“不敢,为张家跑腿就是我应该做的。”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演武厅不在州牧府,设在城东,离府邸大约四五里。
张小奇坐在马车里,缓缓的向城东驶去。老管家决计不肯上车,坚持主仆有别,一板一眼像极了张翦,以至于有个外号,被人戏称为“营州牧的影子”。
一上车,张小奇便对同坐在马车里的阿呆问道:“你怎么看?”
上车后便紧急进入打盹状态的阿呆听到有人问话,立刻醒了过来,“啊,什么?”
张小奇把脸一沉,仔细瞧了瞧自己这个呆书童的黑眼圈,不由想起最近的传闻,说花满楼的对岸,多了位痴儿。
听说那桥溪柳畔之间,夜幕漆影之下,有个少年常常驻首观望,有好事者想看看是哪位发春的小子,结果往往抢先一步,被他溜走,月影之下,只剩下一个大头的背影。
念及此,张小奇嘿嘿一笑,问道:“阿呆,你最近干吗去了?”
阿呆耸了耸眼皮,“最近听闻公子修炼心得,大有所悟,故而修炼得有些废寝忘食,颠倒了作息,我可没偷懒。”
“是吗?”张小奇故作疑问,“我听说最近木兰街那边经常有个骚年去观望,有管事讲,那个骚年好大的一个头啊。”
阿呆本来还有些不甚清醒的脑袋瓜子,如同被人提着脖子侵了下凉水,一下子醒得不能再醒,“公子啊,如此朗朗乾坤,谈论神马骚年实在对不起苍穹老爷,咱们还是谈点正事吧。”
“什么正事?”
“老爷此次的安排,无非是不想你出现在弱冠之试上而已,虽然老爷同意你去学院,但终究到底,你还是坏了他的规矩,他的心底怎么也是不放心的,自然不会就这么等着你出现在弱冠之试上。公子也清楚,所谓家族荣耀都只是个借口,是阻你去学院的借口,如今又成为让你去演武厅的理由。”
“去演武厅自然不会是为你着想,所以这里面必然会有阴谋,也许会发生些不好的事情,你也知道可能会发生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为了保证你去,而且每日都去,便需要有双眼睛看着你。”
张小奇微微有些吃惊,不成想到自己这个迷糊的书童居然早就看透今日老管家的惺惺作态,思考于他本是件痛苦的事情,但看其今日表现,娓娓道来,倒也不嫌疲累。张小奇方才明悟,这哪里是痛苦,这分明是想偷懒装出来的!
若不是今日趁其模糊之间,挑了阿呆的心事,一时情急,自己这个呆书童想转移话题,只怕自己还看不清此人的真面目。想及此,张小奇微微叹了口气,“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貌相...”他的心底反复念叨道。
“不过,还是个呆子。”他在心底又补了一句。
张小奇叹了口气,带了些幽幽的口吻,说道:“就算我知道又怎样,还不是一样得听这些个假仁假义,实力不够,就得听人摆布,就要在别人的规矩下过活,这世间天道秩序,莫不如此。”
既来之,则安之。如今这种局面也只能相机行事,见招拆招了。
似是考虑这些事情有些烦人,张小奇又盯了盯阿呆,眼珠转了转,问道:“阿呆?”
“嗯?”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偷看媚儿姐姐去了?”
“额,公子,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谈谈以后如何才是正事。”
“我们还是先谈谈你每晚是如何度过这慢慢长夜的吧...”
......
......
演武厅。
作为宗族里天赋子弟修炼之处,历来便受到家族重视,张小奇曾经作为其中的骄子,大多数的欢乐与骄傲都洒在了其中,如今故地重游,心底自有一番感概唏嘘。只是故地尚好,昔友已不在。
三年前与他一起来此修炼的子弟们,有的或已从军从政,有的或求学远方,更多的,已被家族安排了一生,打算安稳的做个普通人。演武厅如一座城,始终来来往往,无论谁,在其中都只是个过客。
张小奇的到来让一些子弟有些诧异,但也仅仅是惊愕片刻,然后纷纷各顾各的,没有小说话本里的嘲讽奚落,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实力火候,无论怎样掂量,他们都自叹不如,自然也招惹不起,既然如此,还是安分守己的好。
“雍先生!”
刚入厅不久,老管家便先行了一步,向厅堂里坐着的一人施了一礼。
“原来是大管家。”正坐着品味一种叫做“三江寒”的上好名茶的中年人拿眼睛瞟了一眼,又打量了下立在一旁的张小奇,有一点倒三角的双眼眯了一下,干咳了两声,“这位就是五公子吧。”
“正是五公子。”
“公子,这位雍先生便是老爷特意给你安排的教练,二位既已见过面,也就没老朽什么事了,公子,望你勤奋修行,老朽明日再来。”
说完,老管家便出了演武厅,剩了张小奇与雍先生二人大眼瞪小眼。阿呆在一旁,安静的打着酱油。
张小奇瞧了瞧这位雍先生,脑海里却是忆不起演武厅的教练里有这位雍先生。
要担当教练,必须经过修为考校,还要查他的底细,背景,毕竟是为人师,一切都马虎不得。再看刚才其他人对这位雍先生未有过多关注,张小奇大致猜测多半是临时为自己而特请的一位教练,果然是用心良苦。
再看了看放在桌边的“三江寒”,这种只有扬州才产的上好名茶,张小奇心底大概有了些底,只怕这件事与王夫人丝丝缕缕间也有些关联。
“跟我来!”
雍先生的一句呼喝打断了张小奇的思绪,急忙跟了过去,不出百步,疾至了一片空旷之地,整齐的布置着一排排整齐的木桩,却是演武厅的武校场。
视野刚刚扫了一眼,突然便有一只硕大的拳头,直袭张小奇的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