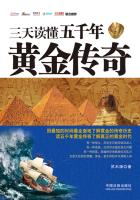卫玠将《射雕》后半部的书稿交给了郝秀才。据说有不少买了半部书的回头客催着周掌柜要下半部。周掌柜自然是高兴的很,便让郝秀才顺道来取书稿,他好抓紧时间开工刊刻。
将郝秀才送出了门,卫玠便打算回房间抓紧写书,若是每月都能有十多两银子的收入,那一年不就有百来两,这可不是小数目,不仅能让卫家的生活宽裕些,说不得还能投资些小生意。
正憧憬着美好未来呢,却见莲衣妹妹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宝哥哥,宝哥哥你快去救救我哥,他被人抓到衙门里去啦!”
卫玠闻言一愣,“你说清楚,怎么回事?”
“我,我也不晓得,就见一帮人冲进清芳院,说我们院里有贼,然后……然后就把我哥给抓走啦!”莲衣急得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哎呦,这可要出大事!”那卫老酒方出了房门,听到莲衣所言也是一阵紧张。
他倒醒得真是时候!卫玠看着急慌慌的两人,反是冷静了下来,问道:“这是多久前的事情?”
“就,就方才。”
“走!”卫玠思忖片刻,提步便往外走去。
卫老酒傻站在院里,不明所以,忙问道:“臭小子,你这没头没脑的要去哪儿啊?!”
莲衣紧跟在卫玠身后亦是满脸疑惑,只听卫玠言简意赅道:
“清芳院!”
上元县县衙大堂内,陆知县哈欠连天的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马典史亲自端了杯浓茶上来,好让陆知县提提神;李主簿则拿出一大摞状纸放在了陆知县面前的大案上。
陆知县看到状纸就皱眉,“怎得这么多?”
“这几日又是中秋又是乡试的,人多了事自然也多,这是几日来攒下的。”李主簿回道。
陆知县喝了茶精神稍好了些,待看到这头张状子上的名姓,眉头又皱了起来,“怎得又是这田圭,他把县衙当家了不成,天天往这儿跑!”
“大人莫恼,这田圭本就是个讼师,打官司不往衙门来却要往哪儿去?”马典史赔笑道。
“什么讼师,我看他就是个讼棍!”陆知县语带不满道,“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往状上写,还嫌衙门里事情不够多?以后若再没事找事,信不信本官发配他去充军!”
“哎,大人您且息怒!”马典史道,“听说这回是真有事,状上写了,说是被人偷了财物,那小贼被抓了还不认账,这不是没办法才告到大老爷您这儿了!”
“马典史,你最近是不是手头又紧了?”陆知县斜眼看那马典史。
马典史尴尬一笑,道:“哪儿能啊,大人你可别冤枉我,我这是就事论事。”
陆知县心里清楚,这马典史怕是收了那个田圭的好处,才这般帮腔,他却不想给这班奸猾小吏当枪使,“不过是个偷儿,哪里需要这般兴师动众。人家争家产、抢地皮、欺行霸市的案子,哪个不比他重要?”
“是是是,您说得是。”马典史连连点头应和,生怕陆知县当真追究。
陆知县敲打了马典史一番便打算翻看下一张状纸,站在一旁的李主簿却突然出声道:
“大人,我看您还是受了田圭的案子,免得以后麻烦!”
“什么意思?”
李主簿道:“大人,您有所不知,这田圭虽说只是个无赖讼棍,却有个不得了的亲戚……”
陆知县闻言冷冷一笑,打断他道:“这金陵城里什么皇亲贵胄达官显贵是本官没见过的?你何时见过本官为这些个怕过事徇过私?”
“大人您自然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只是如今这世道,小人当权,国是日非,属下不是怕您吃亏嘛!”李主簿煞有介事道。
闻得此言,陆知县轻咳一声,问道:“到底什么人?”
“这田圭有个同族兄弟,名唤田吉的,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如今在兵部任事。”
“南京兵部?”
“哪儿啊,南京的兵部哪里还有什么要紧的人,自然是京城的兵部。据说他在京师混得是如鱼得水,颇为得意。”
“这田圭与田吉……”
“那是同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李主簿道,“据说这不学无术的田圭能成为国子监监生,还是那田吉帮得忙!”
陆知县闻言不禁沉吟起来,片刻后,他道:“本官是一县父母,不能坐视这等有碍教化的偷窃之事横行,且让他进来吧!”
衙役们三三俩俩的开始站班,无精打采的喊着‘威武’。
打衙门外走来一男子,一身绣金线绲银丝的长衫很是扎眼。至近前,却见这男子约莫三十有余,脑门上一块青色胎记很是醒目。
“学生田圭,叩见大人!”弯腰作揖,恭敬有礼。
陆知县见他如此,面色稍缓,道:“田生上堂,所为何事啊?”
“大人啊,您治下原本是海晏河清,奈何却有那偷奸耍滑之徒为大人脸上抹黑啊!”田圭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道。
“少给本官装腔作势,有事说事!”
“学生昨日被人偷了一身衣衫还盗走了五十两银子,今日学生抓到了那盗窃的小贼,他却是死活不认。”田圭苦着脸道,“学生原本也不愿拿这等小事给大人添麻烦,可这小贼忒是奸猾,学生奈何不得他,只得叨扰大人了。还望大人替学生做主!”
却说这田圭进门时身后还跟着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两人左右夹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少年。待入了大堂,二人便将那神色慌张的少年一把扔在了堂上。
那少年自然是傅辰。因是在官府县衙大堂之上,左右又有那如狼似虎的衙役,傅辰哪里见过这阵仗,心中极是害怕,哆哆嗦嗦的跪在堂下不敢出声。此时,他听到田圭的诬陷之词,心中气愤,终是鼓起勇气为自己辩驳道:
“我何时偷了你五十两银子?!你,你这是胡说八道!”
“哎呀大人,你看看这贼奴,便是在大人面前还敢这么嚣张!”
这田圭原是个破落户家的子弟,打小不学好,专门在市井中厮混,什么三教九流都认识一些,后来还与那县里的衙役皂隶混了个脸熟。因他伶牙俐齿,头脑灵活,又懂些律法,会写状词,便借着这些关系做起了讼师,专为豪富劣绅打官司,从中获利。也时常教唆他人无事生非,闹出些有的没的,坑骗他人钱财。这么些年下来,他倒是挣下了不少的身家。
陆知县也知道这田圭是什么货色,并不听他挑唆,但对小偷小摸之徒也无甚好感。他皱眉看了那傅辰一眼,而后与田圭道:“你且详细说说。”
“是,大人。”
田圭开始叙述道:
“昨日我在清芳院喝醉了酒,便躺在了那珍姐儿屋里。到夜里我醒过来时发现有人动了我的衣裳鞋子,问珍姐儿,她说自己在外边迎客并不知情。后来我也就没在意,便回家去了。没成想到了家里,却发现自己袖袋里的五十两银子竟不见了。这来来回回寻了一圈却是没有。今日早晨,我便去清芳院找,却听人说,这小奴昨日趁四下无人进过我的房间!”
“大人,若是小娘进我屋里也算是正常,可这小子进来,揣得是什么心思,还不明显么?”
陆知县听这田圭说得头头是道已是信了几分,便问那傅辰道:“你还有何话可说?”
傅辰急得眼圈发红,大声道:“大人,大人您相信我,我没有偷他的钱!”
“没偷?”田圭冷笑道,“我且问你,你昨日是不是进过珍姐儿的房间,是不是动过我的衣裳?”
“我……”傅辰红着脸,一时竟答不上来。
“大人,他无话可说了,这分明是做贼心虚!”田圭道,“还请大人明鉴!”
陆知县立时眉头大皱,怒斥傅辰道:
“小小年纪不学好,竟学那贼奴偷盗,本官便替你爹娘好好教教你,何谓‘温良恭俭’。先拉下去打他十大板,以示惩戒!”
衙役们不由分说上前拽起傅辰便往外拖,那傅辰吓得脸儿惨白、泪儿直流,疾呼,“大,大人……我冤枉……”
陆知县哪里会听他分解,挥挥手便让衙役们赶紧打完了事,好让他审下个案子。
却在这时,打衙门外传来一通鼓声,继而守门的皂隶让进来一少年郎。只见他俊眉秀目,气度不俗,往大堂上一站,顿时让人眼前一亮。
“大人,草民卫玠,有冤情上呈!”
——————
好戏要开始啦~~~亲们记得收藏、推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