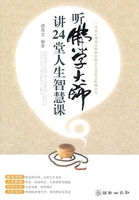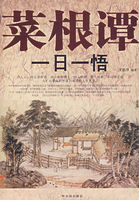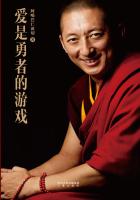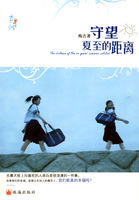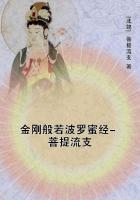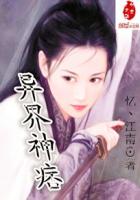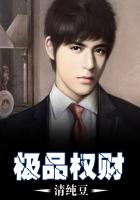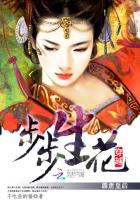付嘱者,授以法,嘱其传持也。《金刚经》:“如来善付嘱诸菩萨。”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1]。吾灭度后[2],各为一方师[3]。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4]。
[1]常随侍使之众,故云不同余人。又其入道比余人为胜,故云不同余人。
[2]灭度,兼命终证果二者而言。《涅槃经》十九:“灭生死故,名为灭度。”《行愿品钞》四:“言涅槃者,具云般涅槃那。古译为入灭息。息即是灭,故但云入灭,或云灭度,即灭障度苦也。”
[3]此“师”字指禅师而言。六祖谓各门人他日各为分化一方之禅师也。唐释慧海曰:“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成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现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4]出家之人,各有宗派。指其所从之宗派言,各谓之本宗。此之本宗,指禅宗也。
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1],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欲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2],戒与非对[3],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4],喜与瞋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5]。
[1]漏,为烦恼之异名。贪瞋等之烦恼,日夜自眼耳等六根门漏泄流注而不止,故名漏。又,漏者,漏落之义,烦恼能使人漏落于三恶道,故名漏。因之而有烦恼之法曰有漏,离烦恼之法曰无漏。
[2]慈,慈心也。毒,狠心也。
[3]非,不是也,恶也。
[4]悲,悲悯也。害,伤害也。
[5]《入道要门》上:“问:云何是中道?答:无中间,亦无二边,即中道也。云何是二边?答:为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过。云何名彼心此心?答:外缚色声,名为彼心。内起妄念,名为此心。若于外不染色,即名无彼心。内不生妄念,即名无此心。此非二边也。心既无二边,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即名中道。”
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1]。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2]。
[1]裴休《原人论序》:“文字性空。”又曰:“无离文字而说解脱,必曰舍文字然后见法,非见法者也。”
[2]《大智度论》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又复常无常,苦乐、空实、我无我等,亦如是。色法是一边,无色法是一边,可见法不可见法、有对无对、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等诸二法,亦如是。复次,无明是一边,无明尽是一边,乃至老死是一边,老死尽是一边。诸法有是一边,诸法无是一边,离此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菩萨是一边,六波罗蜜是一边,佛是一边,菩提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略说内六情是一边,外六尘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此般若波罗蜜是一边,此非般若波罗蜜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
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1]。
[1]后人以此教授之法为说者,颇多。今以慧海所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中语证之如下:“问:云何是见佛真身?答:不见有无,即是见佛身。问:云何不见有无即是见佛真身?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亦不存。既不存无,有从何得?有之与无,相因始有,既相因而有,悉是生灭也,但离此二见,即是见佛真身。”“又问:何者是无为法?答:有为是。问:今问无为法,因何答有为是?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从何生?若论真无为者,即不取有为,亦不取无为,是真无为法也。”“又问:何者是中道义?答:边义是。问:今问中道,因何答边义是?答:边因中立,中因边生。本若无边,中从何生?今言中者,因边始有,故知中之与边相因而立。”按:举此三则,其他可以推知矣。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1],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2]。次年夏末落成[3]。
[1]太极,唐睿宗年号。元年岁壬子,兹岁正月改元太极。又五月改元延和,七月睿宗传位于太子隆基,八月玄宗改元先天也。盖一岁三改元,故云尔也。
[2]促工,促迫工人使勤作而早完工也。
[3]《尔雅》:“宫室始成而祭之为落。”《诗·斯干》序笺:“宣王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之,歌斯干之章以落之。”刘光庄诗:“故国难归去,新巢甫落成。”今建筑完峻,通谓之落成。
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1]。师云:神会小师[2],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3],哀乐不生[4]。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5]?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若吾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6]。
[1]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谓:“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即此意也。
[2]受具足戒未满十夏者,曰小师。又弟子之称,又沙门谦下之称。《寄归传》三:“西方行法,受近圆已去,名铎曷罗,译为小师。满十夏名悉他薛椤,译为住位,得离依止而往。”
[3]《庄子》:“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4]《庄子》:“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5]阿谁,犹言何人也。古诗:“家中有阿谁?”《三国志》:“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困学纪闻》十九:“俗语皆有所本,阿谁出《蜀庞统传》。”
[6]言若吾不知去处,终不预告汝,以至八月间欲离世间。
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1]。法性本无生灭去来[2]。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3]:
[1]不合,犹云不应该。
[2]《六祖金刚经口诀》:“圣贤生不因念,应迹而生,欲生即生,不待彼命。故既生之后,圆寂之性,依旧湛然无体相、无挂碍。其照万法,如青天白日无毫发隐滞,故能建立一切善法,遍于沙界,不见其少。摄受一切众生,归于寂灭,不以为多。驱之不能来,逐之不能去,虽托四大为形,五行为养,皆我所假,未尝妄认。我缘苟尽,我迹当灭。委而去之,如来去耳,于我何与哉?”
[3]按:此偈惟古本载之,《传灯》、《会元》、《正宗记》等均不载也。
一切无有真[1],不以见于真[2]。若见于真者[3],是见尽非真[4]。若能自有真[5],离假即心真[6]。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7]?有情即解动[8],无情即不动[9]。
[1]一切万法无真正故。
[2]言不可作为真看。
[3]若作真实观之。
[4]则此见无一非假矣。
[5]若于自心了得真正。
[6]离假相,当处即是真。
[7]自心若不离假相,离法何处有真?以上说真假。
[8]自此点破坐禅。
[9]木石一切非情物。《血脉论》:“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此心,即无能运动。此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情,因何运动?”
若修不动行[1],同无情不动[2]。若觅真不动[3],动上有不动[4]。不动是不动[5],无情无佛种[6]。能善分别相[7],第一义不动[8]。
[1]不动行,长坐不卧之禅定也。
[2]同于木石。
[3]如寻自心真不动。
[4]即动摇上有不动摇。《林子坛经注释》:“悟性之人,虽在于虚极静笃矣,然而动上亦有不动。而轮刀上阵,亦得见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则何以谓之动上不动?《坛经》曰:性本不动故也。”
[5]误会不动以为即是坐禅。
[6]《入道要门》下:“请华严座主问:禅师信无情是佛否?师曰: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六道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按:据此即知无情者非佛,故无情即无佛种也。以上说动静。
[7]即言能于事事物物措施裕如也。因物付物而不动其心,即是善分别相。余注见第四品“能善分别诸法相”句下。
[8]注见前“于第一义而不动”句下。《高子遗书》:“当得大忿懥、大恐惧、大忧患、大好乐而不动,乃真把柄也。”又云:“须知动心最可耻。心至贵也,物至贱也,奈何贵为贱役?”
但作如此见[1],即是真如用[2]。报诸学道人[3],努力须用意[4]。莫于大乘门[5],却执生死智[6]。若言下相应[7],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8],合掌令欢喜[9]。
[1]如此见,指不可知无情之不动,宜如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2]此见即是真如之用。按:以上真假动静之旨已明,故以下之偈文皆指不诤而言。
[3]自此下言,不可因诤而入生死。
[4]努力,即著力也。
[5]大乘门,顿教也。
[6]已入大乘门,即离生死智。故不可于大乘门中,仍执生死之见。生死智者,落于生死之见识也。
[7]言与人谈论,若彼此契合者,即可同论佛义也。
[8]若彼不契合。
[9] 亦合掌表敬,使彼生欢喜心,而不诤论。
此宗本无诤[1],诤即失道意[2]。执逆诤法门[3],自性人生死[4]。
[1]顿教宗门本是无诤三昧。《金刚般若经》:“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口诀》云:“何名无诤三昧?谓阿罗汉心无生灭去来,惟有本觉常照,故名无诤三昧。”
[2]《智度论》十一:“须菩提于弟子中得无诤三昧最为第一。无诤三昧相,常观众生不令心恼,多性怜悯。”《金刚经略疏》中:“无诤三昧者,以其解空,则彼我俱忘。能不恼众生,亦令众生不起烦恼故也。”《涅槃经》云:“须菩提住虚中地。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一念不生,诸法无诤。”六祖偈曰:诤是胜负心,与道相违背。便生四相心,何由得三昧?
[3]谓固执违逆诤论之法门。
[4]有诤则瞋,瞋则退失无生忍。失却无生忍,自性便入生死轮回,不能超三界矣。《华严经》:“有诤说生死,无诤即涅槃。”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1],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2],以至于今,钞录流行[3],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4]。
[1]摄心者,摄散乱之心于一也。《佛遗教经》:“常当摄心在心。”
[2]寺见前注。
[3]钞录,略取也。流行,流通也。
[4]《刘梦得文集·三十佛衣铭》:“吾既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得传之旨,作《佛衣铭》曰: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无一里。梦奠之后,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达磨救世,来为医王。以言不痊,因物乃迁。如执符节,行乎复关。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贵。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还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众生曷归。是开便门,非止传衣。初必有终,传岂无已。物必归尽,衣乎久恃。先终知终,用乃不穷。我道无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陈,孰非刍狗。”
偈曰:吾本来兹土[1],传法救迷情[2]。一花开五叶[3],结果自然成[4]。
[1]吾,达摩自谓也。
[2]传法,传如来之正法眼藏。
[3]一花,达摩指自己言;五叶,指二祖至六祖五代而言也。或曰,五叶谓六祖后禅家分为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之谶语,此说非是。观上文衣不合传之说,则与五叶之说相符也。若云五叶指五宗言,则遗却二祖下之五代矣。
[4]付衣虽止于五叶,而五叶后,禅宗大兴。故云结果自然成。《五灯会元》十:“问: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开五叶?师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结果自然成?师曰:天地皎然。”
师复曰:诸善智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1],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2],真成净土[3],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4],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5],普润大地。
[1]种智,佛之一切种智也。知佛智一切种种之法,名一切种智。《大智度论》二十七:“一切种智是佛事。声闻辟支佛,但有总一切智,无有一切种智。”《大智度论》八十四:“一切种智是诸佛智也。”
[2]《辅行》二:“今以供佛之处名为道场。”又学道之处曰道场。《注维摩经》四:“肇曰:闲宴修道之处,谓之道场也。”按:不动道场者,言不必在道场中有所举动,已得真成净土也。
[3]《顿悟入道要门》下:“问:愿生净土,未审实有净土否?师曰: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譬如生国王家,决定绍王业。发心向佛道,是生净佛国。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
[4]一相,指一相三昧而言。一行,指一行三昧而言。
[5]《孟子》:“有如时雨化之者。”注:时雨,及时之雨也。
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霑洽[1],悉皆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2],普雨悉皆萌[3]。顿悟华情已[4],菩提果自成[5]。
[1]霑音“沾”,濡也,渍也。洽,音“协”,沾也。
[2]潭州寻和尚注曰:“一念包容十刹。”按:下三句亦皆寻和尚原注。
[3]祖师说法,众生发萌。
[4]声色无边,般若无边。
[5]信受奉行。按:灵明常照,本无去来;慈悯众生,有感即应。诸佛虽无法可说,但一切时中,一切处所,却无不在演说。特众生执象,徒以形色声音求见如来,转相进远,难得聆悟耳。且佛法难闻,明师难遇,机缘之暂,喻如昙花,岂能久住世间?此大师预告徒众以“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决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之言以示人生死大,无常迅速,及时努力,莫遗恨悔也。兹因众哀留甚坚,且有“师徒此去早晚可回”之言,犹是恋形不舍,染诸法相。故大师一面赞扬神会,一面呵斥余众,更说“落叶归根,来时无口”以示众,不可舍本求末,忘却本来佛性,应悟无念之念,不言之教之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