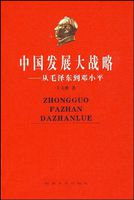5月1日晚,孩子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本·拉登死了,奥巴马马上要有电视讲话。我旋即打开电视机,看了奥巴马的讲话,还有数百民众涌到白宫前庆祝。同一天晚上,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联合城的“9·11”纪念馆前有数百民众聚合,他们手持蜡烛和鲜花,追思“9·11”死难者,气氛凝重。
看电视时,除了奥巴马的讲话,有一位报道员提到一位“9·11”罹难者的家属对杀死拉登的感想。
这位家属说,有人死了,我不会觉得高兴,但这件事实在太特别了。
第二天,另一则报道提到一位名叫谢波德的妇女,她是“9·11事件”时从世贸中心大厦逃生出来的幸存者,“我不想为某个人的死而庆祝,我接受的不是这样的教育。”谢波德太太说,“但这件事非常‘profound’,非常‘profound’。”她用一个难以译成中文的字,一连说了两次,表达她的感受。
我在上课时问学生,你们怎么理解“profound”这个词,有可以代替这个词的吗?不止一位同学说“deep”。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译成中文的字,勉强可以译成“感触很深”。
伊拉斯谟说,成语或习惯语的表达往往只能用原来的语言,翻译以后就会言不达意。同样,那些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感情表达,往往也最难用其他语言翻译。
我想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对拉登之死的感受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这时我发现,我所熟悉的汉语说法,如“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快人心”等,都派不上用场,而偏偏是这个“profound”出现在我的脑际。
“拉登之死”和“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这件事发生时,却又联系在一起。拉登的死,令许多美国人想到的是“9·11事件”中以及在这之前,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被拉登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所杀害的无辜死者。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拉登之死使他们再次感受无辜受害者之死的无比沉重,而不是杀死拉登的狂欢与愉悦。
2011年5月2日波士顿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拉登已去,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的文章:
无论本·拉登的死使美国人在感情上获得了多大的满足,它都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它并不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场通常被称作“反恐战争”,并且被公认开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冲突不会以本·拉登的死而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战争的重点事实上并不是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一枪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打响。
我们陷入了一场决定大中东地区——尤其是富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命运的竞争。这场竞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开始。当时,英法两国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并用一个服务于伦敦和巴黎需要的“新中东”取而代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诺美国将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和财富,这使得美国成为了建立“新中东”努力的一部分。沙特王室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但在开采方面需要帮助。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力量的衰弱,美国成为了中东地区稳定(以及确保西方能够获得该地区财富)的主要西方担保国。也是在6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石油储备再也无法满足美国对廉价能源的需求——廉价能源是个人流动的前提,而个人流动则是美国人所称的“自由”一词的核心内涵——因此,获得巨大的中东石油财富成为了绝对的当务之急。
我们(美国)是从1980年开始参与今天的这场战争的——坦率地说,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作“确保美国生活方式的战争”。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中东政策的全面军事化开始了。吉米·卡特所倡导的“卡特主义”宣称,美国承诺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无论是外交辞令还是威胁使用武力——来防止任何敌对力量控制海湾地区。随后,美国的军事干预倾向不断升级,对此,罗纳德·里根、乔治·H.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先后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不仅阻止其他国家主宰海湾地区,还寻求由我们自己来主宰这一地区。
美国军事驻扎和军事活动的升级引发了敌对反应,“基地”组织则冲在了那些希望将西方力量一劳永逸地赶出穆斯林土地,并给大中东地区留下自身烙印的人的最前线。在20世纪90年代,从世界贸易中心遭受的首次爆炸开始,早期的冲突开始出现。一直到“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才发现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为达成目的会无所不用其极。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乔治·W.布什总统选择参与本·拉登的这场游戏。为了回应“9·11事件”,他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为建立大中东地区秩序所付出的努力,并且有信心美国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来完成这一目标。“准战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战争,没有一座要塞能够置身事外。间歇性的敌对行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战斗。
美国人没有吸取教训。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这两场战争的开销也十分惊人。然而,美国人没有从痛苦和失望中吸取到什么教训。
尽管在决定小布什继任者的竞争中,贝拉克·奥巴马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能够奉行不同路线的候选人,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上任后,他再次加强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并且在巴基斯坦和利比亚开辟了新的战场。尽管奥巴马总统尽力避免使用“反恐战争”的字眼,但这场战争——以及从1915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的计划——却依然在继续。尽管奥巴马总统确实可以将本·拉登的死称作一场重大胜利,但只要最初引发战争的核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本·拉登的死就不是决定性的。
只要美国的生活方式依然依赖对大量外国石油的获取,那么美国决定大中东地区命运的努力就将继续。因此,那些反对西方建立一个服务于西方目的的新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将继续战斗下去。本·拉登的死将不会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
也许,在战略家的眼睛里,对于反恐战争还有另外一番解读,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美国占领了世界岛——欧亚内地的中心阿富汗,所有的大国均已在美国的战略监控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没有了安定的后院。美元和石油拥抱也更加紧密了。
在反恐战争的十多年里,美国加强了情报系统的建设,美国的信息系统强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许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当你拿起手机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你用汉语说“奥巴马”、“中央情报局”等等词汇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通话记录已经被在你头顶几百公里的间谍卫星收集了,这些数据会被实时地传递到美国的中央数据库进行分析,分析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然后逐步筛选威胁等级。也许,我们只要使用现代无线电技术,也就无法逃脱美国人的全球信息监控系统。
反恐战争促进了美国的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同样的,美国人可以将自己的数据分析技术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很多国家的金融官员的通信信息时刻处于美国人的监控之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美国在战场获得单向的信息透明之后,在经济领域也将获得单向的信息透明。这是反恐带给美国的技术进步。
战争是丑恶的,但是战争能够促使美国精英统治集团花钱去研发新的战略技术。二战就是如此而已。回到恐怖主义的话题,2001年,“9·11”这个数字催生了一个新名词——恐怖主义,这十年来,美国就是以这个名词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反恐战争打了十年,不见任何减弱迹象,阿富汗的局势不见起色,伊拉克政权弱不禁风,恐怖分子滋生世界。
美国的种种行为,不禁让人怀疑,究竟是在反恐,还是在制造恐怖主义?也许只要美国想称霸世界,那么恐怖主义就一直会是美国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