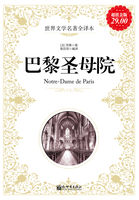现场于是便转移到了张朝晖的房间里。张朝晖本来的想法,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两个人就各不相干了。可瞿红尾随而至,就是出于礼貌习惯也不能将对方轰走。况且瞿红只穿了一件睡衣,里面几乎一丝不挂,如果在走廊里闹腾起来不免麻烦。但他的拒绝却是一如既往的,心理上的抗拒就更胜一筹了。
张朝晖一鼓作气,打开了房间里的衣橱,取下衣架上的衬衫,并从箱子里找了内裤和袜子。然后在刺眼的灯光下解开睡衣的腰带,两肩一耸,那睡衣就自行滑落下去。张朝晖全身赤裸地站在房间中央,一点也不避讳瞿红。脱光后他慢慢地开始穿衣服,先是内裤,再是衬衫。他的动作尤其缓慢,那么优雅和仔细,就像瞿红压根就不存在一样。
再说瞿红,进门之后又恢复了卧地不起的姿势,虽然卑微但避免了诸多的尴尬。她再一次开始哭泣,或跪或卧,随着张朝晖穿衣服的动作调整着自己的姿势,视角却是始终上仰的。
张朝晖的睡衣下滑的一瞬间,瞿红再次燃起了希望,以为张朝晖要和她做爱,不由得瞄向那关键部位。但显然没戏,那地方就像一只黑拳头似的握着,一根手指颓然下垂。但张朝晖的整个形象在瞿红模糊的泪眼中还是极为性感的,就像一尊青铜雕像般坚不可摧,凛然而不可侵犯。随即,张朝晖就给那雕像穿上了衣服。穿了衬衫,再穿外套,然后是袜子,先左后右。眼看就要穿上长裤了,瞿红绝望地哭道:“我还以为你会介意呢……”“介意什么?”张朝晖已经开始打领带了。“介意我怀了丁老板的孩子。”“我说过吗?”
“你不是说,三个人又是一种格局吗?”“我是说过,难道不是这样吗?”说话间张朝晖已经打好了领带,并且穿上了长裤。那长裤提起来后,张朝晖开始系皮带。瞿红再也忍耐不住,扑了过去,一把抓住皮带的金属扣。这一次张朝晖的躲闪很真实,生怕瞿红弄皱了他的衣服。“你要干什么?”他紧张地问。
“我,我要和你做爱!”“做爱干什么?”“我要怀一个我们的孩子。”“怀上然后再把他杀死吗?”
张朝晖厌恶地推开对方,终于将皮带系妥帖了。他跺了跺脚,以便让全身上下的衣服平顺些,之后就坐在床沿上开始穿鞋子。系好鞋带张朝晖站起来,再次跺了跺脚,终于彻底搞定了。但他并无意停下来,又走进卫生间去取剃须刀、护肤霜、香水一大套东西。再次走回房间里,将这些玩意儿塞进箱子里。又去房间衣橱的衣架上取没有穿的衬衫,去写字桌上收拾电脑。
瞿红完全看傻了,她没有再次扑向张朝晖,也没有尾随他,只是坐在地板上愣愣地看着,目光追随着对方的每一个动作。
瞿红也没有再说什么,甚至也已经不哭了。房间里一时安静之极,只有张朝晖走动拾掇的声音。电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播了,或许他们进来以后就没有打开吧?直到房间里已收无可收,张朝晖这才稍歇片刻,抬起头来作最后的巡视。
“你要去哪里?”瞿红木然地问。“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真是太可怕了,太粗俗了。”声音不大,然而回声四起,震得瞿红脑袋嗡嗡直响。
“那,那我们的合作呢?”“我以为我可以,”张朝晖一字一顿地说,“但还是不行。我没法和中国人合作!”
最后一句话几乎将瞿红震昏过去。趁着一息尚存,她终于有所反驳:“你,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
“我是,但不是你们这样的中国人!”于是瞿红便收到了死刑判决,或者说像收到死刑判决一样地瘫软在地,不再挣扎了。
张朝晖最后打量了一眼1727房间,除了那只画盘孤零零地立在床头柜上,这里就再也没有属于他的东西了。当然了,即使是那只画盘也不是属于他的,早在十五年前就卖给了瞿红。此刻,后者委顿在地板上,近乎半裸,苍白的肉体和摊开来的睡衣占据了很大一片地方。她也不是属于他的,或者说是他决定弃之不要的,就像装在时装袋里的那包呕吐物。
张朝晖转身出了门。那门刚刚关上,里面就传出了瞿红歇斯底里的哭号声。好在酒店房间的隔音效果不错,铺在走廊里的地毯也颇能吸收声音。瞿红的哭声虽然刺耳,分贝却不算高。张朝晖一面离开那哭声一面念叨着:“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哭出来才能好受些,毕竟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心里面有愧呵……”
张朝晖带着箱子,乘电梯去了楼下的大堂,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走出酒店。
实际上,除了长城长酒店,张朝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了。当然他可以另找一家酒店,但酒店和酒店那还不都是一样的吗?何况这长城长是他在网上搜索、经过千挑万选才确定的。如今的北京城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联系上的熟人,除了常乐,而这家伙他躲还来不及呢。
收拾行李时张朝晖态度坚定,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但直到来到楼下的大堂仍不清楚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然而不管去什么地方总得把这里的房费结清,于是张朝晖便去了前台。这时候他想起来,瞿红还待在1727房间里,结账时难免要费口舌。张朝晖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不想提及她的存在,于是就对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开一个房间。”他就像刚刚抵达酒店的客人,是从转门那儿而不是从电梯门出来的。
说着张朝晖将护照递过去。工作人员接过,扭头去电脑上查询,然后抬头,狐疑地看了张朝晖一眼,“先生,您已经订了房间,是昨天下午四点三十七分入住的。”就像张朝晖订了房间并住进来他自己不知道似的,对方看他的眼神也像在看一个梦游症患者。张朝晖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他的一只手正好放在裤袋里),证实自己没有在做梦,这也不是一个梦。但他不想多加解释。
“我再开一间,”他说,“就在原来房间的边上。”“您是不是住得不舒服?房间有问题可以调换,今天空房间很多。”“谢谢,不用了。”
“要不我帮您把昨天的房间退掉。”“不用了,明天两间房间一起结算。”“那昨天的房间我们仍然是要收费的。”“当然,当然……”
啰唆了半天,工作人员这才开始办理有关的手续,但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处在他的位置上,见过的有钱人多得去了,但从没有见过一个要同时住两间房的。难道说一间睡上半夜,一间睡下半夜?如此来回折腾那还能睡得好吗?当然了,这年头什么样的怪人都有,他和前来接班的家伙总算是有谈资了,可以说道说道了……
办完手续,拿上门卡,张朝晖拖着箱子返身走回电梯间。仍然是十七楼。电梯门打开后出现了他刚刚离开的那条走廊。走廊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灯光幽暗,一个人都没有。
那走廊相当长,张朝晖以前没有注意到。此刻他就像在一条寂静无声的地道里穿行,拖在身后的拉杆箱轮轴滚动,但不发出一点声音,只是将些微的震动传递到他手上。张朝晖走呀走呀走呀走,因为道路熟悉并不需要东张西望查看指示房间号的标牌。找到1727就找到他的新房间了,于是张朝晖便一路驾轻就熟地向1727房间而去了。到了门口竟然一阵恍惚,差一点就用手上的门卡去开门。突然醒悟过来,自己已经另开了一个房间。张朝晖查看房卡后确认是1726,但他还是在1727的门口停了下来。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并听不见瞿红的哭声。他向前迈了一步,把耳朵贴在门上,还是没有任何声音。难道说瞿红已经离开了?或者说已经睡着了?如果离开了会不会在隔壁1728她自己的房间里呢?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另开一个房间的确是多余了,显然是一种无谓的浪费。
张朝晖将他的箱子立在1727房间的门边,轻手蹑脚地移到了1728房间的门口,再次将耳朵贴在门上猫眼的位置上。那里面也一点声音都没有。张朝晖拿不准瞿红是否真的回了自己的房间,两间房间她到底在哪一间?也许两间房间都是空着的,那就更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了。
最后,张朝晖打开了新开的1726房间的门,拖着箱子进去了。这间房间和另外两间房间里的陈设一模一样,只是气息有所不同。是否可以这么说,瞿红的房间里有似有若无的血腥味,张朝晖原来的房间里则是爱情的气味,新开的这间里只有宾馆房间的气味,说不上好闻还是难闻。这次张朝晖没有兴师动众,打开箱子整理衣服什么的。他毕竟太累了,而且又不是要在这里扎根,就是多住几天的念头也没有。张朝晖开了空调,脱掉外衣就爬上床去,但并没有躺下。他蹲在床上,姿势古怪地将耳朵贴在墙上又听了半天。
墙的另一边就是1727房间,而且两个房间里的床是头对头抵着放的,中间只隔了一堵墙。从1726房间的这张床上应该可以听见隔壁的那张床上的动静。然而张朝晖什么也没有听见,或者说他听见了一些模糊的响动,但无法确定含义。
于是他又跳下床去,关了房间里的空调,在没有声音干扰的情况下继续偷听。关灯以后噪音更减,黑暗之中几乎是万籁俱寂。张朝晖听着听着就像墙上挂着的一张画似的滑落下去。然后他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