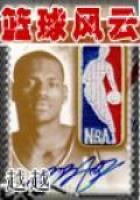当晚算是团圆。以前的饭局虽然最后也是以三个人结束,但张朝晖坐在那儿总是心事重重。常乐看着对方愁眉苦脸地扒完饭,然后就起身告辞。张朝晖也不留,更别说送。今天明显有些不同,当常乐说时间不早了他要回去时,张朝晖死活拉住不放。“哥们再喝两杯。”他说。
黄酒喝完了,张朝晖的店里只找到三瓶夏天留下来的啤酒。张朝晖也不管过没过期,让瞿红开了,倒在三只喝啤酒的玻璃杯里。那啤酒虽没有在冰箱里冻过,但一口下去透心地凉,不禁让人想起他们第一次在小饭店里吃饭的情景。张朝晖少有地健谈,竟然回忆起隔年往事。瞿红再次暗自落泪:他还记得当初啊……聚会到两三点,张朝晖建议常乐就在他们家睡了,说是卧室里的双人床特别宽,是两米乘两米的,完全可以睡三个人。“常乐又不是外人,我兄弟,你不会忌讳吧?”他问瞿红。
后者没有说话,张朝晖又转向常乐,“今儿下雪,路不好走,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差点没摔一跤,回去睡和在这儿睡还不是一样吗?又没人等你……”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并且句句体贴。
常乐最后还是走了。他心里想:陪睡觉那是你的事,再说又不是陪瞿红一个人睡,是陪你们两个人睡,也就是说陪陪瞿红睡觉的人睡。自己就是再高尚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不可能不嫉妒,因此还是一走了之。况且瞿红今天刚说了刘老三和陈玉珍的故事,如果这两人在床上动作起来,自己不就成了他们的儿子了吗?情人做不成做朋友,总不至于去做人家的儿子吧?那也太不像话了!
常乐向张朝晖敬了最后一口酒,预祝他早日收到Eric的邀请函,然后就夺门而出了。透出温暖红光的“张记UFO”被抛在了身后,常乐伸展双臂深深地呼吸,真的就像要飞翔起来了。他想象着自己像一朵大雪花一样向他的“虎穴”飘去,无数朵轻柔的小雪花一路跟随着。
常乐走后,瞿红和张朝晖就进屋上床去了。后者像发现瞿红的厨艺一样地再次发现了她的身体,不禁来势凶猛。瞿红又是一阵难过。她一面迎合张朝晖,一面禁不住心潮起伏。
将近有半年了,他几乎都不怎么碰她了,即使瞿红有要求张朝晖也是应付了事。幸亏有床头柜上的那只盘子,每次她都能抵达高潮。只要手往上面一搭摇晃几下就能如愿以偿。就像做这事和张朝晖完全无关一样,事实也是如此。有时候张朝晖懒得应付,躺下后立马鼾声起伏,瞿红便悄悄地从被子里伸出手,抓住画盘,靠自己的力量消遣一番。一面忙活一边还得提防对方,生怕动作过大惊醒了张朝晖。没想到今天……开始的时候瞿红由着张朝晖,想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自己是否可以不借助画盘就能抵达高潮。后来,随着后者无休止的进攻,瞿红绝望了。那里渐干,就像衣服缩水似的收紧了,并伴有摩擦的刺痛之感,如果再不拿出撒手锏来她就得受伤。
瞿红的手已经从被子里伸了出来,但又收回去了。这会儿她的心情非常复杂,她就是不想让自己快活,就是想让自己受伤,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张朝晖一手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有必要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而不是相反,身体的快乐掩饰了伤害。
瞿红第一次(最初的那次除外)和张朝晖做爱时没有抓住画盘。她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并在心里和对方告别。当然了,这告别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办到的,但至少已经开始了。瞿红要把自己从身体的享乐中抽离出来,走出张朝晖的生活,走进没有张朝晖的生活。
其后的几天,日子照旧。张朝晖画盘子、学英语。由于大雪封门,来大王艺术村转悠的游客几乎绝迹,生意是甭想做了。瞿红则踏雪去农贸市场,踏雪去其他艺术家那里串门,和他们的女人闲话赏雪,再就是陪着常乐去喂老任的藏獒。晚上,张朝晖仍然立于村头打电话,瞿红、常乐仍然围炉饮酒。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家都在等待冰雪消融的那一天。
终于,这天上午村子上来了一个人,绿衣绿帽绿自行车,映衬着田野上的皑皑白雪。仿佛那人是春天的信使(也的确是),将一封洒着香水的信交到了张朝晖的手上。张朝晖再次激动起来。不用说,那天晚上又是一番团聚。夜里,张朝晖又是一番猛攻。瞿红照例没有理会画盘。
第二天早上,张朝晖黎明即起,进入前店工作,画盘子。门外小街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房檐的椽子上正往下滴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大王艺术村里竟然有了一些游人。瞿红一直没有从后面的卧室里出来,等她出来的时候已是焕然一新。
她穿上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衣服,手上提着大包小袋,身后拖曳着那只大皮箱。瞿红昂着头,从店堂里穿越而过,奔向门口。她没有朝张朝晖的方向看,就像那人根本不存在一样。“你这是干什么?”张朝晖不无惊讶地抬起头。“你不是要去美国吗?我也该回家了。”“别价,”张朝晖说,“签证还不一定能办下来呢。”正是这句话激怒了瞿红,她停在店堂中间不走了。“张朝晖啊张朝晖,你到底是什么人?签证办不下来我就留下,办下来我就得走人?!”“我可没有让你走。”
“那还不一样吗?”瞿红说,“张朝晖,我告诉你,你有移民倾向,我要去告你!”
听闻此言,张朝晖霍地就站了起来。“你敢!”他说,同时奔到了门边上,下意识地用身体挡着大门。
“我敢!我敢!我就敢!”瞿红叫喊着,人也不出去了,而是转身往房子的里面冲。
瞿红冲到货架前面,抓起一只画盘就向地上扔去。一声脆响,画盘顿时就碎成了两半。
“这可是艺术!”张朝晖绝望地叫道。
“艺术怎么啦,我全买了!”瞿红说着又拿起一只画盘,扔在地上,“这只我也买了。”她说。
张朝晖浑身颤抖着,也向货架冲过去。他抓起一只画盘,举过头顶,想了想又降低了高度。“你扔啊,有种你就扔,你扔的我也买下了!”瞿红说,然后扔了第三只盘子,就像在为对方做示范一样。
“那好,我帮你扔!”张朝晖手上的画盘终于落地,由于力道不同碎成了四瓣。自此以后两人就不再言语,一只接一只地从货架上取盘子,然后扔在地上。动作变得冷静而流畅了,节奏感也出来了。你来我往,乒乒乓乓,掷地有声,就像是在合奏一样。他俩默默无语地轮番扔着盘子,渐渐地竟有了夫唱妇随的意思。
以前,瞿红从未参与过张朝晖的工作,后者坚决不让,这是第一次,两人协作将货架上的画盘扔得一干二净。瞿红有感于这样的场面,这时候早就愤怒全无,反倒是一团暖意从心头升起。张朝晖自然也有他的想法:反正这些盘子卖不掉,不扔白不扔。瞿红说她已经全买了,我扔的她也买,也就是说,每扔一只就等于卖掉一只,每砸碎一个就等于画盘的价值实现,自然是砸得越多越好,只怕不够。再说马上就要去签证,签了就要去美国,想必需要一大笔的费用,这钱不从画盘来从哪里来?不从自己的艺术来又从哪里来?
于是张朝晖扔得更加坚定,也更加沉着和仔细了,非得看着盘子粉身碎骨才肯罢休。如果没有完全粉碎,碎成两半或者三瓣,他就拿起来再扔。直到所有的画盘全都扔完了,只剩下那面空虚不已的货架,张朝晖捡起地上的一块小瓷片,一面琢磨着:哪儿还藏着画盘呢?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起身直奔里面的卧室,再出来的时候手上竟然有一只完好的画盘,也就是当初瞿红买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盘子。他将那盘子高高地举了起来,瞿红见状扑了过去,伸手去够。“不,不要!”她尖声大叫。
没有够着盘子,但瞿红抓住了张朝晖的手臂,用双手拼命攥住。张朝晖使劲地上举,几乎把瞿红给吊起来了。如果这时候张朝晖撒手,盘子就会掉下去,但不能保证碎得彻底。因此他并没有撒手,就这么让瞿红吊在自己的胳膊上转圈。
转了两圈之后,张朝晖一阵晕眩,差点摔倒。瞿红及时落了地,将对方的身子一把扶住,两人相拥在一起。
张朝晖除了感觉到瞿红的体温,还感觉到了她的急切。那盘子上画的毕竟是他的肖像,自己不在乎,但瞿红在乎,如此的在乎。张朝晖虽然天性冷淡,但并非铁石心肠,一时心软加上头晕,画盘就被瞿红抢夺到手了。
瞿红抢到画盘后就放开了张朝晖。她将那盘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自我解嘲说:“这盘子我已经买过了,不能再买第二次。”听上去有点可笑。
事情到了这份上,性质已经全变了。瞿红和张朝晖都觉出了这一点。愤怒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余的只是人生无处不在的幽默。因此当他们相拥着走出“张记UFO”的时候简直就像是一对幸福的情侣。
瞿红抱着画盘,绘有张朝晖肖像的那面朝内,紧贴着她小巧的乳房。张朝晖略微落后,一条手臂温柔自在地揽着瞿红的后腰。两个人一概笑容可掬。
门外的小街上雪后初晴,游人渐多,明媚的阳光下世界清晰得可怕。房子的右侧停着瞿红的桑塔纳,车窗玻璃熠熠生辉,由于长时间没有开动过,轮胎上方尚有积雪。一大伙人,本来是堵着店门看热闹的,看见这一对璧人灿然而出,不禁向后退了几步。这伙人中有村里的艺术家,也有来艺术村观光的游客。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没见过啊?”瞿红撒娇般地说。“没见过。”一位剃着光头的艺术家说。瞿红冲他嫣然一笑,“我们就要离开大王村了,把带不走的东西处理一下。”
“原来如此。”光头说,“都散了吧,该干吗干吗去。”于是看热闹的人便意犹未尽地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