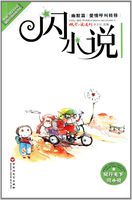天将黑时分,为不引人注意,龚合国夫妇坐出租车(而非局长专车)来到离县城约三十公里外的龙头村。
村西头,一处两亩地大小的鱼塘东侧,龚合国家三间正房和两间西厢房的老祖屋,如今已经改造成连成一体的二层小楼。楼下,一个高大、宽阔的门洞,贯穿了厢房和正房的连接处,将盛夏的和风,一点点抽吸到宽敞的院落中来。
龚合国夫妇进院门时,他的老母和姐姐一家人刚吃完晚饭,正在门洞下纳凉。鱼塘岸边,有一些暗红的火星闪烁,青烟时不时地飘进门洞——那是驱蚊用的蚊烟。
“妈,姐、姐夫!”龚合国简短地打过招呼后,便和邬红梅急急地走进楼下东侧的房间——这里是他老母亲的卧房。他们关好房门后,移开靠西墙的一面老旧的衣橱,白色的墙壁上便露出一个圆圆的小洞。邬红梅忙掏出随身带来的钥匙插进去,一个小铁门便自动打开了,露出里面一个约两尺高、一尺宽的灰色的保险箱。她又摸出身边的一张纸条仔细看了一遍,才伸出肥厚的手指,一会儿正过来一会儿又反过去地反复旋转保险箱的号码锁。终于,那锁“滴答”一声开了,露出了里面上上下下几个抽屉。
邬红梅打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放着的都是些房产证,名字有她和龚合国的,也有龚合国老母亲和他姐姐以及他姐姐的孩子的,共有六本。邬红梅打开其中的一本,执在手中,不无骄傲和得意地对龚合国说:“这套房子,已经涨了快十倍了!”
没想到龚合国听了,却冷冷地道:“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为什么不高兴?不管怎么说,这家产有一多半是我挣的。”邬红梅嘟起嘴,有些不服气。“那又怎么样?万一这是上面设的一个局,为了‘引蛇出洞’,钱算得越多,判的刑期还不是越高!”“有那么严重吗?不是说好可以留70%……”
“凡事还是多往坏处想想为好。”龚合国说,一面在本子上仔细记下了那六本房产证的人名和地址。
看他写完了,抬手擦着脸上的汗,邬红梅这才悻悻地将手中那些房产证重新放回原处,接着打开了第二个抽屉——里面全是些珠宝首饰:鸡血石、翡翠挂件以及和田玉等等。龚合国也一一登记下来。最下面一个抽屉比较大,差不多可以抵上面两三个。里面一多半地方放着美金、英镑和日元之类的外币,估计有60万元人民币。角落处还端放着一尊几公斤重的金佛,以及一棵和真白菜差不多大小的“玉白菜”……“就这些了?”抄录完毕,龚合国问。邬红梅刚要作答,房门口却传来龚合国老母亲的声音:“里面热死了,快出来乘乘凉吧!”“好的,妈,就出来!”邬红梅一边答话,一边朝龚合国点点头,但又压低嗓门提醒他:“你说的,还有些字画放在你办公室里……再还有,你书房里的那几件青花瓷,赵军给买的两套黄花梨家具还没算进去。可是……”
“可是什么?”龚合国合上本子,问。“你真的要把我们这些年来辛辛苦苦挣的这些家产,都一五一十地交代出去吗?”
“——这个嘛,你别担心,我自会考虑的。但不这样清点一下我心里没数。再说,有些东西不亲眼看一看也早忘了……”
“你不会是想借机查查我有没有藏‘私房’吧?”邬红梅听了,仍然心存疑虑,甚至还有些不信任地乜了龚合国一眼。
“你这扯哪里去了,我这里都紧张得快要崩溃了,这种时候哪还有心思和你玩心眼……再说,我如果不放心你就不会交给你了。”龚合国说,看到邬红梅依旧一脸委屈的神色,就弯下腰,低下头,凑到她汗津津的脸上蜻蜓点水般亲了一口。
这一招还真管用,邬红梅马上又和颜悦色了。于是,两人重又锁好保险箱,关上小铁门,并将衣橱移回原处,才回到门洞里和大家一起纳凉。但因为蚊子多,邬红梅坐下不久便被咬了几口,夫妇两人又决定去村外的灌溉渠上走走。
“哎,世事无常。升官升不了,麻烦却揽来了。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早点编个理由申请退休算了。你看看,这满天的星斗……想起来,真是应了《红楼梦》里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啊……”到了村外,走过一座小石桥后,龚合国抬眼望望布满在黑暗苍穹间的满天繁星,不无感慨地说。
“你不是都揣摩过了嘛,上面是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干部队伍全部垮掉而不闻不问的——就是一只老母鸡,也会拼命护着自己的小鸡的,更何况,我们的党,不是从来都‘伟大、光荣、正确’吗?”邬红梅捏紧他的手,头靠到他肩上,满怀憧憬地说。
“揣摩归揣摩,再‘伟大、光荣、正确’也不能说就不会犯错误。”龚合国说,忽然又道,“要是朱瞎子还在就好了,可以请他帮着算一算,他是能够未卜先知的。”
“你可以再找鬼头镇的茅婆婆嘛。”邬红梅提醒他。“我早想过了,但不能找。现在找她的人一定很多,说不定她早就被监视起来了。”
“那就明天一早去庙里求签。”邬红梅又说。“更不行,这种时候去那种地方等于自己往枪口上送,那里一定会有反贪局或纪委的人在监视。”两人沉默不语了一会儿,龚合国忽然猛地抽回自己的手,道:“对了,我们可以去村东头的土地庙求个签,这时候肯定不会遇到人。”“土地庙?土地庙里又没有签,怎么求?”邬红梅不解地问。“这我自有办法。”龚合国说,便拉了邬红梅急急地往回走。到家后,他让正在上高中的小侄子找来一张白纸,用水果刀裁成四片,再用圆珠笔分别写上“真”与“假”,“通”与“不通”。然后,又让姐姐去村里的小卖部买回一对蜡烛和一束“平安香”。
邬红梅也想去,但被他拦住了,“这种事情只能男人做的,你去了于事无补,目标也大,让别人看到不好。”
邬红梅就识相地留在家中,陪婆婆和大姑说些闲话。村里的土地庙留在龚合国记忆中的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童年记忆中的:屋檐和屋脊都翘得很高,土地公公(似乎还有一个土地婆婆)端坐在里面砖砌的案台上,面前放着铜质的烛台和香炉。香炉里常年布满香灰,村里人手割破了,都会去那里抓一点香灰往伤口涂一涂,抹一抹,过几天自然就会结痂愈合。当然,村里谁家里不和,或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也会到这里来烧香磕头求告。可惜,这土地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捣毁了……另一个便是20世纪末村里的老百姓们在村干部的默许下又偷偷重新修建的。因为怕上面知道了,认为是搞迷信,要强令拆除,就没有盖成原来的土地庙样子,而是建成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房的格局,兼之西墙就是借用隔壁一家人家的院墙,故即便有人从门前走过,也不会想到这里是一个土地庙,反倒会以为是一个茅房了。
龚合国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踅进土地庙里,掏出打火机点亮一对蜡烛后,才发现水泥板的案台上,除了原来黑陶的土地公公外,东西两侧还各多了一尊白瓷的观世音菩萨像和石膏的毛主席像。
这样三尊塑像排在一起,很让龚合国吃惊、困惑和感慨。尤其是毛主席像,他可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想不到如今竟与神、佛“殊途同归”……以至于他已然点好了那束平安香,一时竟不知该向谁去叩拜。
但他转念一想,也就心知肚明——人世间办点事,有时还要敲上几十个图章才行,现在向阴间和天界求告,岂能随便冷落了哪一个?于是,他无限虔诚地将已经点燃的香仔细插进香炉里(值得提一下的是,这香炉其实是用一个硕大的黑陶钵替代的,至于烛台,则是两个小一些的泥碗,里面盛满了已掺杂着许多蜡烛油和泥灰的大米),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仁慈善良的土地公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最近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想请你们看在我多年勤勤恳恳工作的分儿上,帮我逢凶化吉,并指点迷津……”
可是,刚刚念完,磕完头,蹲身预备站起的当儿,像是被人突然点了穴似的,他竟一阵头晕目眩,然后仰面八叉地摔倒在地。幸而屁股比较肥厚,爬起来摸一摸,只被硬硬的泥土块硌得稍稍有些疼痛,并未伤筋动骨。
他是个早已习惯了“共产党员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人,就觉得有些奇怪——他平时很少头晕目眩的,难道是贫血,或者有人推了一把?猛然就有些开窍:“我念过那么长时间的‘妈妈抱抱’,就是想和毛主席对上‘频道’,请他老人家保驾护航的。虽说他老人家后来没能帮助我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说不定今天倒会帮我脱苦脱难呢……所以,祈祷岂可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在最后?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和土地公公都答应帮忙了,毛主席却生了气,才推我一把……啊啊,真是……”
于是,他忙整整衣冠,朝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一躬,又将毛主席排在前面,重新念了一遍祈祷词,并追加了几句“妈妈抱抱”,然后万分虔诚地再磕了九个响头。
然而,站起身后,他还是打了个趔趄。再仔细一想,又发现还有些不对劲儿——虽然土地公公的级别可能比自己还低,最多也只能算个“乡镇土管所领导”,但谁都知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自己既然是到土地庙来祈祷和求签的,理应土地公公才是主人,是正神,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势利,主宾不分,反倒让菩萨和毛主席压住土地公公呢?
他心里连叫几声“不妥”,就又重新跪下去,将祈祷词中三位“尊神”的次序重新变更为“仁慈善良的土地公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
再拜,再磕头,他才心满意足地再次站起身。但他忽然又有一种错觉:面前端立着的三位“尊神”,瞬间竟变成“县委、人大、政协”三套班子的头头了。思想起来,他平时也经常给他们烧香、磕头的,但其中似乎总有一两个“频道”对不好,不然,他这样的教育界“能人”又何至于十几年不挪窝呢?
他吹灭了蜡烛,心神恍惚地预备走了,出门前才想起签还没求,就又在三位“尊神”面前跪下,从口袋里摸出那四张纸头,揉成一个个小纸团,合在掌中抖了抖,再让左手掌心朝上,托住那四个纸团,然后闭上眼,抬起右手,用粗粗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犹犹疑疑地从那四个纸团中拈出两个,凑到手机的荧光屏前,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个纸团上真真切切写着“真”,第二个纸团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通”。龚合国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就又试了两次,结果竟惊人地一致。他大喜过望,完全相信这是土地公公、毛主席和观世音菩萨在“显灵”,就又一气磕了三九二十七个响头。“通了,通了,通……”出了土地庙后,他极少有过地兴奋异常,心里不住地叨叨着,同时仰脸朝天,一遍遍轻舒双臂,并暗暗发愿:“……只要能渡过眼前的难关,过些日子,一定回来好好重修土地庙(当然,还要带上邬红梅一起去韶山祭扫毛主席的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