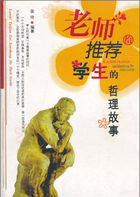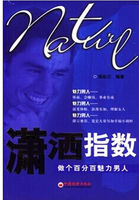原来,是一本用过的图画本。上面还有我大哥念书时用的名字。有一些破损,但还是显得很整洁。我想,大哥一定是很珍惜这个图画本的。我打开来看,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漂亮的铅笔画。有人物,有风景,还有大哥临摹的毛主席像,画得真的非常好,有很多画,老师还打了分数,都是优。直到现在,记忆中,我都认为那是我看过的最精美的铅笔画。
大哥说,哪一天我画得和他一样好了,他就答应给我买水彩笔。我当时也没有生气,就乖乖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画过大哥,而且相信大哥是说话算数的。
但是没有过多久,我自认自己的绘画技艺还没有任何的提高,大哥忽然就送了全套水彩笔,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这是我记忆中,少有的和大哥交流的片段。
也是那一年,大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大嫂。他比大嫂大3岁。这年,我大哥27岁了。已经属大龄青年。
我母亲很喜欢我大嫂。大嫂不嫌弃我们的家境,在当时,算是我们家高攀了。我想,当时,我大哥最吸引大嫂的除了大哥心地善良以外,还因为我大哥实在是英俊潇洒。当年,我大哥真的很帅气。追他的姑娘有很多,但一听说家里还有四个正在念书的兄弟姐妹,纷纷掉头。所以,我对于我大嫂肯嫁给大哥,让他有个温暖的家,一直都很感激。
一年后,大哥和大嫂结婚了。婚后,大哥还是常常帮助我们。也许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大哥和大嫂在婚后8年才要了小孩。
在大哥的同学中,他的孩子是年龄最小的。偶然想起这一切,我们兄弟姐妹也觉得有些内疚。可大哥从来不在意这些。
那时,我们的家境已经好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人还在读大学。我在上海读大学也好几年,其实已经长大,但在大哥眼中,还是小孩一个,所以始终再没有任何贴心的交流。他对于我的一切,还是像父亲一样的关怀。除此而外,在我面前,大哥也从不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是和大嫂之间的任何事。大嫂不在时,大哥会常常问我在上海读书钱够不够花之类的问题,而我面对他,总有一点像面对长辈一样的怯懦。
在我的眼中,大哥和大嫂像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时,他们或者相敬如宾,或者沉默不语。生活的真相原本就是平淡质朴,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他们和大多数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同。
这些年,我在上海一个人工作生活,谈过一些恋爱,但最后还是一个人在城市里独来独往。现代男女,爱得很难纯粹,偶然会觉得有一段刻骨的恋情,才是真的传奇。
半年前,大哥从原来的单位辞职。在离小城50公里外的开发区自己单独做些小生意。与大嫂分居两地。
这是我了解到的我的大哥。还有他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中秋夜母亲的一番往事细诉,我一直会以为大哥在为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岁月后,已经拥有了幸福。母亲的话,让我感觉,一切恰恰相反。
这个中秋夜,我在给母亲打电话之前,大哥打过电话给母亲。他头一次在电话里对着我母亲哭泣。他说,他要离婚。
母亲说大哥在电话里的哭泣令她伤心欲绝。我听了就觉得吃惊,在我眼中,我甚至认为我大哥是个不会哭泣的男人。母亲和我在电话中说起这一切,也哭。我在母亲内疚的哭泣中,慢慢了解到大哥生命中那段年轻的往事。一切,在隔了二十多年后,我第一次知道。仿佛在我眼前,忽然展开一部怀旧的老电影,在母亲的叙述中,那些人物和情节,虽然蒙着一些岁月的沙尘,但依然是清晰如昨日。
大哥1978年高中毕业时,19岁,曾经在家待业一年,帮母亲打理一些事,也是在这一年,大哥认识了和他同龄的名叫云英的年轻女子。
我大哥很喜欢她。那个叫云英的女子对大哥也是很仰慕。她是我大哥爱过的第一个女子。可是我母亲反对。原因很简单。云英也是待业在家,没有工作,在家中,云英也是老大,家中兄弟姐妹也多,负担也是很重的。
听我母亲说,在那个年代,没有工作,是令人羞愧的,是让人抬不起头来的。我母亲年轻时已饱受过没有工作被人瞧不起的苦,所以,母亲绝对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将来找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踏进家门。
关于有没有工作这一点,时隔二十多年后,我母亲说,这在如今根本早已不是什么事,可当年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在我母亲眼里,她觉得两人都是清苦人家的孩子,倘若都没有工作在一起,日子该怎么过啊?当年,我大哥也做过一些抗争,甚至跪在我母亲面前。我母亲也只能哭泣。她埋怨自己的无能为力和父亲的早逝。她对大哥说,你要是找了云英,你的兄弟姐妹怎么办?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他们养活?
现在,我想,我完全理解我母亲当年把大哥和云英拆散的那份“坚定的残忍”。同时,我也对云英后来的一些际遇,有些伤怀。
云英被迫离开我大哥后,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神经错乱。后来,经过治疗,康复后没多久,就结婚了。隐约听说,只是在性格上,不再有从前少女时的那般开朗。
大哥1979年和云英分手后,二十多年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络。我母亲,这二十多年来,也从没有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间,说起大哥的这段往事。而我大哥,从他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里,更不会让人觉察到他内心里还有这样一段深藏的温柔。
大哥在开发区做生意的半年后,遇见了二十多年没见过的云英。云英在当地的小学,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老师。前年离婚,唯一的孩子都快二十岁了。
大哥和云英这半年里,陆续地见过几次面,除了感觉彼此都老了以外,感情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是大哥现在想离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大哥有没有恨过母亲,我能确定的是,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他对我母亲非常地好。
我母亲二十多年来,不提这些旧事,是因为她一直以为大哥早已经忘记了云英,一直生活得很幸福。母亲错了。我们都错了。正像大哥在电话里的那场对母亲隔了二十多年后的哭泣,他说,这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一天是感到幸福的,我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的。
母亲在电话里,给我说起这一切,情绪还是很激动,她说如果早知道这样,二十多年前,她也不会把云英赶走的。母亲希望我可以给大哥打个电话。后来,母亲在我的劝慰中,停止哭泣,就挂了电话。
去年的中秋,上海是阴天。是一个看不到月亮的中秋节。放下母亲的电话,我有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我在窗前,外面有隐约的夜雾。想起大哥,我忽然觉得这二十多年来,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茁壮成长的过程中,他却是天下最孤寂的一个男人。他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这种突如其来的内疚感,令我热泪盈眶。
我拿起电话,去拨大哥那个对我来说略显生疏的电话号码,我还不太能够确定自己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
但在那一刻,我只想对着电话听筒,好好地喊一声大哥。
外婆这样对你说过话吗
赵婕/文
冬天的黄昏,我去学前班接六岁的儿子。一进教室,他就过来亲我。对我的出现,他欢喜不尽。
我们各自都只是戴上一只手套,另外两只手互相牵着,体温就足够温暖。他走在绿化带的矮矮围墙上,就比我还高一些。
我们一直手拉手,乱蹦乱跳乱唱歌。我唱:“我的乖娃娃呀,我的好儿子呀。”他唱:“我的好妈妈呀,我的妈妈好呀。”
儿子突然停下来:“妈咪,外婆这样对你说过话吗?”
前面我和儿子说过很多话,他是指外婆说的什么话呢?我迷糊了一阵子。
“就是外婆叫过你乖娃娃吗?”
我停顿了一下:“没有。外婆不习惯这样说话。不过,外婆也很爱妈妈的。每个妈妈爱孩子的方式不一样。”
有时候,我会把儿子当一个小小的知己,告诉他一些“限制级”的事情。
有一天,他早上醒来,忽然流着眼泪对我说:“妈妈,我不原谅你,你道歉也没有用!”
“什么事?”我还颇镇定。
“你关过我黑屋子。”
“什么时候?”
“姥姥姥爷还有奶奶来的时候,我三岁的时候。”
“为什么?”我有点儿难过。
“我把瓜子壳混进瓜子里。”
想起来了。当时他太兴奋了,一直在家里捣乱,各种花样。怎么说都不听,忽然想起母婴杂志上的招儿,说是把孩子隔离现场几分钟,比如关进黑屋,可解决问题,且不像打骂一样给孩子留下伤害。我像一个聪明的傻瓜那样做了。
“外婆小时候还狠狠打过我呢,可比关黑屋子厉害多了。”
儿子立刻就对我挨打的事情十分关切了。我就讲了一点儿童年往事。
“她打伤你了吗?”
“没有,只是打疼了。不过,我原谅外婆了。”
“我不原谅!”儿子厉声说,眼睛涌满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