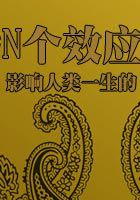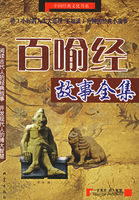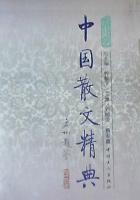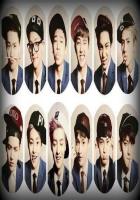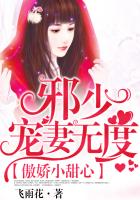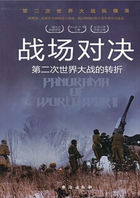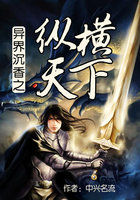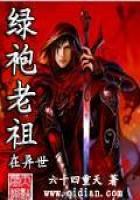正因为此,所以荀子主张礼要隆、法要重。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目征其末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对犯法的人不加以严惩,就不足以警戒,社会就会发生混乱;对犯法的人不处以刑罚,民心就不服,国家就不稳定。惩处刑罚应该根据法律进行,如果有现成的法律,就依法量刑;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就可以比照执行,“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在执行法治时,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当,“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相称,使犯法者当罚,社会才安定;刑罚与所犯的罪不相称,当罚不罚或罚不当罪,社会就会动乱。对于犯法的官吏,也要依法惩治。“正法以齐官”,这样,“百吏畏法循绳”,君主才能把自己的治国理念落到实处。这里荀子强调了法律上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民同罪同罚;一是法要重但要慎用,必须量罪而罚。
所以荀子提倡的“重法”并不是要实行严刑峻法。荀子力主慎用刑罚,对“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要让他们有谋生的职业并进行教化,如能够通过教育将其转化,就无须杀掉;而对于首恶分子以及与社会敌对的人则不能宽恕,就要处死,所谓“元恶不待教而诛”,“才行反时者死无赦”。他批评当时的统治者在对待百姓犯罪问题上的粗暴和草率,“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无辜也”⑾⑾。统治者贪得无厌地聚敛财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才造成“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的局面。荀子强烈反对以族论罪的株连制,批评那些不知教化百姓而乱施刑罚的君主,“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荀子认为,能否合理地利用法律与执行法律的统治者个人素质等有直接的关系,“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也就是说即使有法治,而没有合理利用法律的德治;有正确的法律,而没有合理执行法律的统治者,那么法律就不可能真正发挥治国作用。
荀子正确地认识到法治和德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二者都不可偏废,否则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在荀子的传播思想里,所言的“礼”具有“法”的意味,他常常把“礼”和“法”并举,言“礼”即为“法”,言“法”即为“礼”,两者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由于他提倡的“法”在“礼”包裹下,故而不得不最终把法治的希望寄托在“圣王”身上。这样,他对“圣王”的期望,从本质上说与他的“性恶论”形成明显的悖论:君主的人性也是恶的,中国古代的皇帝不是通过武力和篡位夺取政权,就是父死子继,哪能够培养出理想中的“圣王”?荀子还提出:“君子者,法之原也”,把法治能否传播和达到理想效果归结到“君子”身上,然而,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可能出现有效的机制来确保所选拔的官吏都是或者大部分是“君子”的。这样,“礼”的传播所要求维持传统秩序的规范,和“法”的传播所要求惩治暴贼和恶吏的律法之间产生了无法回避的矛盾,使荀子的传播思想处于两难选择,要么陷入历史循环的悖论,要么陷入一厢情愿的空想。因此,他的学生韩非大胆舍弃了荀子那容易为人所混淆的“礼”而直言“法”,明确提出“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
墨家与名家的传播思想
一、墨子“耳目之实”的传播思想
墨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出生何地常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又说他原是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墨翟可能出生在孔子死的前后,公元前478年左右;死在孟子生的前后,公元前392年左右。他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乎属于“士”阶层。但他又承认出身于自由贱民之治工艺者,传说还会制造五十石重车辖。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奔走于各诸侯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曾“学儒家之业,受孔子之术”,而自成一家之言。墨子的思想核心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个方面。墨子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身体力行,相传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曾“南游使卫”,宣传“蓄士”以备守御;曾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因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伐鲁未成;越王邀作官,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吾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墨翟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著作《墨子》中。
(一)重“事、实、利”和“言必立仪”
墨子传播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内向传播的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在《明鬼下》说: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见莫闻,则必以为无。就是说判断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否,不应该凭个人的臆想,而应该以众人的所闻所见为依据。提出了有关检验传播真实性的标准问题,这里排除了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以众人的耳目为基准,因而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他否定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传播思想,有其进步性。由此他认为圣人的认识能力的确高于一般人,原因在于他们“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从而他进一步否定孔子的天命观,说:
我所以知“命”之有与无者,以众人之耳目之情,知有与无。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
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批评孔子一方面教育人要学习,一方面又坚持天命观点,这就好比要人包起头来又要人去掉帽子一样,自相矛盾。
墨子的内向传播观点并不停留在用耳目、重视听上,他还提出了“谋”和“言”。如果说耳目、视听是受播过程,那么“谋”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思考,而“言”则是信息的反馈和新一轮的传播。为此他有一系列的论述:
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
[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谋”即思考,从古知今,以显推隐,由此及彼,是一种内向传播的推理过程,是感性认识的发展。“言”是人们认识的最直接表现,因此墨子认为有必要确立一个检验“言”正确性的标准——“立仪”。如果没有检验言论的客观标准,就会像在旋转的轮子上观测日影的东西方位一样没有了定准,也就不可能辨别是非得失和利害。对言语的检验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以历史记载中前人的间接经验(古者圣王之事)为依据,二是以广大群众的直接经验(百姓耳目之实)为依据,三是考察言语的实施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利益。
墨子对言语传播的检验,首先提出以“事”、“实”、“利”作为三条原则,进而提出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实施效果作为准绳。墨子言之“有本、有原、有用”的“三表”论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表达了经验主义的传播思想。虽然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提倡学习前人的经验,却迷信古人;而墨子认为学习古人要有所批判,所谓“古之善者则訹(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与孔子的传播思想完全不同。
墨子主张“言”不必迷信古人,而要看它能不能在未来的实践中体现实际效果,能不能具有预见性。《鲁问》记有这样一回事:
有一次,有一位叫彭轻生子的人对墨子说:“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墨子设问说:“假设你的父母在百里外的地方遭遇了危险,如果你能在一天之内赶到那里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你赶不及的话,可就危险了。现在这里有‘固车良马’,又有‘四隅之轮’的‘驽马’,你要赶去救你的父母,你准备选择哪一辆呢?”彭轻生子答复说:“‘固车良马’跑得快,当然乘这一辆去。”墨子随即便说:“既然这样,凭你已有的经验,知道哪一辆赶得及,哪一辆赶不及,岂不就了解了将来吗?怎的说未来的事不能预测呢?”
从墨子的“三表”法,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言语传播的基本观点:第一,从思想性看,墨子处处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前提。当然这不是说墨子志在创建今天意义上的人民世界,但说明他已经看到当时奴隶制国家的行将没落,为了争取奴隶解放和促进已经萌芽的新的社会的成长而已。
第二,从方法论说,墨子以人民大众所感觉着的存在为认识真理的准则,较之孔子的正名思想有很大程度的进步性。他不是从维护社会腐朽的立场出发,而充分体现追求社会进步的一面。
(二)求“取实予名”和“察类明故”
孔子把传播的基本概念——“名”定位在“知”的基础上,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墨子则把“名”定位在“实”的基础上。墨子针对孔子的“正名”说提出了“取实予名”的传播命题。
所谓“取实予名”,就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称的名称。墨子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即“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诸圣人所先为,人效名实。名不必实,实不必名。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不与大同,是有便谓焉也。以形貌名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名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
今瞽曰:“巨[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者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这里阐述了名(符号)与实(所指)的关系,名与实必须具有统一性。但有时候有名不一定有实,有实也不一定有名。如果石头是白的,剖开石头,里面也是白的。石头虽大,也必须确认它与别的大石头在大小上的差异,才能指称它。
以事物形貌命名,也得知道它是某物,然后才能知道它叫某物;不能以形貌命名的,即使不知道它是某物,但只要知道它叫某名就可以了。墨子又举例说,盲人所以不能区别地择取混在一起的白色和黑色,并非他们不知道黑和白的“名”,而是因为他们无从“取”。这里墨子提出了传播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传播的概念不在于“名”本身,而在于传播的“名”与所反映的“实”是否名副其实。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名”,只能根据具体的“实”来取舍;正确的认识不在于知道抽象的“名”,而必须依附于“实”。“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
“取实予名”,实际上探讨了语言符号与所指的关系,还强调了通过实行来对各种“言”进行检验。孔子认为,“言必行,行必果”是“小人”的哲学。墨翟则指出,凡立论不仅要符合实际的情况,还要身体力行地实践。他说: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不足以举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墨子严肃地指出,言论必须付诸实践,能够通过实践得到检验的就推行它,实践行不通的就不能推行它;否则就是“荡口”,是空洞的言论。
如何做到名副其实呢?墨子提出了“察类明故”的命题。同一传播概念往往存在着不同的内容,即同名而不同类。因此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看事物的实质。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古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而或仁不仁。然则不在古服古言也矣。”
判断一个人仁与不仁,不在于这个人表面的衣着和言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具体分析进行区别。又比如杀害无辜的人就是不道德,发动战争去杀害更多无辜的人,那就是不义的战争。但是战争有不同的“类”:其“故”在满足少数人的贪欲而进行掠夺性战争,就叫“攻”;其“故”在挫败对方的掠夺,以拯救国家和人民的,则叫“诛”。同是“战争”实不同“类”。墨子反对“攻”而赞成“诛”,他常在论辩中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由此他进一步说: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
这不仅是论辩的道理,也是传播的基本道理。“类”、“故”、“理”,从逻辑范畴提出的传播概念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类”要求对同“名”的客观事物进行类比分析和类推,以求正确把握;“故”要求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分析和研究其原因和结果;“理”要求掌握事物的内部规律,即决定取舍是非的依据。“取实予名”和“察类明故”是传播上的重要命题,它提示我们在传播活动中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考察,进行合理的分类,准确了解各类事物的同异、因果及其根据。
二、墨子“明是非之分”的传播思想
《墨子》一书对语言传播特别重视,在名实论基础上,墨子充分阐述了语言传播的功能和技巧,他强调语言传播具有论辩和进言的功能,并指出语言传播的“三法”。墨子从语用、语义、辩论、说服与修辞五个层面,作了详细论述。
(一)语言传播的功能——论辩
墨子把论辩当作语言传播的一种突出功能提出来,《墨子》对论辩学作了详尽而具体的概括,成为很有体系的观点。他说:
夫辩,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他认为论辩的作用就在于辩明是非,审视治乱,明确异同,考察名实,权衡利害,决断嫌疑。因此论辩的方法是要探求万物的各种现象,分清事物的各种类别,并通过言论的辨析,用名称来指述事物,用言语来表达思想,用理论来阐释原因,加以例证和推理。论辩的原则是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必须做到独立思考。
墨子对论辩有比较系统的见解:
1.论辩的目的是取胜于人,说服对方
墨子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不主张无谓的论辩,认为论辩必须分是非,争胜负,而胜利的必定属于正确的一方。所谓“当”,就是与事实相符合。这样便定出了一个论辩的客观标准。即此墨子与庄子不同,庄子也讲“辩”,但是庄子强调相对论的“反辩”,常以宇宙之宏观范畴与人的主观之心理定势来决是非。墨子对自己的论辩非常具有自信心。他曾说:
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击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他认为论辩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相信自己的论辩理论足以传播自己的思想。他说叫他放弃论辩,就像舍弃一年的收成却去拾别人遗弃的粟米一样!他坚信自己的论辩坚如磐石,别人的言论犹如蛋卵,以蛋卵击石,其结果可想而知。
2.论辩的效应是主动进言,推进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