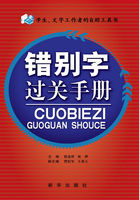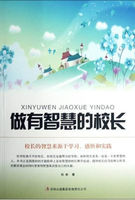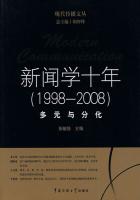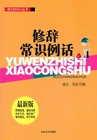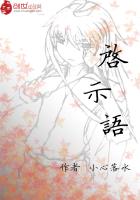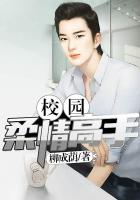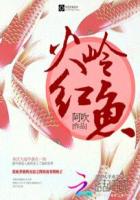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耳。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矣,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
这段文字,公孙龙运用了多重逻辑论证法来驳斥孔穿的言论:
(1)类推法。孔子把“楚人”与一般概念上的“人”区分开;公孙龙把“白马”与一般概念上的“马”区分开,但是孔穿却认同前者而反对后者,自相矛盾。
(2)假定法。孔穿既然修业儒学,自然应当认同孔子的观点,但如今又对此加以非难,自相矛盾。
(3)归谬法。公孙龙凭着“白马非马”而成名,孔穿却要求他放弃这一基本理论,那么公孙龙还能拿什么来教导孔穿呢?没有什么可教却声称向公孙龙求学,自相矛盾。
(4)推因法。孔穿表示要向公孙龙学习,因为承认自己的智力不及公孙龙,却反过来教公孙龙抛弃白马之说,那么等于显示自己的知识与学问高于公孙龙,高于公孙龙而又要向公孙龙学习,自相矛盾。
由此可见,公孙龙在传播活动中对概念的认识非常清晰,对概念的运用非常准确。那么作为公孙龙学说精华的“白马非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呢?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曰:“有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是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如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天下无马可乎?”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马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黑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业。”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与马也;异黄马与马,是以黄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辞也。以‘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耳。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白马’也。以‘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立论与“白马非马”一样著名的另一论断是“离坚白”。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脱离“物”的纯理论的传播概念。因为一般人在传播活动中总以耳目所视所听的现实作为基本概念,自然认为“白马”也是马。但公孙龙异乎一般人的认识,他认为“白”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概念,“白马”是两个概念的结合,已经不同于“白”也不同于“马”,故“白马”非“马”。马在现实认识里是一种食草性动物,四肢强健,擅长奔跑,等等,但这只是马的“形”,或称“貌”,亦即“物”。当我们把“马”从马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时,这个概念就不再存在于现实,而只存在于人的精神中。“白”的情况也一样,甚至要比“马”更为抽象。因为我们不能把“白”呈现于人前,它始终依附于其他具体事物方能呈现,在现实中找不到“白”,可见的只有白马、白羊、白布、白纸等等,“白”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同样道理,万物通有“白”,也通有“坚”,它们只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未必固定成为“石”的内涵,只能依附于其他任何“物”而存在。所以“白”也好,“坚”也好,都是可以离“石”而独立的。
公孙龙在《指物论》里对概念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任何事物都必须有一个“名”,“名”界定事物,但“名”本身不被界定,即“名”已经不是被它界定的“物”了。用现代符号学鼻祖索绪尔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名”就是符号,符号包含着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如语言或文字形式;所指就是该“名”所对应的抽象的“意义”,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它们结合一起的对应“物”是客观事象。所以“马”是个符号,它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马,只是反映现实中的客体——马的高度抽象物——无色、无形、无性的“马”,而这种“马”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公孙龙在中国传播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名”、“物”与“指”的严格区分。
(二)“审其名实”
公孙龙的《名实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传播学论文。他从逻辑角度指出,天地及其所出产的一切,都是客观事物,可称为“物”;客观事物跟构成客观事物的各种元素恰如其分的结合,就形成事物的本体,称为“实”。有形有实的事物本体总是占有一定的空间,这叫做“位”。当事物的本体脱离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就失去了原来的“位”,也就不成其为“实”。只有当事物的本体处在它本来的时间和空间的位置上时,才可以得到确定的命名。所以事物的“名”必须与“实”相符合。
公孙龙是这样论述的:
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而位其所位焉,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故彼彼止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一当而当,正也。
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切此且彼,不可。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
“名”和“实”既是逻辑概念的中心对象,也是传播概念的核心信息。公孙龙认为名与实是并存而相对的,有其实方有其名,有其名必有其实,不会有名而非其实,也不会有其实而无其名。而且他强调,物体的名称确当,那么该名称就应该专属,所谓“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如果名称不确当,这一事物的称谓就不能通行,名跟实的关系会发生混乱,所谓“不当而当,乱也”。名称应该专属,用确当的称谓去命名确当的事物,这就叫名实相副。
名实相称谓之“当”,谓之“正”;名实相背谓之“悖”,谓之“乱”。名和实之间处于一种变化状态的平衡,“实”变化了,“名”也得变化;“名”变了,“实”也就不是原来的“实”了。比如以“牛羊”为例:
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曰:何哉?曰: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
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
意思是:说羊牛因齿之“有”与“无”而不同,这不对,应该是类同;说羊牛因角之同俱有而相同,更不对,因为它们类不同。既然这样,羊牛有不同有相同,公孙龙子·通变论.庞朴学.公孙龙子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2虽有同但实际不同,因而认为羊牛结合可以成为“马”,则更错误。羊牛和马比较,更无相同之处,因为“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怎么可以合而为马呢?所以说“羊合牛非马”。
在公孙龙看来,万物是由“物”的要素构成的,各个要素本身是不变的,要素可以合成,但不能成为新要素。马的要素不同于羊牛两要素,所以羊牛两要素不能合而为马的要素。公孙龙进一步说:“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牛羊二。是而羊而牛,非马也。”“不二”指是独立的一要素,不是二要素,羊牛则有二要素,而要素本身都不变,故无法有马的一要素。羊是羊,牛是牛,马是马,羊牛不能成为马,这就是名实相副。
公孙龙在《名实论》里,不仅给“物”下定义,给“名”定位,更了不起的是他还表明了一个极为可贵的传播思想:“实”决定“名”,“名”随“实”变。公孙龙坚持这一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为了“正名实而化天下”,因此也特别强调地提出“审名实,慎所谓”的理论。这是公孙龙非常成熟的学术观念,也是他传播思想的全部要旨之所在。
公孙龙在名实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超越了墨子的“取名予实”说,但论辩问题上并没有独特的发展,虽然也提出了关于论辩的十三条论证,但主要探讨了论辩守则的问题。在桓宽《盐铁论》中引到公孙龙一个重要的思想:“论之为道辩,故不可以不属意,属意相宽,相宽其归争,争而不让,则入于鄙。”指出论辩的目的是为了说清是非,所以不可以不留意对方的论点;要留意就得互相宽容,互相宽容就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议;如果进行无谓的争议,就不免流于粗鲁和卑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公孙龙子》原有14篇,证明汉代时《公孙龙子》全书是完整的,那么西汉宣帝时桓宽所著的《盐铁论》中所引公孙龙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台湾学者关绍箕说,“足见公孙龙主张君子之争,而反对意气之争;毕竟辩论是一种理智活动,是一个厘清是非的传播行为”。
公孙龙与当时的一大批论辩家一样,都涉及“名”的概念和“辩”的技巧,而且都明白地揭露瞬时运动的矛盾,但采取强行调和的态度,这可能与当时道家学说流行(所谓“黄老之学”)的大环境有关(惠施就有“合同异”的倾向,今人或褒为“辩证思维”)。名家和墨家不仅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在思想上具有部分一致性。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时代,赋予了自由争鸣的学术空气,从而出现了名家独特的“无限”论。但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人们更急于寻求解决严酷社会问题的办法,名家学说无法获得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他们的学问轻则被讥为无用,重则被视为“诬悖”,“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为天下之长患”。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加强,名家最终在战国末期走向衰亡,他们的学术也很快废绝了。在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更不存在这种思潮复活的土壤。中国古代对解决无限问题中的矛盾,以后没有再出现有突破性的成果。
黄老学与庄子的传播思想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道家的得名,可能来自于老子的《道德经》。道家人物众多,典籍丰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风格的一帜。
根据《艺文志》之《诸子略》所引,道家37家,著作有993篇之多。但大多亡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及著述有《老子》、《庄子》、《列子》、《皇帝四经》、《管子》和《尹文子》等。
一、老子“大辩若讷”的传播思想
老子原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当过周王朝的王家图书馆官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见周室衰败,弃官而去,到了城关,关长尹喜不让出关,一定要他把自己的学问记录下来才放行。于是李耳就把自己的思想见解著录成书,为5000余言分上下篇,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道德经》。
老子的哲学体系包容万象,涵盖了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虽然老子不像孔子是一位传播大家,但是,他的《老子》一书还是可以发现有不少言论反映出他的传播思想。
(一)“唯德是从”的传播思想
在政治传播和思想传播方面,老子一再强调“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思是君王如果能掌握“道”的规律,就可以使万物因感化而自然驯服。在老子的理论系统里,“道”是先天地发生的,它超然独处,又永恒无变;它虽然永恒无变,但能用它来应付万变。因此,在老子的政治传播思想里,“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只代表一种控制着整个思想的原则,真正的传播内容则应该是“德”,“德”是“道”的部分,也是“道”的具体化。所以老子曾反复说: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要发扬“德”的思想,要使“德”成为传播的内涵,那么首先要遵循“道”的准则。因为“道”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又称为“常道”;同理,符合“道”准则的“德”也是永恒不变的,故又称为“常德”。
如果一种思想,在传播中能坚持一贯,保持始终,那么它日益积累而渐多,就能在精神世界里真正实现“道”,即所谓“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就是“道”。如果把“道”传播到具体的物质世界中去,就成为有形的“物”,并化为日常生活中有用的“器”。所以老子又说,“朴散则为器”。“散”就是传播。
(二)“名可名,非常名”的传播思想
老子在言语传播方面有一组很严格的概念,即“常道”和“常名”。“常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范畴”,“常名”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通称”。范畴是一切事物最具有基本意义的类型或范围,在老子看来“常道”是无法用言语说得清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通称是事物最具有一般意义的命名,如各种各样事物的“常名”即客观存在之“物”,它是最接近于范畴的名物概念。因此老子有一句名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可以说得出来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为了说明这个在言语传播活动中理论性很强的抽象概念,他举了例子:把天地混沌的现象叫做“无”(不是现代汉语有与无的无,是作为宇宙的对立面提出的概念),把生育万物的宇宙叫做“有”。那么,“常无”这个名称是为了方便研究天地混沌运行规律而采用的符号,“常有”这个名称则是为了方便研究宇宙运行规律而采用的符号。这两个符号其实质是,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给予的命名,它们共同的名称可以叫“玄”。但是还有一个比宇宙之“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叫“玄之又玄”,它才是宇宙和万物最最基本的规律。
老子实际提出了一个传播学上很严肃的问题,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众多不可概念化的物象或事象,因而一切言语传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语义”解释的制约和“语义”传播的局限。这里提到的“语义”不能按人们经验的理解去接受,它是通向纯粹思维的对应物,由于古人尚无精确的术语认识,老子的“玄”常使今人不知所云。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最清虚的思维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的有意识的对应物”,这似乎是对“常道”、“常名”、“常无”、“常有”等,以及对“玄”的很好注释。
(三)“不言之教”的传播思想
老子对言语传播是持批判态度的,一方面他肯定语言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在取信于人上的局限性。这方面他说了很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