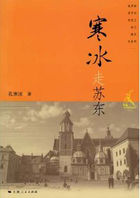西陵峡(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西起今湖北巴东县之官渡口,东至今湖北宜昌之南津关,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全长二百五六十里,中间有六七十里的宽谷相隔,分为东西两段。峡谷中峰峦夹江壁立,峻岭悬崖横空,险滩星罗棋布,江流曲折回环;峡内奇石嶙峋,飞泉垂练,苍藤古树,翳天蔽日,风光明丽,雄伟壮观。
西陵峡的出口处,便是素有“雄当蜀道,巍镇荆门”的南津关(南津关:关隘名,故址在今湖北宜昌西的西陵峡出口处。)。江面在此处宽仅七八十丈,江岸狭束,形势险要,江水如剑,咆哮激湍。待到长江破关而出之后,水势陡然转平,江面豁然开朗,猛增到七八百丈宽。在南津关上放眼望去,关内群峰竞秀,千岚争奇,礁石林立,险滩密布,江岸蜿蜒,波涛汹涌;关外天高地阔,开朗明丽,巨川缓流,舟楫穿梭,田畴依偎,绿原如茵。
吴国的军事重镇西陵(西陵:城邑名,故址在今湖北宜昌。),就坐落在南津关下游十几里处的长江北岸。西陵原名夷陵,战国时就是楚国的江防重地,秦将白起领兵伐楚时曾在此处进行过激战,把这里夷为平地。西汉末年王莽篡国后曾将夷陵改名为居利,黄武元年(222)孙权又改其名为西陵。
在西陵的西面,有一小洲突出于江中。相传在古时曾有青龙、白龙化为勇士,驾驶着神舟载木材出三峡。在此处遭到水妖的阻拦。二勇士与水妖展开了激战,神舟被搁浅在了江边,形成了一个小洲,因而被称为搁洲,又日郭洲(郭洲:即今湖北宜昌之葛洲坝。此洲紧邻长江北岸,突起江中,形成一座孤岛。)。小洲长约二里,宽约一里,像是一只从西陵城伸出的巨掌,直指南津关,随时都准备击打破关而出的入侵者。
永安二年(259)孙休拜陆抗为镇军将军,命他假节(假节:暂时授以符节。三国时期,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往往加假节、持节、使持节等名号,以示其权力之大小。东下,北御魏军南进。五年来,陆抗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一只眼睛注视着西边的蜀国,一只眼睛紧盯着北边的魏国,沿江河布防,据险要而守,严加戒备,没有给魏国和蜀国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保证了吴国西境的安全,赢得了孙休的赏识和信赖。)出镇西陵,都督三峡及江汉地区诸军事,西防蜀军去年秋季,风云突变,魏国挥师伐蜀,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僵局,也打乱了江汉地区的军事平衡。陆抗随机应变,把绝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用到了魏蜀交战方面,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变化,并审时度势,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和军事部署。所幸的是,吴主孙休对陆抗言听计从,使陆抗的军事意图能得以实施。
可是,令陆抗深为惊诧的是,罗宪竟然想出了那么一个撞船的绝招,不仅使吴军损失了大批的将士和战船,而且步协也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此,陆抗一边让步阐护送着步协回建业治伤,一边重新寻找着夺取夔门的办法。
随着巴蜀大地降雨逐渐增多,江水也在不断上涨,流水变得更为急湍。时令不等人,再拖延下去,长江就要进入洪水季节了,在三峡内行船将更为困难,大军要溯流而上去进攻夔门就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甚至会使他抢占巴东的作战计划泡汤!尽管他已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抢在洪水到来之前挥师西进,才有可能夺取夔门,进而占据巴东,实现他的战略构想;尽管他属下还有足够的水军和战船可供使用,只要调整好作战部署,还能冲过三峡,占据巴东。然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则必须得到吴主孙休的允准,他不敢自作主张,擅自引兵西进。
近些天来,陆抗一面向孙休连上三表,请求率军去攻取夔门;一面加紧整顿水军,以便在得到孙休的允准后能立即行动。不知是孙休害怕陆抗重蹈步协的覆辙,大损水军战船,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军事实力变得更加不利;还是孙休被迫放弃了原先的战略计划,降格以求,要把有限的兵力用于自守保境,以换取暂时的安宁。所以,陆抗至今仍旧没有接到孙休允准他率军西进的诏书。
时光在不断地流逝,江水在逐渐地上涨,陆抗心急如焚,望眼欲穿。这一日,他再次来到江边,面对着滔滔东下的江水,默默地伫立着,久久地沉思着,像根立在岸边的木头桩子一般,大半个上午一动未动,一语未发。
也不知过了多久,太阳从阴云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耀眼的光芒把陆抗从沉思中刺醒。他手搭在额头上,朝着下游的江面眺望了片刻,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正要离开江边,忽听有人高喊:“镇军将军!”他循声望去,只见从上游郭洲方向驶来一只快船,正在向他靠拢过来。
转眼工夫,那只顺流而下的快船已来到了岸边。紧接着,一位身手矫健的大汉仿佛虎跃山涧似的,嗖地一下从船上蹿了下来,跳出两丈多远,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陆抗的面前。
来者约有三十岁左右,身长八尺有余,豹头虎背,狼腰猿臂,与瘦弱斯文的陆抗相比,更显得威猛而健壮。此人便是水军头领吾彦。
吾彦字士则,出身寒微,年轻时以捕鱼打柴为生。他体魄强壮,膂力绝群,翻山如履平地,入水好似蛟龙,在山上打柴时曾打死过一只金钱豹,在家乡很有威名。后来,他投身到陆抗帐下,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由于他作战勇敢,且颇具将才,深得陆抗的赏识。陆抗欲破例擢升他为将军,但又怕众将不服,于是在一次大会诸将时,暗中使人佯装疯癫,狂舞着大刀闯入帐中。那些毫无戒备且赤手空拳的将领都大惊失色,皆离席躲避。惟有在帐中为众将斟酒的吾彦毫无惧色,顺手操起了一个几案,与那持刀“狂徒”进行搏斗,并当场将其制服。在场众将皆被吾彦临危不惧和高超的武艺所折服,纷纷请求陆抗提拔吾彦为将军……
吾彦被提拔为将军后,果然不负众望。他治军有方,军纪严明,使他统领的兵马成为陆抗属下的主力,他也成为陆抗的得力干将。步协、步阐兄弟从夔门大败而回后,陆抗便命吾彦统领水军,准备再次去夺取夔门。
吾彦一见到陆抗,就急切地说:“镇军将军,江水昨夜又上涨了一尺有余。若照此速度再涨下去,要不了多久,三峡内便难以行船。”
“此事我岂能不知。”陆抗望着那浩浩荡荡的江水,若有所思地问,“水军与战船如何?”
吾彦响亮地回答:“按照镇军将军之令,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一声令下,立即便可起锚开船!”
“嗯一一”陆抗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吾彦瞧着不动声色的陆抗,焦急地说:“水火无情,时不我待。我军此时如不大举西进,待到洪水季节,只怕是欲进而不能矣!”
“此事我岂能不知……”陆抗欲言又止,再次手搭凉棚,向着下游方向凝望着。突然。有一只插着红色三角旗的小船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使他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他睁大双眼,仔细地眺望着那只劈波斩浪、溯流而上的小船,自言自语道:“去建业送表之人回来矣,但不知陛下是否……”
吾彦闻听此言,也扭脸向下游望去.发现了那只专门往返于西陵与建业之间的信船,不由得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说:“镇军将军在此稍候,末将前去迎接圣上之诏书!”说罢,又嗖地一下从岸上蹿回到那只快船之上,朝着下游疾驶而去。
工夫不大,吾彦手捧着孙休的诏书又重新回到了陆抗的身边。陆抗急忙展开诏书。读了一遍,提高了声调说:“吾将军,圣上已允准我军西进之请。汝立即去整顿水军战船,午时起锚开船,直奔巫城。不得有误!”
春尽夏来,天气逐渐变热,江水不断上涨,夔门之外的滟预瓘大部分被滚滚的江水所吞没,只有碾盘大的顶部还露出水面,像是一只漂浮在江心的大葫芦。在汹涌的波涛中摇荡。
自从罗宪用撞船的办法击溃了步协、步阐兄弟率领的吴国水军后,夔门暂时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只有那翻滚不息的江水。日夜不停地撞击着赤甲、白盐二山,激起高高的浪花,发出阵阵的轰鸣,以此来警告和提醒着过往的舟船。
罗宪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击溃了吴国的两万水军。这一辉煌的战果,大大鼓舞了永安的守军,也大大提高了罗宪的威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决心跟随着罗宪固守夔门。
创造了这一水战奇迹的罗宪,却没有陶醉在这巨大的胜利之中,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清楚地知道: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夔门和三峡对于吴国安全的重要性,吴国绝不会因一战失利而放弃夺取夔门、锁住三峡、卡断魏军东进之路的计划,给国家留下无可补救的后患;他们肯定要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夺夔门!同时,他也明白:此战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出奇制胜,打了吴国水军一个猝不及防;善于水战、训练有素的吴国水军.在清醒过来以后,定会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免重蹈覆辙;因而,此战只是争夺夔门的开始,而不是保卫夔门的结束,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知己而又知彼的罗宪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了如指掌:如果没有外援,仅凭他手中的这点兵将,无论如何是保不住夔门的;总有一天,将士们要全部捐躯,夔门也将落入吴军之手!为此,他除了派出多名暗探严密监视巫城、秭归一带吴军的举动外,还遣使前往成都求援,请求魏军派遣兵将驰援夔门。
近些天来,尽管各处的暗探一再报告:巫城、秭归一带的吴军并无大举西进的迹象,但罗宪紧绷着的心弦始终没有松弛,反而是随着江水的不断上涨越绷越紧。这几天他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三峡内的平静并不是真正的平静,而是大战前的寂静;吴军一定要抢在洪水季节之前,再次来争夺夔门;江水每上涨一尺,吴军大举西进的日子也就逼近一天。
还有一个令罗宪提心吊胆的原因是:派往成都求援的信使至今尚未返回,救兵更是杳无踪影。这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结果只有一个:近期内他只能是孤军奋战,独自面对吴军的进攻!
罗宪手中的水军与强大的吴国水军相比,众寡悬殊,强弱悬殊,根本无法进行直接交战。他惟一可以依赖的就是险恶的夔门和汹涌的江流,他只能重施故伎,用撞船的办法与吴军进行抗衡,固守待援。因战船的数量有限,用一只少一只,维持不了几天,打造又来不及。所以,他只能命令兵士们到江边的山上砍伐树木,捆扎木筏代替船只。多亏了兵士们乐于出力卖命,十几天的工夫,就把附近山上可用的树木砍伐一空,江边上已瓘满粗长的树木,并捆扎出了不少木筏。
这一日,罗宪又来到江边,看望那些搬运树木、捆扎木筏的兵士。那些汗流浃背的兵士见罗宪来看望他们,大受感动,干得更加卖劲。罗宪也大为感动。竞忍不住亲自动手与兵士们一块干起来。
罗宪与兵士们边干边聊,正干得来劲,聊得热乎,参军杨宗匆匆忙忙地跑来,把罗宪拉到一个僻静无人处,低声地说:“据巫城、秭归暗探来报:吴国三万水军、两千只战船已抵达巫城,不日就将进军夔门。”
罗宪不禁一怔,神色紧张地问:“率军之将为何人?”
杨宗连忙回答:“镇军将军陆抗。”
“陆抗!”罗宪大惊失色,瞪大眼睛望着夔门,惊慌不安地说,“只怕此番夔门危矣!”
杨宗瞅着罗宪惊愕的面孔,诧异地问:“太守为何出此不祥之语?”
“唉——”罗宪长叹了一声,神色由紧张变为冷峻,惴惴不安地说:“陆抗颇似其父陆逊,智谋超群,极善用兵,吴将之中无有出其右者,非步协、步阐兄弟可比!吴国此次派他率军前来攻夺夔门,可见是志在必得。”
“太守不必过于担忧。”杨宗指着江边瓘积如山的树木和排出老远的木筏、战船,宽慰着罗宪,“陆抗智谋再高,但也无法飞过瞿塘峡与夔门去。只要我军按照老办法,用战船、木筏与树木去撞击逆水而上之吴军,他们就无法通过瞿塘峡,就只能望着夔门兴叹。”
“我等可想出撞船之法,陆抗亦可思出避撞之计。此法只可暂救一时之急,但却非长久之计。”罗宪仍旧凝视着夔门,忧心忡忡地说,“再者,江水滔滔不绝,战船、木筏与树木却是有限,一旦用尽,我军将何以阻挡吴军?”
“如今已是夏初,再过一月,洪水就会到来。”杨宗不以为然地说,“只要洪水一来,瞿塘峡内江流如泻,巨浪滔天,船只根本无法通行,还何患吴军进攻!”
“只怕是等不到洪水到来,夔门就已为吴军所得。”罗宪悲观地低语了一句,把目光从夔门上收回来,转移到了上游八阵图垒方向,极目远眺了一会,再次低语道,“派往成都之信使为何至今还未返回?”
“或许……”杨宗想说些什么,但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妥,把话咽了回去。
“如今我军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罗宪悲哀地自语了几句,低头沉思了良久,才抬起头来,严厉地命令杨宗,“杨参军,汝在江边支起军帐。从今日起。我搬到江边居住,与夔门共存亡!”
杨宗迟疑了一下,犹犹豫豫地说:“江边潮湿风大,不宜久居。太守还是回永安城居住,末将愿代太守在江边守候,有事随时向太守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