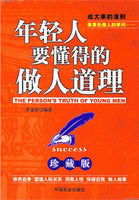——[瑞典]雅·瑟德尔贝里
有一天,两个非常年轻的人——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坐在一直伸进水里的湖岬的石板上,湖水汩汩地拍打着他们的双脚。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两人都瞧着西沉的落日,陷入沉思。
小伙子想:“我真想吻她。”他抬头看看她的嘴唇,立刻就使他想到那嘴唇的样儿就像是意味着要他去吻。当然,他在和别的姑娘恋爱,而且,她也并不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但是像眼前这样一位姑娘,他确实从来没有吻过,因为她是一个理想的化身,一颗天上的明星。对一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女性,又能怎么办呢?
姑娘想:“我真想要他吻。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有机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我对他根本不屑一顾。我会站起来,把身上的裙子裹得紧紧的,非常冷淡地、轻蔑地白他一眼,然后挺起腰杆,镇静地走开,而且并不显示任何不必要的慌张。不过眼下为了不让他猜出自己的思想活动,所以我应轻声慢语地问他一声:‘你认为,这以后生活就与从前不一样了么?’”
他想:“如果我回答一声符合她的心意,她也许就更容易让我吻他了。”但是他不能肯定地记得,过去在另一种情况之下,对于同一个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他生怕自相矛盾。因此,他注视着她的眼睛,回答说:“我有时候这么想。”
她对这样的回答很高兴。
她想:“最低限度,我喜欢他的头发,也喜欢他的前额。颇有点美中不足的是,首先,他的鼻子长得太丑了,其次,他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学生,只是一个为通过毕业考试而读书的学生。总体来说,他并不是使我的女友们感到烦恼的那一类人物。”
他想:“这会儿我肯定可以吻她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怕得要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吻过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他也不知道这一吻是否带有危险性,因为她父亲是这个小城市的市长,而且她父亲就在离这儿不远地方的吊床上睡觉。
她想:“要是他吻我,我想我最好是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接着她又想:“可是他干吗不吻我呢?难道说我是个丑八怪,根本不讨男人欢喜?”
她朝水面上探着身子,想看看自个儿映在水中的形象,但是她一无所获,荡漾的微波把她在水中的影子打得粉碎。
她又想:“要是他吻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她只被男人吻过一次,那是在城市大饭店舞会以后,被一位酒气熏天、烟臭扑鼻的中尉吻的。在接吻时,她几乎没有什么快感,尽管他是一位中尉。要是他不是中尉的话,她真不情愿让他吻她。除此以外,她恨他。因为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向她献过殷勤,也根本没有对她表示感兴趣。
他们两人就这样坐着,各自揣摩着自己的心事。
最后一缕光线也消失在山那边,天色渐暗。
他想:“尽管夕阳夕下,夜色降临,而她仍然愿意和我坐在一起,这表明她也许不会太反对我吻她。”
于是,他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她的脖子。
对这样的轻举妄动,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她原先以为他仅仅是吻她,不会动手动脚,那样一来,她就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就像公主似的抽身就走。但是对他这个举动,她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当然,她也想对他生气,但是她又不想失去这次被吻的机会。因此,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
紧接着,他吻了她。
这一吻比她原先想像中的还要微妙。她觉得自己渐渐脸色发白,周身无力。这当儿,她根本没想到要给他一记耳光,她根本也不记得他只是一个为了毕业考试而读书的学生。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但是,他却想起一位笃信宗教的医生所写的一本《女性的性生活》书中的一段文字:“必须预防夫妻之间的拥抱受色欲的支配。”因此,他想,这个预防很难实施,因为即使是一次亲吻,就使人感到灵魂的颤动。
皓月东升,两个年轻人仍旧坐在那儿,相互吻着。
她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一看见你,就爱上你了。”
于是他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惟一的爱人。”
在工厂爆炸时,小杜果的妈妈被炸死了,不知情的小杜果此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阿依色奶奶和玛丽阿姨的关怀。工厂再次发生了爆炸,一直没见到妈妈的小杜果突然明白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