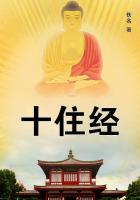“滚,滚开,颜峰你给我滚开!”随着一阵惊怒交加的呵斥,西皇崇梓胡乱挥舞着雪藕般的双臂,猛地睁开了眼睛。
静室外的天色已是微明,夜晚给天墉城覆盖的冰壳正在不断融化。然而即使是这并不炫目的天光,也刺得崇梓重新闭上了双眼。
外间的渐函,已经不知何时离开了。
支撑着从榻上坐起,崇梓咬着牙关忍过强烈的眩晕,这才慢慢调整紊乱的呼吸,以求让自己看上去依旧庄重威严。
可是,无论她怎样克制,这个数十年来生杀予夺铁血专断的女皇,此刻依然忍不住像只受惊的猫一样,睁大警惕的眼睛扫过自己身周每一寸空气。就仿佛,某个无形的人正躲藏在那里,充满恶毒地狠狠盯着她。不不,他并不是躲藏在空气里,他分明就躲藏在她自己的身体里!
一念及此,西皇猛地从榻上跳起,手指下意识地抠住了自己的胸口。是的,他就在她的身体里,潜伏在她的每一寸骨头,每一滴鲜血、每一根毛发里,难怪她一直无法摆脱他!
颜峰!
脑海中又冒出这个名字,西皇猛地咬紧了满口细密的白牙。
“是你先对不起我,又怎能怨恨我无情?”站在权力巅峰的女人即使病入膏肓,依旧不改强势,“就算你还活着,我也可以再杀死你一次!总有一天,我要找到你的尸体,把你烧成飞灰!”
然而没有人回答她心底的咒骂,静室里安静得甚至可以听见灰尘在光线中飞舞的声音,就好像颜峰真的变成飞灰,充斥在她身边的空气中,不断通过呼吸进入她的身体。
无声地对峙了好一阵,崇梓终于放松了紧绷的身体,颓然坐回木榻上,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颅,感觉到全身又是冷汗涔涔。
几个月来,每天她都经历着这样无影无形的折磨,那个早已死去的男人如影随形地跟着她,睁着他恶毒的眼睛折磨着她的身体和灵魂。
她知道,他要斩断她的筋,搅碎她的骨,抽干她的血,吸尽她的髓,而他很快就会成功了!
她试过所有的法术,服过所有的丹药,却无论如何无法将那个男人从身体里驱赶出去。他就像她骨中的骨,血中的血,早已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世上又有哪一种法术或丹药可以把自己从自己的身体里剥离出去?
“我们曾经发过誓要永远在一起,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她仿佛看到,他就站在埋葬着他尸骨的珙桐树下,俊美的脸上露出阴鸷的笑意,胸口被她一剑贯穿的地方仍在滴着鲜血,“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下手啊,以至于我宁肯放弃神人高贵的灵魂,将自己变成尸蛊,这样我们就能同生共死水乳交融了,哈哈哈!”
“你骗人,尸蛊虽然阴毒无比,却只有进入人体内才会有用,可你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你根本不可能害得了我!”
尽管不断提醒自己,巨大的恐慌还是像昆仑山一样无时无刻压迫着崇梓,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如今已是到了稍一集中精力就头痛欲裂的地步,处理政务根本力不从心。
而自从她惊异地发现珙桐树下再没有颜峰被掩埋的尸身后,扰人心智的梦游之症就如同附骨之疽般蚕食掉了她的冷静和理智。
只要查不出颜峰尸体的去向,总有一天,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西皇崇梓,其实是一个徘徊在清醒与崩溃之间的疯子。
所以,她不得不安排才十三岁的渐函仓促与神农国皇子定亲,并提前参与政事,而让女儿将那个心仪的溟妖带来,也是对未来西皇决断力和应变力的一个考验。
身体里的阴影暂且退散,西皇屈伸了一下自己苍白的手指,紧闭的嘴角抿出一道深刻而冷硬的细纹——实际上,无论渐函会如何庇护那个溟妖,都无法改变那个溟妖的命运。
因为西皇已经决定,当那个迷惑人心的溟妖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是他的死期。
这是在将权力移交给皇太公主之前,西皇必须尽快完成的事。
因为在她前途未卜之际,绝不能在女儿身边留下任何一个可能致命的隐患,而且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抉择和磨炼,女儿才有资格和历代西皇一样站在权力的巅峰。
历代西皇以女子之身牢牢掌控昆仑全境,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她们能够锻造出连男子都无法比拟的存在——铁的血和铁的意志。
所以当十多年前,身为秘密情人的颜峰想要阻挠她与神农国联姻的计划时,她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他,而且还——如果说崇梓从颜峰这件事中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这次处置渐函带来的溟妖时,一定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不再给他任何一点贻害和报复的机会。
“陛下。”一个声音忽然在静室外轻轻响起,如同清晨一声婉转悦耳的鸟鸣。
崇梓没有出声,依旧闭着眼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虽然知道自己日暮途穷,但一生好强的西皇并不愿意自己的病态落入他人眼中,哪怕是自己的贴身侍女。
想是熟悉西皇的脾气,外面等候的人善解人意地安静下去。直到良久以后,崇梓轻咳一声,那轻柔动听的声音才再度响起:“奴婢伺候陛下。”
“是秋奴吗?进来吧。”崇梓不动声色地坐在榻边,看着掀开帘子走进来的侍女。自从病后,西皇就只命春夏秋冬四婢每日轮流伺候洗漱,而这一日,恰好轮到刚从神农国出使归来的秋奴。
谦卑地垂着头,秋奴将西皇洗漱晨妆的用具一一捧进屋内,然后根据崇梓的习惯,先为她奉上一杯阆风巅上万年玄冰所化的天水茶,这才将呕丝之野出产的丝绒面巾泡入缂丝莲头紫金盆中,拧干了双手奉到崇梓面前。
昆仑山的万年玄冰至阴至寒,用它泡制的茶水沁人心脾,对被噩梦折磨了一夜的崇梓而言更是如同甘露。她一口气饮完了杯中茶水,接过秋奴奉上的面巾擦了把脸,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些许愉悦的表情。
见西皇已走到蒲团上坐下,秋奴熟稔地在崇梓面前支起一面铜镜,然后跪在崇梓身侧,开始为她梳头。
感觉到象牙梳子轻柔地在发丝间穿梭,崇梓从铜镜内看着身后侍女娴静温婉的脸,心中一动,忽然轻声唤了一声:“秋奴。”
“奴婢在。”秋奴似乎被西皇这句突如其来的呼唤吓了一跳,手一抖差点将梳子掉在地上,“陛下有何吩咐?”
“难得你这些年来尽心尽力地伺候我。”崇梓的眼神幽深如潭,一瞬不瞬地盯着镜中侍女。
“能伺候陛下是奴婢的福分。”秋奴赶紧回答。
“若是以后让你伺候皇太公主呢?”崇梓仍旧盯着她的眼睛,锐利的目光直刺入秋奴的内心。
“奴婢必将如伺候陛下一样尽心伺候公主。”秋奴毫不躲避崇梓的目光,温顺地回答。
崇梓满意地点了点头,确实,这么多年来,每当她用读心术探查秋奴的内心,所看到的只有彻头彻尾的忠诚和顺服。于是她微微放松了紧绷的肩背,微笑着对这忠心的侍女道:“明天是朝会,届时我会颁旨,封你为天墉城总管。”
天墉城总管管理偌大的昆仑皇城,可以说是西皇治家第一人,地位尊崇,权力极大,以秋奴双十年纪担任此职,不可谓不皇恩浩荡。
然而崇梓说完这句话后,却并未听到任何感恩叩谢之声,身后持着象牙梳子的侍女只是一片静默。
“怎么了?”崇梓猜测秋奴是被这天大的恩典惊得傻了,倒也不怪罪她的失礼,脸上依然保持着笑意。
“只是天墉城的总管吗?”秋奴缓缓地开口,声音清冷得仿佛打在玉砖地上的冰粒。
崇梓一惊,猛地觉察到镜子中侍女的眼神已经变了。她努力想要再度运起读心术,却发现自己的肌肉、筋络和骨骼一瞬间都僵化得如同顽石,竟是一丝灵力也无法调动起来了!
“真是吝啬呢,只给个区区总管的职位就想将亲生女儿打发了。”秋奴笑了笑,手中的梳子依然一下一下地梳理着崇梓的长发。
“你……”仿佛晴天霹雳,崇梓好半天才费力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你知道了什么?”
“全部。”秋奴挑起崇梓一缕长发,开始像往常一样为她绾起盘云髻,“包括被你强行抹去的七岁前的记忆。”
“谁告诉你的?”崇梓的语气微微有些慌乱。她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自认为世上读心术第一人的自己,竟然从未看清过身边这个女孩的真实想法!
难道说,秋奴的读心术竟然胜过了自己,那么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岂不是正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秋奴的面前?
“母亲到现在对女儿还是这种颐指气使的口气。”秋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仿佛一个对母亲撒娇乞怜的小女孩,“母亲难道就不肯唤一唤我的名字‘渐幽,渐幽……’我真是想听啊。”
“渐幽?”西皇冷笑,“从来就没有这个人!你的名字,只是叫秋奴!”
“是啊,在你心目中我只是秋奴,连名字都像是编号一样的奴婢。”秋奴一丝不苟地继续为崇梓梳着式样繁复的发髻,声音依旧轻柔温顺,“可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这个名字!”
“恨?”崇梓暗暗发力,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喉咙也在逐渐僵化,能够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小,恐怕只有秋奴才能勉强听见。
然而生性强硬的女皇仍旧不肯示弱,紧盯着镜子里的人像,仿佛又看到了十三年前将稚嫩的手指掐在婴儿脖子上的那个小女孩。小女孩幽深的黑眼睛是那么可怕,明明白白地宣示着她对妹妹渐函的仇恨,以至于崇梓不得不狠心用药抹去了她的记忆,不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
可是现在,那个桀骜的小女孩渐幽的眼睛和一向温顺乖巧的秋奴的眼睛重合了,证明无论怎样的调教也无法真正磨去她眼中令人心惊的偏执和倔犟。
“后悔当初没有像杀掉父亲一样杀掉我?可你知道吗,我曾经那么恨你当初没有杀掉我,我宁可死,也不愿跻身奴婢群中任人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