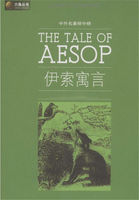离开呼家堡的时候,呼国庆心情十分沮丧。
他并不是怀疑呼伯的办事能力,他只是觉得他晚了一步。既然市里已经定了,那就是说,王华欣已走在了他的前边。到了这时候,只怕连呼伯也没有回天之力了。假如他早来一天,也许还可以挽救,现在会已开过,决议一旦形成,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事已至此,他想,也就破罐破摔吧。
于是,他干脆也不回县里了,就独自一个人开着车,到市里找谢丽娟去了。
夜半时分,他敲开了谢丽娟的门。当小谢穿着一身睡衣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他仅说了一句话。他说:“有酒么?”
谢丽娟一句话也没说,只默默地把他让到屋里,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尔后,她把一双拖鞋放到了他的脚前,跟着就蹲下身来,伸出那双嫩葱一样的手亲自给他解鞋带……待他换上了舒适的拖鞋,身子靠坐在沙发上时,小谢已把酒端上了,那是一瓶红酒和两个精致的小菜。尔后,她才抬起头来,望着他那一腔悲愤的神色,轻声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呼国庆沉默了一会儿,又一连喝了三杯酒,还是说了……
小谢深情地望着他,一直在默默地听着。等呼国庆把该说的都说了,她才偎过去,亲昵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咱不做这个官了,好么?”
呼国庆也赌气说:“这个鸟官不做了。”
小谢又说:“那么,现在你完全属于我了。”
呼国庆就跟着说:“属于你了。”
小谢说:“在我这里,你该高兴的。我要让你高兴起来……”说着,她站起身,先是拉上了客厅里的窗帘,接着,她把屋子里的各种灯全都打开了。霎时,房间里一片明亮!
呼国庆一惊,忙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谢对他莞尔一笑,说:“你等着,我要让你过一个狂欢之夜!”说着,她推开卧室的门,扭身走进去了。
片刻,卧室的门一点一点地开了。接着,有低低的音乐声从房间里流出来,在那轻曼舒缓的音乐声中,走出来的是一个俏丽的模特儿。只见谢丽娟新换了一身粉紫色的一步裙,裙衫的开口很低,上边若隐若现地露着一片乳白,颈上是一串闪闪发光的水晶项链,头上呢,还斜斜戴着一顶粉紫色的夏式女帽。她迈着妙曼的猫步,款款地向客厅走来。当她走到客厅中央的时候,身子微微地转动起来,在呼国庆面前做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舞姿,尔后定格片刻,她又款款地走回去了……当她第二次走出来时,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真丝长裙。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她连发式都换了,她把那头黑发绾出了一个高高的发髻,那发髻衬着一袭曳地长裙,使她显得分外的高雅飘逸,她看上去不像是在走,那分明是在水面上飘,像莲花一样地飘然而至,在呼国庆眼里简直就像是仙女下凡一般!她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迈着轻盈的舞步……再往下,就分明是一团火了。那是一身红帽、红衫、红摆裙。人像是在火里裹着,那火跳着、荡着、旋转着,燃烧着的是西班牙舞姿;那脖颈也像是弹簧做的,一弹一弹一耸一耸地动着,显得十二分的妖冶、放荡!
此时此刻,呼国庆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小谢会对他这么好。他觉得他得到的不是一个女人,是美的和,是美的积!三十多年来,他好像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女人,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女为悦己者容”!女儿真是水做的么?那骨那肉也都是水做的?不然,怎会有如此的浪漫?如此的风流?那鲜艳在一次次的展览、一次次的舞蹈中,变幻着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妖美,那一行一动、一颦一笑、一嗔一嘻,真是千娇百媚呀!
已是深秋了,夜寒寒的,可谢丽娟却一次次地从她的闺房里走出来,一次一次地更换裙装,一次次地展览自己,那奉献饱蘸着女性特有的爱意……当她换到第八次时,小谢两手提着裙边,躬身施了一礼,含情脉脉地说:“国庆啊,我最喜欢的八套衣服全都给你看过了。你喜欢么?”
呼国庆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喜欢。”
小谢说:“高兴么?”
呼国庆说:“高兴。”呼国庆说着,不知怎的,眼里竟有了泪水。
小谢说:“这一生一世,我从没这样儿让人看过,包括我的父母。我只给你一个人看。我只是希望我爱的人高兴。那么,你告诉我,你还想要什么?”
呼国庆一时泪流满面,他双手捧着脸,哽咽着说:“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这辈子能遇上你,值了。”
最后,谢丽娟站在那里,闭上双眼,顷刻间化成了一条白亮亮的美人鱼……当两人相拥在一起时,谢丽娟柔声说:“主人哪,我的主儿。你只看了形式,还没有品尝内容呢。我是你的魔盒呀!我就是你的小魔盒。打开吧,你快快把她打开……”
那是怎样的“魔盒”呢?有风么,有雨么,有惊雷么,有闪电么……当然是有的。那分明是一个忘忧谷,在那里可以让你忘却一切烦恼,你觉得你时而像是在驾着彩虹飞翔,时而是在鸟语花香中踱步,时而又在飞流直下的瀑布里放舟;那云儿就在你的手上,风儿就在你的脚下;天是什么,那是你的腰带;地是什么,那是你随手丢弃的土块;你是什么,你是一片羽毛,你是一支响箭,你是一条快枪!疯吧,你自由了。你是上苍,你是主宰,你是万物的神,你是放荡的魂,让世界颠覆,让时光倒流,让万物都来倾听这肉在肉中的歌唱!
多么好哇。“魔盒”放出的是人世间最优美的旋律。那旋律一遍一遍地诉说:“好么?我好么?想再好么?”
他说:好。再好。再好。
这真是一个狂欢之夜呀!
第二天,当呼国庆醒来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钟了。他懒懒地躺在小谢的床上,体会着从未有过的松弛和乏累。一夜的翻江倒海,使他仍沉醉在那无比的甜蜜之中。那美妙,那温馨,那无比的好,实在是让人陶醉呀!此时此刻,他甚至忘了自己是身在何处。他只是觉得乏,太乏了,那乏像是在美酒里浸过、泡过,带着让人惬意的慵倦。
他睁开眼来,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吸着,望着烟雾一圈一圈地在他的眼前散去。尔后,他扭过身来,看见床头的小柜上摆着一个精致的小托盘,托盘上放的是一杯牛奶、一个煎蛋、两片面包,还有一张纸。他伸手把那纸拿了起来,只见上边写着:“我的人,早餐已备好。我上班去了。等我回来。”后边是一个花形的“吻你”。
当他放下那张纸时,手不由自主地碰到了他的手机。到了这时,他才想起来,他的手机已经关了一天一夜了。他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刚要开,迟疑了一下,却又随手把关着的手机撂在了床头上。
蓦的,他心里就像被虫咬了一样,突然就忆起了他目前的处境。他还是县长么?一县之长。也许,停不了多久,三天?五天?七天?等那个会一开,他就不再是县长了。多少年的心血、奋斗,也就付之东流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能有今天,容易吗?他曾是怎样的努力呀!本来,他认为他是熟悉这块土地的,他知道这块土地上生长着什么。在理论上,他甚至可以给他们开一门有关这块土壤的“政治课”。可是,他却败了,败在了那个王华欣的手下,他真是不甘心哪!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于是,那一团乱麻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接着,他的大脑里像接通了信号一般,立时就化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在机器里,市、县两级的干部们全都成了一个个符号,那些符号在不断地进行排列组合,不断地变幻着组织方式,X Y Z=……可是,不管怎样的变化,其结果最终仍是:此题无解。
呼伯说,有些事,要看值不值……值不值呢?
门响了一下,轻轻的。片刻,谢丽娟突然推开卧室的门,“喵”的一声,跳到了呼国庆的怀里,说:“我的人,你醒了?”接着,她又亲了他一下,轻声说:“我是偷偷溜回来的,还不到下班时间呢。我想看看你。”
呼国庆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谢丽娟贴在他的耳边说:“怎么,你后悔了?”
呼国庆说:“后悔什么?不后悔。”
谢丽娟说:“真不后悔?”
呼国庆有点机械地说:“真不后悔。”
谢丽娟说:“那好,告诉我,中午你想吃什么?”
呼国庆笑着说:“吃你。”
谢丽娟“呢”了一声,在他身边撒娇说:“你吃,你吃。”
呼国庆刚搂住她,谢丽娟却出溜一下,从他怀里滑出去了,说:“别,你太累了。”
过了一会儿,谢丽娟靠坐在他的身旁,忽闪着两只大眼睛,说:“国庆,你的县长情结太重了。我知道,在这块土地上,人是活脸面的,脸面就是人的命。如果仍呆在这里,你会很痛苦的……”呼国庆刚要说什么,小谢却把他的嘴捂上了,说,“你听我说完好么?我昨天晚上就想过了,今天早上又认真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辞职。”
呼国庆一愣,说:“辞职?”
谢丽娟点了点头。
呼国庆诧异地说:“你辞职干什么?”
谢丽娟说:“咱们一块走,离开这里。”
呼国庆有点茫然地说:“上哪儿?”
谢丽娟有点兴奋地说:“去深圳。我那里有好多同学呢。论你的才干,决不比他们差。”
呼国庆沉默了。
谢丽娟偎在他的肩头上,轻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你愿不愿去?”
呼国庆沉吟了一会儿,说:“愿。”
小谢说:“有点勉强,是吧?”
呼国庆说:“我是心不甘哪……”
小谢说:“国庆,我都是为你考虑的。我是怕你一旦……”
呼国庆拍了拍她,说:“我知道。”
小谢说:“天下很大,不是吗?”
呼国庆说:“天下很大。”
小谢说:“这么说,你同意了?”
呼国庆一时冲动,悲忿地说:“走!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小谢一听,“咯咯”地笑起来,于是,两人又滚在一起了……
午后,呼国庆一觉醒来,突然觉得心里很空,很烦躁。他竟然有了一丝犯罪的感觉,他甚至觉得他是在走向堕落。一时,就觉得卧室里那带有淡淡香味的静谧像无形的锯一样,在一下一下地锯他的心。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那没有电话,也没人请示工作的日子,竟是这样的难熬!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把手机打开了……
片刻,电话铃响了,响得很骤!呼国庆心里一个冷惊,立马对着话机说:“哪里?”
只听电话里急切地说:“呼县长么?喂,是呼县长么?!”
他听出来了,立即回道:“……根宝么?是我,我是国庆。”
徐根宝在电话里说:“你在哪里?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也打不通你的电话。这会儿,你在哪里?!”
呼国庆怔了一下,迟疑说:“我、在……市里。”
徐根宝在电话里说:“呼伯让我转告你,要你立即回到县里去。回去以后,不要向任何人打听消息。原则是,不问不说,照常工作……你听清楚了么?”
呼国庆听了,心里砰砰跳着,从床上一跃而起,说:“明白了。”
挂了电话,呼国庆快速穿好衣服。当他要离开时,才“呀”了一声,猛地一拍脑壳,在慌乱之中找到了一片纸,给谢丽娟匆匆留了一个条——
小谢:情况有变化。来不及等你了。回头再给你联系。
国庆匆匆。
紧接着,门“啪”的一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