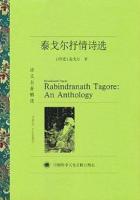文/张秋实
苏州是我童年的故乡,灯船是我童年的伙伴。离开苏州好多年啦,怪令人思念的。我们大学一放暑假,我就和妈妈挤上火车,去探望我的外婆婆,最主要的,还是去看看我日盼夜想的灯船。
童年记忆里的苏州,最深的怕是那彩色的灯船吧,那时,初夏的夜晚,外婆常扯着我去看灯船,有时高兴啦,给我讲灯船的故事,哪怕是最古老的,甚至老掉牙的传说吧。所以,大了,人们一提起苏州,在我的记忆里,它不是一座座优雅精致的园林;也不是那怡静的流水,小桥,人家;除了灯船,还是灯船。
妈妈轻轻推推我说:“兰兰,在想什么?”
我从沉思中醒过来,笑笑说,“我,我在想灯船呢。”
到达苏州的第一个晚上,外婆就和我们商量着,说要带着红菱和甜藕上灯船。上船了,那通亮的水面上像一个彩色的世界,灯影沉下去了,像许多彩带子飘在无底的深水之中。透明的水中,灯船稍微一动,那彩带子就乱了,乱得不可收拾。我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小时候不是央求着外婆婆带我去捞彩带子吗,外婆曾哄我说,那是天上落下来的彩虹,不能捞,也不能用手指头指,哪个指头指了,哪个指头就生疮。童年,每个人的童年,大概都有一些天真、幼稚,而又十分可笑的事情吧。
外婆提着的小竹篮里,装满了鲜灵灵的菱角,我抓一把,吃着。我央求着外婆再给我讲灯船的故事。妈妈打断我的话,非要我背一首关于苏州的诗来作为讲故事的条件不可。我嚼着菱角,背起了那刻在我儿时脑际上的诗句来。那是一首晚唐诗人杜旬鹤的《送人游吴》的五言诗: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背到这儿,我心头有了些隐隐的乡思,这里,留下了我儿时的多少记忆哟!那富有诗意的灯船,曾驮着我的童年,曾驮着我童年想象的翅膀。
一只只灯船过来了,慢悠悠地交织着。外婆问我,“那大学的书上可记着苏州的灯船?”我摇摇头说,“这算什么,怎么能写入大学课本上呢?”妈妈却笑着问我说:“兰兰,你知道东方的威尼斯是指哪个地方吗?”我不假思索而又满有把握地说:“上海。”妈妈和外婆都笑了。妈妈说:“大学生啦,还这么寡闻,瞧,还不如你这不识字的外婆哩!苏州,早就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啦。”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外婆一定要给我讲讲这苏州的灯船,好像这些心事憋在肚子里难过。
“苏州的灯船啊,不知多少年多少代了。听人说,大清道光年间就很盛。那时,灯船上都搭着灯架子,每只船上至少说也有上百盏灯,船呢,也宽大,两边有侧门,中间有大排门,舱中还有绣花窗帘哩。每年的春四月,就开始搭灯架子啦,开始的时候,叫‘试灯’,一直到桂花凋败才结束,那叫‘落灯’……”
妈妈又告诉我说,她小时候,每逢佳节,天不黑就去观灯船,太阳不落,结伴的游船早来了。听大人们说,那叫“下虎丘”,下虎丘的船,一定要在东溪小泊。当暮色染水的时候,就好看极了,百灯齐亮,水色灯光,一碧万顷,一只一只首尾相接的灯船上,琵琶重弹,轻歌曼舞,绕过斟酌桥,牵着鱼鳞波,迤逦来到了野芳浜。
“您坐过吗?”我问妈妈。
“没有。小时候也像你一样好奇。天天晚上看哪,看哪,我讲的这些,一半是看到的,一半是听到的。”
彩色的灯船上飞来了一阵阵歌声,外婆对我和妈说:“解放前,都是富门豪户家坐,穷人站在边边瞧,如今,是不一样了。……”一只灯船过来了,录音机里正放着贝多芬的《月光曲》。一只灯船过来了,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她们脖子上系的红领巾,大约是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的营员们吧;又一只灯船过来了,上面坐着佩戴校徽的大学生,你瞧,他们在醉心地涉猎着这不夜的灯市,想必是来寻诗的吧。
天上的月光,船内的灯光,水面的波光,溶在一起了,使你觉得如在银河中穿行。岸边的琴声,船上的歌声,近处的笑声,溶在一起了,如飘动的诗,似流淌的画……